
頭薦骨/身心學/澄心/SRT/一人公司/被動式投資,關注個人安康發展與生活品質(QOL),個人接案中。 詳情請洽:https://tinyl.io/3L4b
不再試著修補生命
在生物動能取向的頭薦骨(BCST)中,會以慣性模式(inertial pattern)稱呼那些持續限制住身體展現自身的種種過往,BCST的主要工作向度,也是試著消融種種過往影響的殘餘,並支持身體能更完整地展現自己。然而,慣性是什麼意思?舉例而言,當一個人曾經遭遇過車禍,被撞擊的那些部分可能在骨骼結構或組織層面上留下持續性的影響;也可能在我們身上持續運作著出生時所發生的擠壓,而導致長期性的偏頭痛,或者頭顱裡的不平衡感;又或者我們曾經接受過醫美或整齒的醫療工作,因而感覺臉歪掉或不平衡。
這些都是某些慣性模式常見的呈現方式,而慣性模式不只會出現在肉體的生理功能展現上。「身體」兩個字不只包含了肉體的生理性層面,身體也包含了種種其他的面向-情緒、情感、身體感受、認知、存在感、原形,或者存在的基底等等,也都蘊含在「身體」兩字之中。而所有身體的層面,都可能有慣性的模式在裡頭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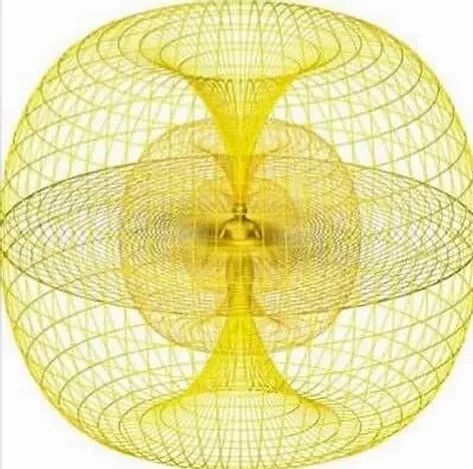
所以,不只是身體種種組織的病變或扭曲,沒有說出口的情緒或感受、我們習慣性的人際關係互動、習以為常的身分認同、種種我們看待自己與整個宇宙之間的關係,或者任何我們能想得到的面向,都可能出現習而未查的慣性模式。然而,這並非說慣性模式是對的,或者是錯的,研判一個東西是對或錯,這本身就是一種心智的慣性-想要快速地判別某個價值觀或看法是否可以接受,或者是否是熟悉的事物。
這裡或許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讓這樣的說法比較容易被理解。
早一輩的人對女性常會有一種集體式的認同,「女人應該要持家、要保守、要『盡到身為女人的本份』」。這裡我會先將「這樣的觀點是對或錯」這樣的判斷存而不論,而只是來看看,當這個觀點變成一種慣性的自我認知時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讓我們想像一位老婦人,她很年輕時就離開了自己的家並嫁入別人家中。在她離開她的原生家庭之前,她的家人對她不斷地教誨是,「妳到了那邊就要以夫家為大,要顧好廚房,早上起來要記得打掃點香。女人家不要太懶惰,要以婆婆為重......」。於是,這個人在嫁過去之前,就有了某些應對未知情境(那個不知道有誰、生活習慣是什麼,幾乎完全陌生的夫家)的方式:當好一個女人、一個媳婦,要「安分守己」,可能還覺得要遵守一套媽媽告訴我的生活方式,不然「就會給自己家蒙羞」。
我們如果讓這個想像繼續,來到五十年後,我們可能會看到這位為某個家庭付出了一生的老婦人,她可能滿懷著「這個家從來就沒有人會感謝我為他們做了什麼,沒有人謝謝我煮飯,沒有人謝謝我打掃......」之類的怨;或者,可能會覺得自己不能閒下來,不然其他家人會吃不飽,即便其他家人可能都已經成家立業,生活再也不是問題;或者可能會覺得自己好像沒有真的活過。
值得重新申明的是,這裡並不是說這種對於身分認同的慣性是好或壞,只是一種思想上的延伸,看看這種認同可能帶來的結果。而對這名婦人來說,這一切-覺得沒有被榮耀、沒有活過、沒有辦法閒下來等等-都是真實的。這一切在這種人生觀中都是真的。然而,另一種從慣性的角度來看的觀點也同樣真實:這名婦人太過地認同了「女人就是應當如此」的故事。
在不同的角度下來看,這兩種真實都同樣真實,差別只在於那個切換不同角度的能力,被某種慣性的習慣給侷限住。同樣地,這兩種觀點也會帶來兩種不同的自我認識方式:對過往的自我認同,可能會更多地帶來「我是這個家的受害者,我無能為力做出什麼改變」;而從慣性的角度來看,我們可能看到更多的積極性面向:「我受傷了,我有某些受傷的感覺,那是源於我的過去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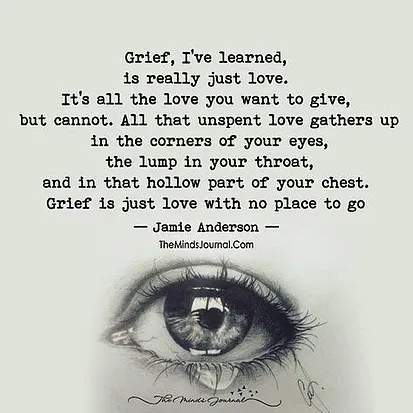
「我受傷了」跟「我是受害者」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我受傷了」是一種對過往歷史的精確描述,這裡面描述的是一種造成後續感受的經驗,是個人曾經發生過的歷史,它是對實際發生過的事做出的描述。換句話講,「我受傷了」是跟過往發生的事拉開一段距離,但不是背離這件事,也不是逃得遠遠的,就只是待在一個適合的距離下去看它。
「我是受害者」則與上述的說法有很大的不同。這句話會讓一個人用受害者的身分來定義自己,並在裡面分化出另外兩個部分:那個加害你的加害者,還有對於被拯救的渴望,或者,這個拯救者會特異化成所謂的彌賽亞情節(Messiah complex):我拯救別人,而我暗地裡期待著有一天別人能用我拯救別人的方式來拯救我。
當我們用受害者的身分來自我定義時,某個部分可能還會引此為傲:我是受害者,我受害的程度比你高。一個受害者可能與另一個人比較誰受到的苦比較多,或者藉此合理化將別人視作加害自己的人,並藉此批評那個人在加害自己。比如說,我們可以說自己很敏感,但這與藉此指責別人不用敏感的方式對待自己,這之間其實有很大的區別。
受害者是過往的歷史在運作,加成我們浸泡在過往的歷史,因而未能完全明鑑當下整體的運作。我們可以為受害者的身分加上無窮盡的敘說,找尋無窮盡的理由,然而,這背後其實在做的都是一件事:我強迫性地聚焦在「過往發生過問題,我要試著修補問題,或我要試著把過去殺掉」這個焦點上,然後問題就會不斷地被強化。或者,我們甚至可以用這個故事來說自己很努力,然後持續增添故事的細節。
著名的薩滿阿貝托(Alberto Villoldo, Ph.D.)曾經在他的《印加大夢──薩滿顯化夢想之道》裡這樣描述過:「我們喜歡在自己的故事中加入很多細節,讓故事聽起來感人肺腑,並自己編造了一個情節,讓自己深深陷在裡面......大家爭相比較誰受的苦比較多、誰的擔子比較重、誰的痛苦才是真的痛苦。對於誰該先開口道歉這件事,又是誰的藉口比較合理。我們腦中蒐集著各種標示著『傷口故事』的檔案,不時便拿出一疊向人們揮一揮,宣稱這些故事可以證明自己如何值得被憐憫,值得特別的待遇,或者不需要在關係當中付任何責任。」

要從慣性當中改變會需要勇氣,而在改變之前更需要的其實是看見。同樣重要的是,「想要從慣性中改變」這件事,一直都是個人生命當中最隱微、最為私密的一些內在決定,以及某種神祕的感召。慣性如同我們出生後的子宮,那是一處溫暖、熟悉、能確保某種安全性的狀態,多數人會在這種慣性之中昏睡,直到某天,我們被生命撼動,然後開始覺得有哪裡奇怪,或者開始覺得哪裡不對勁。
待在這種出生後的子宮裡並不是好或不好,這種環境的確會提供一種安全感。只要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動,我們就得以維繫這種安全的感覺;然而,這種奠基於「事情不會有太大變化」的安全感,本身的前提就不是一種穩定的前提。萬物都在變,我們賴以界定自身的安全感,實際上也隨時都在變化著。
好消息是,我們可以從種種強迫中慢慢學習轉移焦點。面對慣性的第一件事是,認知到我們不是試著抹消自己的過去。過去發生了,這是事實;我基於某種犧牲或奉獻而有失落感,這是事實;我會因為某人突然離去而心碎、憤怒或歡愉,這也是事實。這些不是我們需要去抹煞的事實,而是有待我們整合進入生命中的感受。
在資源的建立上,我們有機會慢慢整合與多元化自己生命的意義。過去發生的的確發生了,破碎、失落、混亂、矛盾、害怕與擔憂、焦慮與挫折,那些以一整團的感受在當下持續運作著。但即便如此,這仍然意味著我們有機會可以拾起過往的種種碎片,有機會可以跟過去沒有活過得好好道別,有機會可以哀悼過往的難過與失落,也有機會好好的看到憤怒底下的那些脆弱。
生命會越來越複雜,而我們看待這種複雜的角度可以越來越單純,這是不相衝突的。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