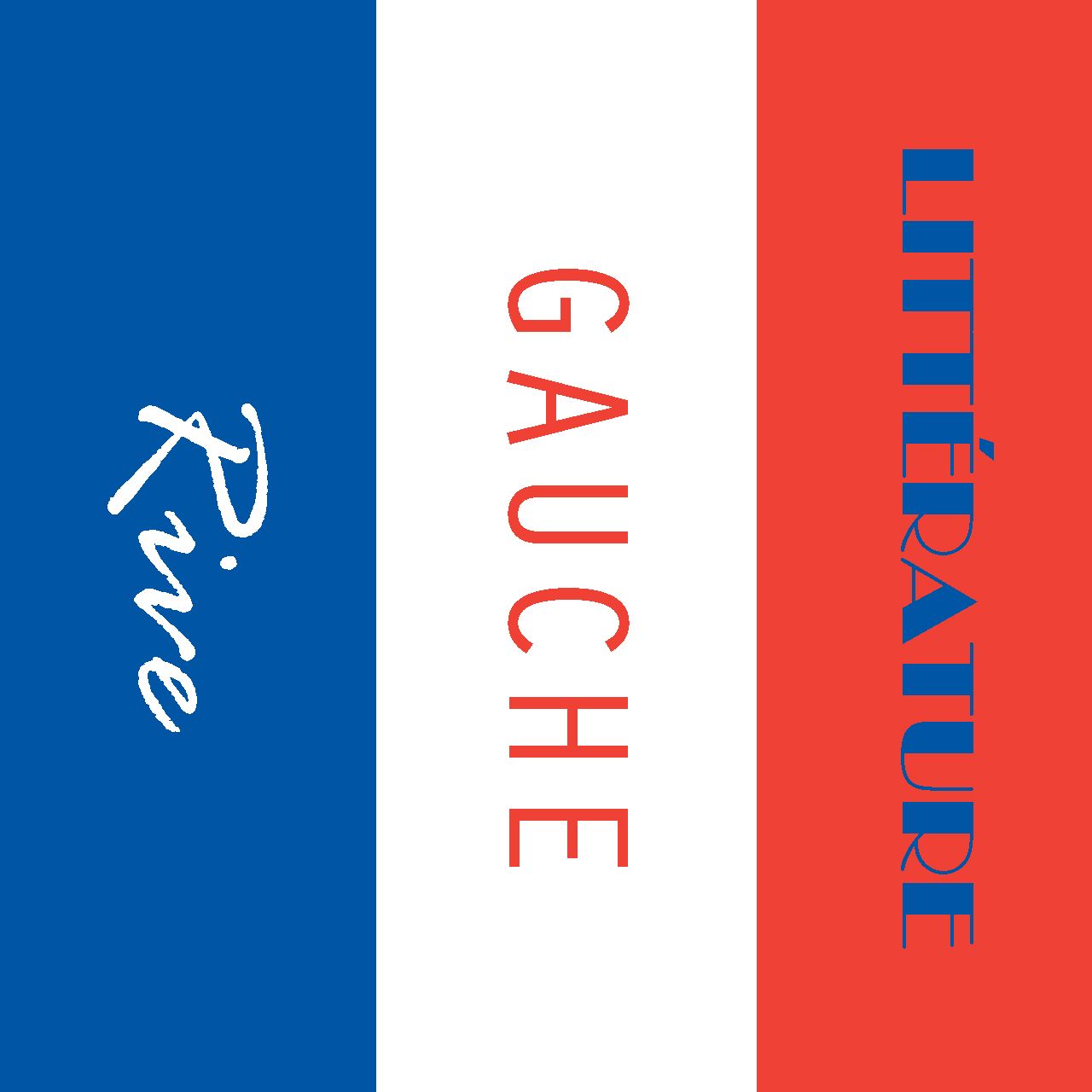
“让想象力统治一切。” 微信公众号:rivegauche_68
短篇小说/列宁在2008

列宁在二〇〇八
文/林伯奇
图/Leo Reynolds,于伦敦,2015年2月6日。
绘/Alexander Kosolapov, 1987
瓦西里站在警局门外安静地吸烟。这烟是他不久前从中国带回来的;他站在警局门口,时不时地走动几步,然后接着抽烟。他眯起自己的灰眼睛凝视着灰蒙蒙的天空——八月,又是八月。不一会儿,维克多拖着他的脚步从警局大楼里走了出来,脸上还带着淤青。那一青一肿的部分,有的是打架的时候打的,有的,瓦西里认为是在警局里给打的。
“走吧。”接到了维克多,瓦西里就把香烟扔在地上踩灭,两人走向瓦西里的那台二手现代小轿车。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滨之声’广播电台。”车载收音机里传出一个轻柔的女声,这个女声很快就被另一个雄浑的男声盖了过去,“今日,联邦总统德米特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正式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与格鲁吉亚当局达成一致协议……”
“你要抽烟就打开车窗抽,他妈的。你抽烟的样子真像个哈萨克农民。”瓦西里不满地说。汽车以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从一上车,维克多就开始抽烟;维克多这人话不多,瓦西里这么一说,他便把车窗摇了下来,夹着烟头的手搭在车窗上。八月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空气里增添了不少细小的水珠,天空常常是阴阴沉沉的,这样的天气让瓦西里觉得比冬天的苦寒更加难以忍受,而把被二手烟熏过一遍的水蒸气吸进气管的事情让他恨不得现在就掐死维克多。“他妈的,车臣还没完,格鲁吉亚又乱成一锅粥。整个高加索都像他妈一锅粥。”瓦西里嘟囔了一句。
“得,你又要提你表哥在车臣挂彩的光荣事迹了,我们都他妈听腻了。”维克多终于开口了,发了一句牢骚,“他现在还好么。”
“他现在去德国了,我也没有怎么跟他联系。”瓦西里说,“但愿他一切都好。”
“是么?他一条腿在车臣给打瘸了,还能去德国混一混……”维克多笑了,瓦西里也跟着他笑。车子从金角湾海岸的公路驶过;维克多凝视着矗立在大桥工地旁边的卫国战争纪念雕塑许久,把手里的烟头给弹了出去。烟头落在公路上的水洼里,熄灭了。
连长,开火,开火吧连长;为了我们身后的俄罗斯、莫斯科和阿尔巴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滨之声”广播电台通过电波传递出这样的歌声,现代小轿车里的两人陷入了一阵沉默。维克多闭上眼睛,画面接踵浮现在自己的眼前:高耸的高加索山峦,坦克成群结队地穿过乡间小道;飞机盖住天空,扔下炸弹;穿着迷彩服海魂衫的士兵站在绿色的田野里向远处发射火箭弹;格鲁吉亚人节节败退。不论怎样,总算是结束了。瓦西里和维克多都如是想到。北京奥运会还在进行时,而如果把瓦西里和维克多扔到老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老家去,这些在远东工业区里长大的孩子们即便经历过再多清一色阿迪达斯外套的“街头大战”,恐怕也会不知所措。瓦西里可能能撑得住,但是维克多恐怕就会变成一个战场PTSD患者,屁滚尿流地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他们这些小年轻是俄罗斯的耻辱,维克多的父亲如是说。小轿车停在一栋筒子楼的门口,维克多下了车。“我晚点来找你。”瓦西里对他说。“洛卡(Пока)。”维克多回应,瓦西里便离开了。维克多下了车便往筒子楼的大门走去,但他走到大门口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折返了回去,摘下了一把野花,捡了个塑料瓶,把野花插在塑料瓶里放在筒子楼下的一尊铜像下。铜像的基座上刻着几个字:В. И. 列宁。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个不缺雕像的城市,而这些雕像也从来不缺少鲜花。大大小小的列宁雕像,卫国战争纪念雕像,还是和帝国时期历史有关的雕像,到处都是,而维克多从小就在这么多雕像里成长,他自然就养成了会给雕像献花的习惯。维克多平时沉默寡言,很多人觉得他是个怪人,以至于他会给雕像献花的习惯也被视为一个怪癖。但对维克多本人来说——他只是想做这件事情,仅此而已。
“妈,我回来了。”维克多打开了自家的门,打了声招呼。
“你回来了?”维克多的母亲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没有看维克多一眼,“我待会要回厂里加班,晚饭放在桌上了,你热一下就好。”
“哦。”维克多嘟囔了一声,就走进自己的卧室,把门一关,倒头就睡。
自有记忆起,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布隆施泰因大部分的时间便在远东海滨小城符拉迪沃斯托克度过。他是俄罗斯人,但是有犹太人和蒙古人的血统。作为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的同龄人,尽管他是在社会主义时代最后的几年里出生的,他对那个曾经存在过的超级大国没有什么记忆,只记得自己的童年在吃了上顿没下顿里度过。维克多的父母本都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造船厂的工人——老谢尔盖去了满洲,这里只剩下了维克多和他的母亲。维克多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有时他去附近的汽车厂做做短工临时工,有时他也会去满洲带带货顺便探望一下父亲(尽管父亲不是很愿意见到他),带的货大到汽车小到各种日用品,有时他给当地的大佬收收保护费催催债,有时他又会在大街上接连闲逛个两个星期也可能会去国立大学干个杂工之类的职务。维克多是个混混。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个堆满了铜像的城市——又或者说是一座堆满了垃圾的城市。曾经赫鲁晓夫来到这里,说,要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成苏联的旧金山;这么多年过去,苏联解体已经有17年的时间,依然可以在这个又叫做海参崴的城市里找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影子。符拉迪沃斯托克堆满了列宁像,赫鲁晓夫楼,大大小小仍在运营的破旧工业厂房和像维克多这样的痞子。如果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还有什么存在意义,可能仅限于拿来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举办会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贸易集散中心;港口里停着的军舰还能提示这座城市有过的光辉历史。它曾经是西太平洋的旧金山。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座时间被停止了的城市——或者说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都是如此,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巴罗夫斯克,从伊尔库茨克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似乎都被冻结在了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然而然,这里的居民慢慢就生成了一种nostalgia的情感。维克多和瓦西里也不例外。瓦西里是军人的后代,他的祖父参加过卫国战争,后来被派驻到远东便落叶生根,而维克多的祖先是在帝俄时代被流放过来的。他们两个人打小就认识,成年后又一起往返于俄中边境之间,只是就连瓦西里也不理解维克多献花的意义在哪。有人会献花的——不论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是政府委派的人,符拉迪沃斯托克最不缺的就是老人,维克多干嘛要对献花这件事情这么上心?他真的是社会主义者么?他很nostalgic吗?为此维克多过去还因为献花受过嘲笑。
人们常说筒子楼下的铜像上的那个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讨厌他的人会说他是一个疯子,这些对铜像的议论,从维克多的孩提时代就不绝于耳。理想是什么?如果他知道答案,那维克多就不至于当一个混混。这是他和瓦西里站在铜像边上一起抽烟时想的问题。尽管铜像上已经长了层锈,表面凹凸不平,但铜像刻画的眼神传达的依然是某一种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宝贵精神。这时,那股nostalgia的感情便会升起。维克多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把献花当成一件习惯来做,可能是想抒发他的某种情感,但那股动力在何处,他也不是很清楚。
当维克多再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窗外的黄色灯光从玻璃窗照了进来,房间里微微地有一种朦胧感,维克多这才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拉窗帘。他站起身,揉了揉自己的凯撒式短发,走出了自己的卧室。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08年8月……”伴随着由大彼得罗夫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时间,前进!》音乐,晚间新闻节目拉开了序幕。维克多站在厨房里,把母亲留下的饭菜和罐头肉汤微波加热了一下便草草地吃了晚饭。
维克多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什么,那些关于梦境的记忆已经被起床时的头痛和眩晕感冲淡,他只记得梦里有几样东西:火车,大海和列宁铜像。火车汽笛很响,海浪很高,列宁铜像也很高。他就记得这么几件事情了。
吃完了晚饭,维克多看了看钟表,随后就听见了楼下传来了汽车鸣笛声。那是瓦西里的现代小轿车的声音。听到鸣笛声,维克多便披上了一件空军夹克,便下楼去与瓦西里会合了。
“一杯伏特加。”“一杯格瓦斯。”
瓦西里和维克多驱车来到了达瓦里希酒吧。达瓦里希酒吧是瓦西里和维克多常常拿来打发时间的场所;这里也是当地地头蛇的地盘,他们也常常为这些人干活。
“碰杯。”绿色的玻璃酒杯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瓦西里和维克多坐在吧台那里点了自己的饮料,酒精逐渐舒缓了维克多的头疼;吧台旁的小电视正在实况转播北京奥运会的比赛,舞台上的乐队正在弹唱披头士的《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
“最近,”维克多对瓦西里说,“有什么活干么。”瓦西里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又给维克多点了一支。
“你还要干活啊。”瓦西里说,“你才刚从条子那里放出来。你瞅瞅你这样,左一个疤右一个瘀青,今天晚上要是有姑娘搭理你,这个星期的酒我请。”
“上次跑那趟没赚什么。我再跑次中国呗。”维克多说。
“你太鲁莽了,老兄。”瓦西里说,“你太容易被发现了。不是你赚的不多,是你可能带来的损失太大。”
“老彼得车厂那里还有活么。”
“这个倒是有。老彼得最近刚弄到一批日本货,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吧台旁边的一个桌子围坐着一群年轻人,看起来和瓦西里维克多年龄相仿,像是在开个什么聚会,弄得挺欢腾。
“他们在干什么?”瓦西里问酒吧老板。
“他们都是国立大学的学生,要去莫斯科了。”老板一边说一边擦着玻璃杯。
“是啊,现在都他妈去莫斯科了。”瓦西里说,“莫斯科好混,想升官发财的都去莫斯科了。就剩下咱们这种瘪三还留在海滨喽。”
“莫斯科有什么好的。”维克多嘟囔了一句,“这里不会好,莫斯科也不会好。哪里都一样。”
“大城市的机会总是比这里多一点。”酒吧老板说,“远东海滨,大概也就这样吧。”
“哈尔滨也是座大城市,待在远东,对我来说,足够了。”维克多说。
“你好像也就去过中国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吧。”瓦西里说。“我乐意。”维克多恶声恶气地说了一句。
“不论如何,未来总是美好的。”酒吧老板说,“干杯吧,小伙子们!再不干杯就迟了。愿祝所有人都能遇见自己的美好未来——至少莫斯科没有这么多的列宁铜像。”
维克多凝视着酒馆老板的脸,有些迟疑地举起酒杯,跟瓦西里碰杯。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等两人在达瓦里希酒吧打发完时间,已经是十点钟的事情了。
“你送我回去吧,我最近有点累。我想早点休息。”维克多钻进现代轿车的副驾驶座,对瓦西里说。
“唔,好吧。”瓦西里说着,发动汽车。
两人驱车向维克多家驶去。
“这么多人现在都走了……”瓦西里说着,“我看看。我们的小学同学里,科科洛夫,斯梅尔诺夫,察里金斯基去了彼得堡;罗曼尼茨基,切斯卡钦去了莫斯科……”
“瓦西里·米哈伊维奇,你要去莫斯科么?”维克多说。
瓦西里久久没有说话。“我想去,想去莫斯科,学着做点生意,能从西方那边赚点钱。老是待在这滨海也不是回事啊。”
“原来连你也是这样么?”维克多点燃一根烟,嘟囔着说道。
“维克多,你看我们这……”
“原来连你也是这样么。”
汽车开到了维克多家楼下,维克多下了车,头也不回地朝自己家走去。“嘿,维克多……”
“晚安。”维克多说。
回到家后,维克多躺倒在自己的床上。他没有开灯,屋外的黄色灯光映射在布满灰尘的天花板上,整个房间里堆满了阴影的黑色和灯光的黄色。车辆的路过有时打破了黄色的光影,窗户的影子则投射在维克多的脸上。他回想起他对瓦西里说的“原来你也是这样么”的话便想笑。他闭上眼睛,眼前浮现的是一万公里外的圣瓦西里大教堂的样子;想笑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一时顺着说出的话是有多么可笑。
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一个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的人想出去的围城,那它必定是海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这里有着被这个世界所遗忘的东西,而这里的人们为了避免要被遗忘的命运,纷纷要从这保险箱一样的,被时间隔离起来的城市逃出去。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居民们自带时间的基因,而时间的封锁也会随着他们的脚步扩散开来,从这遥远的海滨到莫斯科,然后是整个俄罗斯,再然后是整个欧洲。维克多接受了这海滨小城的基因,他对莫斯科没有更多的向往。这里的居民,不是过去被流放的,就是被派驻到远东来守卫俄罗斯母亲每一寸领土的人。维克多也会继续在这海滨守卫下去,但他恐怕守护的不是那个抽象的俄罗斯母亲,而是时间。维克多是时间的卫士。
符拉迪沃斯托克人离开了土地,却走不进海洋;维克多是时间的卫士,也是欧洲的弃子。
慢慢地,维克多又进入了梦乡。在他的梦里有火车的汽笛和大海的波涛,他们一起演奏了一首《时间前进》;太阳从东面的海平线上升起,而列宁像的影子指向西方。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各就各位!”基梁诺娃说道。
“好极了!这一下该我上啦!”华斯科夫说,“我要去抓活的!”
德国人的飞机被打中了,德军的飞行员被迫弃机跳伞。女战士们欢呼。大银幕上正在放映的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1972年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电影院里没有几个观众,有的只有几个老人家,维克多,和放映厅角落里正在为客人提供服务的性工作者。维克多懒洋洋地躺在已经开裂的皮座椅上,双眼无神地盯着大银幕发呆,把两只脚翘在面前的座椅背上。一个中年人走到维克多的旁边:“这里可不是你到处放肆的地方,小鬼。”
维克多瞥了他一眼,缓缓地起身。随后他突然给了面前那个中年人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中年人趔趄了几步,随后便捂着鼻子匆匆地跑出放映厅,嘴里还不忘嘟囔几句“现在的世代”这样的话语。
离开了电影院后,维克多乘上了开往工业区的巴士。他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静静地看着这海滨小城里的一切。来自中国的商人;鱼肉工厂的卡车;大烟囱;各种各样的雕像纪念碑。有莫斯科人会想着来这符拉迪沃斯托克么?维克多想到。这个城市里充满了铁锈的味道。那么莫斯科是什么味的?这个问题维克多倒是从来没有想过,他对于俄罗斯的首都没有更多的想象,这件事情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当他的心里冒出了一个“福尔马林味”的答案时,他不免笑了一下。
维克多下了巴士,徒步行走。据说再过一段时间,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巴士将会换成由韩国大宇制造的客车。维克多穿梭在工业区的街道上,走到了一家车房前。车房门口停了整整一排本田丰田马自达的车子,锈迹斑斑的招牌上写着“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字样。
“我听说这里有活干,”维克多走进车房,说,“我是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
老彼得走了出来,“是的,这里是有活……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维克多。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
“噢,好……你父亲是谢尔盖·布隆施泰因么?”
“是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
“我认识你父亲。过来看看吧,小子。”
“Bravo!”
电视里正在播送北京奥运会的赛程;伊莲娜·伊辛巴耶娃以5米05的成绩再一次打破了女子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110米男子跨栏的第一轮比赛中,刘翔宣布退赛。
“我去找了老彼得。”又是在达瓦里希酒吧,维克多对瓦西里这么说道。
“是么?不错……”瓦西里喝了一口冻啤酒,“你打算做几天?”
“三四天吧,不长。”维克多说,“做做杂工,改装之类的东西。我打算过段时间再去趟中国。”维克多又说,“你决定了么?”
“啊,我打算过段时间就把车卖了。”瓦西里说,“没办法,资本主义的世界太诱人了。你不打算去么?”
“莫斯科不属于我这种人。”维克多说,“瓦夏,不得不说你的决定实在太突然了。”
“是么?在俄罗斯什么是不突然的。”瓦西里又喝了一口啤酒,“突然一下子,德国法西斯就宣战啦,我们就造出氢弹啦,走进发达社会主义啦,柏林墙倒塌啦,弗拉基米尔·弗拉基伊维奇就上台啦……”
“该来的都会来,”维克多喃喃自语,“只是我不习惯只有我一个人去跑货罢了。”
“‘海滨之声’广播电台。今日,我军正式开始从格鲁吉亚撤军。针对北约方面对俄罗斯发出的谴责,我国政府……”
“一群可怜虫,”瓦西里说,“我是说那些格鲁吉亚人。”
“谁不是呢……”维克多点上一支烟,“有的可怜虫要死在高加索山脉上,有的可怜虫要死在远东的海滨。”
瓦西里笑了笑。“Up to mighty London came an Irish lad one day……”他唱道。
“All the streets were paved with gold and everyone was gay……”维克多也跟着唱。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It's a 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to the sweetest girl I know!
Goodbye, Piccadily!
Farewell, Leicester Square!
It's a long long way to Tipperary,
but my heart's right there!
就这样,两个俄国人用蹩脚的英文在车里唱起了《到蒂伯雷利的漫漫长路》。现代小轿车缓慢地在路上行驶着,路过一个小的篮球场;人行道上有几个穿着阿迪达斯的小年轻走着。
“嘿,维克多。你看那不是鲍里斯么?”瓦西里说。
“是的,他是。”
“你之前说你看他不顺眼好久了。来吧,下车揍他一顿。”
维克多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抽烟。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白昼的亮光反射进维克多的房间,他熄灭了手里的烟头,喝完了杯子里的茶,便站起身穿上他的空军夹克。
“妈,我要去看看爷爷。”维克多走出房间,对客厅里的母亲说。
“噢,好的。”
“准点报时。现在是VLAT时间,2008年8月19日,早上9点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滨之声’广播电台……”
维克多乘坐巴士,来到了一栋比自己家还要老的公寓。公寓楼下的老人正在下象棋,收音机里传来“海滨之声”的声音。
维克多走上楼去,敲了敲一扇木门。过了好一会才有人应声:“谁啊?是谢尔盖么?”
“是我,维克多。”维克多说,“爷爷,我来看您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来给维克多开门。“是你啊,好小子!你爸爸呢?”
“他还在中国。我来看看你,爷爷。”维克多说,走进了门。老人的家比维克多的公寓要显得更加简陋:一台原产东德的黑白电视,一瓶兑了白水的联盟牌伏特加,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还有一副画着一个红军战士的牛皮纸贴画。
“我给您带了些吃的。爷爷,你最近怎样?”说着,维克多把纸袋放在木质餐桌上。纸袋里装的是一瓶斯丹达牌伏特加,香肠,肉罐头,汤罐头和一些新鲜蔬菜。
“很好很好……”爷爷看着纸袋里的食物,“你呢,小伙子?”
“我现在在汽车厂上班。”维克多说。“工资待遇都不差。”
“啊,汽车厂好,汽车厂好……”爷爷嘟囔,翻弄着维克多给自己带来的食物。“你是个工人了。”
“工人,”维克多也跟着念叨,“工人。”
“呵,我还以为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我这个老不死的啦……”爷爷说,“你不去莫斯科么,维克多?”
“我不去莫斯科,爷爷,”维克多说,“我要是走了,谁来看您呢?”
“现在的年轻人该去莫斯科的都去莫斯科啦,”爷爷说,“今天楼下的伊万·瓦什科夫就要去莫斯科了。你小时候还跟他一起玩过呢,你还记得他么?”
“是的,我记得他。”维克多说,“我有时会去一去中国吧,去看看中国有没有什么生意。”
“莫斯科,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就去这两个地方,”爷爷说,“你也应该去欧洲看看,维克多。”
“那里不适合我,爷爷。”维克多说,给爷爷泡茶,“我喜欢海边。”
“我们本来就是被流放来东方的人,维克多,”爷爷说着,打开了那台东德的老电视,“虽不说落叶归根,去欧洲那边看看总归是好的。”
“爷爷,”维克多烧好了水,走到列宁肖像前,细细地打量着面前的像,“你能跟我讲讲过去的故事么?”
“怎么,你想听?”爷爷说,“你开始对这些老故事感兴趣了么?你过去从来都不爱听的。”
“只是……你还记得么?瓦西里·米哈伊维奇也要去莫斯科了,我就想听一听那些过去的故事。您不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么?”
“呵,同龄人说不上,我虽是个老不死但还没那么老,差不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肃反的同龄人罢。”爷爷说着,往烟斗里装进烟叶,“有些事情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大肃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维克多问,又把视线移到了斯大林肖像上。
“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我只记得,每天晚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路上都开着‘乌鸦车’,会有半夜敲门的侦查员……很多人都不见了,比如和我们同一个大院里的朝鲜族小孩……他们都不见了。”
“他们都不见了。”维克多复读了一句。
“因为我们家是工人,我们才得以留了下来。”爷爷说,“四五年的时候正式进攻日本,这里也成为了前线。咳……”
“时代……”维克多盯着斯大林的肖像嘟囔着,“什么样的时代……”
“关于那个时代的东西,能讲的实在太多了。何不去读读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爷爷说。
“爷爷,我得走了。”维克多对爷爷说,“我得回厂里上班了。”
海浪拍打在石壁上。维克多一个人走在海边的人行道上,两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叼着一根烟。海边的风很大,浪很高;太平洋海军舰队的船只稳坐在港口里,一面圣安德烈十字旗挂在舰尾上迎风飘扬。维克多慢悠悠地走着,看着大海和远处的岛屿。波涛汹涌的大海让他想起了自己以前逃学翘课和瓦西里在船上钓鱼的时光——时间,如果要问维克多时间去了哪里,人死后去了哪里,大概是到了海浪里了吧。海浪替死人释放他们生前尚残存的生命力,让他们好去到死后的世界安眠;时间也被卷进海里,随着日月而潮起潮落,它们尝试着扑向陆地,扑向那广袤、荒芜而黑暗的西伯利亚平原,却又被力量无情地拍打回过去,无限轮回。
烟丝烧完了;维克多踩灭了烟头,靠在海边的栏杆上,拿出了一个金枪鱼午餐肉蔬菜三明治大口咀嚼了起来。要是能有一杯啤酒就更好了,他心想。海面上泛起了一层大雾,让商船和岛屿时隐时现;维克多看到一尊巨大的雕像浮在远处海面上。那是斯大林的雕像。就在维克多试图定睛看清楚的时候,斯大林雕像的影子又被茫茫的雾海所淹没,盖了过去,在海面上消失不见。那是海市蜃楼么?维克多想。吃完了三明治,维克多把手放在牛仔裤上拍了拍,便往车房的方向走去。
“这是你这几天的薪水。”维克多放下手边的扳手,合上引擎盖。老彼得从休息间里走了出来,拿出一个信封交给维克多。维克多打开了信封,点了点钱,“下次还有活的话,你还可以再来。”老彼得又说。
“谢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维克多把信封塞进口袋里,收拾收拾东西,便离开了车房。一颗足球飞了过来,砸碎了车房的玻璃。老彼得捡起了足球,朝着车房对面的空地大吼大叫,把足球扔了回去。
“……哈尔滨新闻广播,FM 106.2,北京时间,8月22日早上10点……”
“……女士们先生们,开往绥芬河的列车即将发出……”
维克多先是把鱼肉罐头工厂的卡车开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又从哈巴罗夫斯克过境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是一座维克多来过很多次的中国城市。这个曾经受俄罗斯势力范围支配的中国城市,到现在为止城市的整体风格依然有着俄罗斯的味道,从传统到现代,从帝国到苏联,从市中心的东正教教堂到居民区里的筒子楼,甚至是从防空洞改建而来的地下商场和停车场,都是北方以北的人们带给这座中国城市的影响。现在的哈尔滨街道上开满了贩卖从黑河和满洲里运来的俄罗斯货物的商店,或许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里俄罗斯给这个中国边疆城市施加的影响;这里的广播电台和电视机都在直播北京奥运会的实况赛事,哈尔滨的市民们都沉浸在举办奥运的喜悦里——尽管仅仅三个月前,这个国家尚沉浸在四川地震带来的巨大伤痛之中,但伤痛已经被奥运会的盛大与宏伟盖了过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着奥运会的影子。
哈尔滨——哈尔滨。维克多并没有因为所在地的变化改变他原本懒洋洋的步调,相反,走在哈尔滨的大街上他反而觉得自己更轻松自然。曾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如果还有机会他想要再来中国。他想看看那些他没有完成而中国替他完成的东西。当然,中国是不愿意让他再访问中国,也不愿意他说中国替他完成了他想要完成的东西的。幽灵流浪在广阔的旧大陆的上空,它离开了欧洲,先是被赶出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然后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它跨过了东欧平原,跨过了乌拉尔山……或许在切尔诺贝利的水泥石棺里还封存了它的分身,但那终归是死的;只有在乌拉尔山以东,它还能像个僵尸一样存在。
维克多来到了一家手机数码产品批发市场。市场里面人来人往,里面不乏维克多的同胞,他们讲着和维克多一模一样的语言,与中国商人们进行攀谈。市场里出现了从香港走的iPhone 3G水货;手机市场仍然是诺基亚、摩托罗拉和索尼爱立信的半壁江山,当然,还有面向俄罗斯市场的三星。维克多穿梭在人群当中,白色和绿色的灯影反复投映在他的脸上,照亮了他的眼白,又黯淡了他的蓝色虹膜。维克多学着他的那些同胞,与柜台前的服务人员攀谈着。
到了中午时分,维克多吃完了午餐,便在批发市场周围的道路上闲逛。维克多最经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闲逛。他在街边小摊上买了一盒烤冷面,坐在街边的长椅上,看着哈尔滨的大街上的汽车和公交车。
维克多注意到了和他坐在同一个长椅上的人。他长着典型的亚洲人面孔;年龄是四五十岁上下,脸黑黑的,长满了皱纹,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穿着脏兮兮的工装和胶鞋。老工人也注意到了身旁的这个外国青年正在打量他,于是也同样看着维克多,与维克多四目相对。
维克多不懂什么中文,老工人很明显也不懂俄语。但是他们对视的几秒间,这两个陌生人似乎产生了什么共鸣,眼神仿佛成为了一种共通的语言。维克多从老工人的眼睛里读出了很多东西;他在老工人的眼神里读出了很多他自己说不出来的话语。就像尼采在意大利的都灵抱住那匹饱受虐待的老马哭泣一样,维克多也冒出了一种冲动,与老工人抱头痛哭,喊出那句“我苦难的兄弟啊!”;但维克多哭不出来。他不记得眼泪的味道,他不知道哭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而哭。
“开往莫斯科、新西伯利亚方向的001M号列车即将发出……”
维克多提着大包小包地回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几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也同样提着大包小包,走进车站,维克多认出了他们——他们正是之前维克多和瓦西里在达瓦里希酒吧消磨时光时那些坐在一旁开欢送会的国立大学学生。他们与维克多擦肩而过,维克多点燃了一支烟,来到站广场上,拿起公共电话打给瓦西里。挂上电话,他抽着烟,看着写着“卡尔·马克思大街”和“列宁路”字样的路牌,以及车站对面的列宁铜像。
铜像是一九三零年落成的;和维克多的爷爷差不多大。维克多想起很久以前说的爷爷可以去中国养老的话。远处的铜像,列宁伸出一只手来,指向东方,伸向维克多;维克多仿佛听见铜像在对他说话,但不知道铜像在说什么。
“老家伙,真有你的。”维克多对列宁说。
“……希望你们回国后,让这种精神生生不息、世代永存。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现在,遵照惯例,我宣布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并号召全世界青年四年后在伦敦举办的第3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聚。谢谢大家!”
现代小轿车里,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声音从北京通过调频102.1的俄罗斯之声符城广播的无线电波传来。
“奥运会这就结束了。”瓦西里说,“这辆车我也联系到了商家,很快就卖了。”
“是么?好吧。”维克多说,“我这后面还有大包小包的,你看看路子把它们都卖了吧。”
“我大后天就走。去莫斯科的车票已经买好了。”
“那,祝你一路顺风。有空回来看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您。”满洲里如是说。
“сука блять!”
符拉迪沃斯托克下起了雨——这是2008年的8月末。夏天开始过去了。一辆汽车开过,路上水洼的水溅到了维克多的身上,他朝汽车骂了过去。维克多头上蒙着那件空军夹克,迅速地跑回自己的筒子楼。
回到家,脱下湿透了的衣服,煮上水。从中国回来后,维克多先是在家里睡了一整天,然后他也没有联系瓦西里。雨水拍打在公寓的窗户上,走廊里和列宁铜像上。
维克多光着膀子,看电视,喝茶。窗外的雨停了。维克多闭上了眼睛,仰卧在椅子上,脑海里浮现出自己穿着军装,行走在格鲁吉亚的大山里正在与敌军交战的样子。随后他站起身来,穿上衣服,下楼,站在列宁铜像前打量着列宁。
眼前的列宁伸出一只手来,伸向维克多。维克多抚摸着列宁的手——冰冷,粗糙,没有生机。如维克多所见,铜像,它只是一尊铜像而已。这样想着,维克多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和列宁对视着。他看着列宁,列宁也在看着他。
“怎么办?”维克多对铜像问道,“怎么办?”
铜像没有回复。
维克多搞不清楚铜像的动作的含义。它是在呼召,还是在求救?那只饱经风霜的手,从昔日领袖的地方伸向维克多,渴望着从二十世纪初与二十一世纪的维克多进行一次对话——但它没有变化,维克多能听到的,只有雨滴从屋檐上落下的滴答声。
这个曾经说要解放全世界的男人,如今却被困在一尊铜像里面,动弹不得,伸出手来向维克多呼救,却只能如此沉默。整个独立国家联合体里分布着各种各样,各种大小的列宁铜像,星罗棋布,对各地的人们伸出他的手,大步迈进。在过去看着他,好像他就从1918年走向未来的年代,伸出手来,在呼召着铜像之下的人们,正在发表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维克多一闭眼,仿佛就能听到《什么是苏维埃政权》的具体文段;如今这些雕像都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它们的表面不再锃亮,已经锈迹斑斑,被腐蚀得坑坑洼洼,现在它伸出手来,是在向所有人求救。如今它已经身处列宁曾伸出手指向的未来,却是如此落魄,似乎落后于这个未来,只能成为过往时代的见证者,成为人类历史的见证者。即使未来人类灭亡,这些雕像仍然存在,会告诉未来的文明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列宁的墓位于莫斯科红场上。他本人的遗体也被防腐处理,供人展览参观。遗体也变成了铜像。维克多不曾去过莫斯科,他只通过照片了解过莫斯科是什么样的。莫斯科——一座曾经被称为“世界革命之都”的城市,如今人们谈起它,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圣瓦西里大教堂的画面多过那些重工业设计风的大厦。或许,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体进行防腐处理,会起到让人前来参观瞻仰的意义,尽管这样做与他本人的精神相悖;而如今连这样的意义都没有了,列宁墓变成了一个商业旅游的景点,而他的遗体与动物园里的猴子具有相同的命运。
梦想枯竭了。警察代替了海盗,侦查代替了冒险。
“去莫斯科。”一个微弱的声音传入维克多的意识。
“什么?”维克多问铜像。他看了看周围,周围只有他一个人。
“去莫斯科。”那个声音对他说。
“你要我去莫斯科么?”维克多问眼前的列宁。列宁没有动口,维克多握住它的手,一如既往地冰冷,没有变化。
“去莫斯科找。”那个小小的声音说。
“我凭什么相信你?我为什么要去?”维克多问。
“去莫斯科找。总会找到的。”声音说。
“去找什么?找你么?找你的遗体么?”维克多问。
“去莫斯科找。总会找到的。”声音又说。
“你最终还是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去莫斯科。”维克多说。
“去那里找,总会找到的。”声音说,“去把它找回来,总会找到的。”
“为什么是我?”维克多问。
“你想去,难道不是么?”声音说,“你已经失望透了。你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该怎么找?”维克多问。
“去那里就好了,你总会找到的。”
“好吧,你说服我了。”维克多对列宁说,“那我就去验证一下吧。”
维克多上楼去,打了个电话给瓦西里。没有人接。他又拿好自己的东西,走出筒子楼,跑向巴士车站乘车。
“我决定了,”维克多对瓦西里说,“我也去莫斯科。”
“噢,那很好啊。”瓦西里说,“那现在去买车票吧。”
“俄罗斯”号特快列车飞驰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轨上,向西面开去。可能维克多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选择去莫斯科,去那里要寻找什么——但去就是了。或许在莫斯科会一无所获,但既然那个声音——那个贯穿了加里宁格勒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国境的声音,穿越了无数时间的声音,那个遥远的声音,激起了维克多对远行的渴望,决定去一万公里外的莫斯科找回一些什么——顺便探望一下列宁。就这样,列车向前开去,抛下了东方冻土,没有停歇。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滨之声’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大彼得罗夫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的,《时间,前进!》。”
2020.4.26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