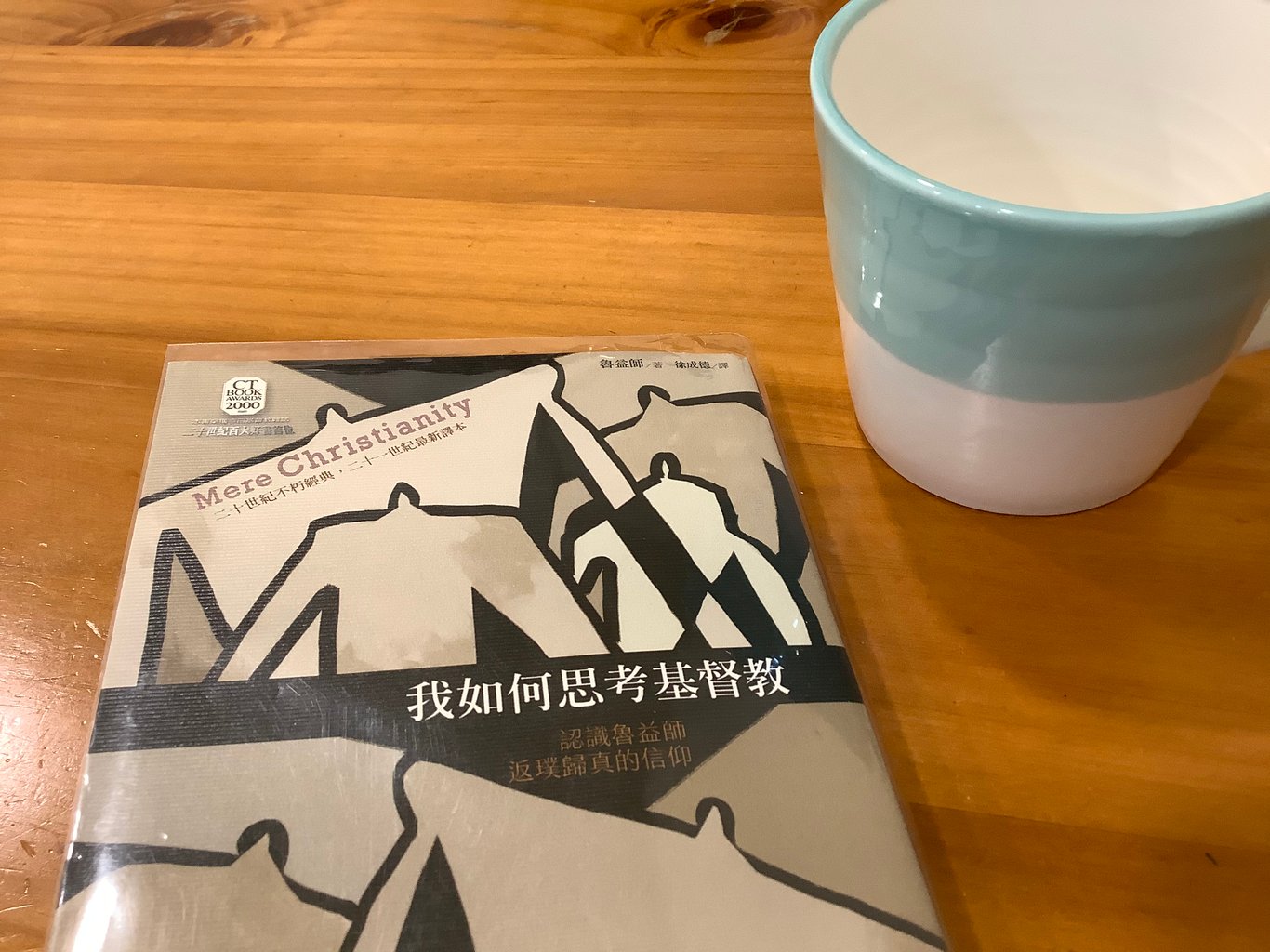
喜歡文字、思考、咖啡、旅行、電影⋯⋯
十七世紀一個荷蘭士兵與平埔族女孩的愛情故事(二)
「所以你會殺了我嗎?」
范勃亨想起那天他從瑯橋回到新港社,趕回去見Tagutel時,她對他所說的話。
從瑯橋到新港社途中,他幾乎沒有停下來休息,在聽到消息以後,心裡似乎無法產生別的想法,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想見到Tagutel。
心裡對她的想念,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熾烈。
他無法分出心思去思索尤紐斯牧師派人傳訊息告訴他的事:Tagutel出軌了,她的情人是平埔族青年Packoy。這個消息無法在他腦海裡產生真實的意義。他滿腦子都被一件事佔據。那就是Tagutel的臉。他迫切渴望再次地見到她。
回到Tagutel的家,這是結婚後他為她新蓋的,所有的建材都選擇最好的。他希望她所有的一切都能用最好的,因為他知道她值得。這是他一直想告訴她,卻無法說出口的一句話。那些沒有表達出的情意都化為昂貴的禮物。但是他知道禮物不會說話,那些情感仍舊被關閉在他的心裡,一如既往地哽住在喉頭。他突然發現,自己一心地趕路,那麼渴望見到她,就是希望能說出那些未能被說出口的話語。在一切都太遲以前。
但是他渴望的那張臉孔,在見到他時,所說出的第一句話卻是:「所以你會殺了我嗎?」
他愣住了,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隔了許久才緩緩地搖搖頭。她為什麼覺得他會殺了她?
她看起來似乎鬆了一口氣。「我以為你們荷蘭人會殺死出軌的妻子。」
在這句話哩,深深刺痛范勃亨心的,是她說「你們荷蘭人」這句話。後來他用很多很多的酒,都無法填補這句話在他心裡挖出的空洞。他是她的丈夫,但是對她來說,他只是那個「你們荷蘭人」。
可是他也知道,這不能完全責怪Tagutel,荷蘭人在福爾摩沙殺了許多原住民。而他是其中的幫兇之一。新港社人愛他,接納他做他們的一份子。他們稱他為[弟兄]。大肚社的頭目不知道為什麼對他信賴有加,指定要他做接待,才肯從大肚到大員來參加地方會議。他們把他視作他們當中的一份子,但是他心裡知道,他是為壓迫者工作的。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地區貿易的獲益而工作。就連他與當地土著的婚姻也是其中計畫的一部份,為了得到當地人的信任。
所以Tagutel也是這樣以為的嗎?他是為了政治的目的才和她結婚?因為她是一個孤女,容易教化,就和那些無依無靠的小琉球女孩一樣?
在那時他才發現,在他的心裡,深深地渴望Tagutel對他的理解。他希望她能理解他對她的愛,能夠理解在殖民者與殖民地人民之間,他內心的掙扎,理解他心裡那個同樣漂流的孤兒。
離婚後有一次和他的上司尤紐斯劇烈的爭吵,是為了新港社人Kava和Valutoch的案件。尤紐斯指定范勃亨和他共同審理這起離婚案件。即使幾個月前他才剛經歷過被背叛及離婚的痛苦,牧師卻刻意地讓他參與在Kava和Valutoch的案件審理中,這令范勃亨感到相當痛苦。
他沒有把內心被攪動的情緒表現出來,表面上,他仍然是那個盡忠職守的探訪傳道,扮演著在Kava和Valutoch案件當中,中立的審判者角色,但是一部分的他跟著當事人的陳述、情緒,一再被拉扯回三角關係的痛苦糾葛中。
Kava指控妻子Valutoch和青年Sampa有婚外情,要求取回所有給妻子的財產。尤紐斯認為為了嚴厲處罰不忠的Valutoch,除了鞭刑之外,還要沒收Valutoch的全部家產,以示懲尤。審判中尤紐斯有意無意的總是把眼光撇向范勃亨,似乎無聲地在指責他對Tagutel的罪刑太過寬容的態度。
案件宣判之前,范勃亨喝了酒,拜訪了牧師館裡的尤紐斯。尤紐斯似乎已經就寢,穿著睡衣出來應門時,看起來吃驚而不快。是的,他一定沒想到他居然會有這個膽量反抗他這個上司。他一直是那個溫和有禮的范勃亨,但是此刻的他滿身酒氣,粗魯的要求尤紐斯更改他的判決。指責他的判決太過嚴厲、不恰當。他記得尤紐斯站在門口,身體往後挪了幾步,臉上露出避開什麼骯髒東西的表情。
「范勃亨,你喝醉了?你喝了多少酒?你難道不知道醉酒是.........」
是罪惡。
從牧師的表情,他羞愧地看見自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罪人。白天的他是可靠正直的政務官員,夜晚沒有人看見的屋內,他只是一個沉溺放縱的酒鬼。
「我只是說.........這樣的判決,會不會太過嚴厲了?」他的氣勢弱了下來。
「范勃亨,我對你非常失望,判決已經確定了,現在請你立刻回去睡覺,丟掉那些可惡的酒,不要再墮落了!」
門砰的關上了,范勃亨在那裏注視著關閉的門,恍然若失,頹喪地坐在庭院內的泥土地上,隔壁的教堂裡還有微弱的燭光。
「范勃亨」心裡有一個熟悉的聲音。
不是他記憶裡父親或母親的聲音,他太早就離開父母,離鄉背井討生活。這個聲音比他對那模糊不清的故鄉但澤都令他感覺到親近、熟悉。這是他所信仰的,那一位曾經為罪人上十字架的神,會在心裡呼喚他的聲音。
這個聲音令他想哭,因為他想起自己在離婚後,就不願意再對神禱告。被背叛,被丟棄的痛苦,讓他不自覺地想逃離神,就像他用酒精企圖想逃離自己一樣。
「對不起.........」如果他真的可以和這位神說話,這是他會想要說的。
他並不常讀聖經,此刻心裡卻浮現在教堂裡聽過的聖經上的一段故事;宗教人士帶著一個行淫被抓到的女人到耶穌面前,故意問他說:「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怎麼處置她呢?」他們說這句話是為了試探耶穌,找機會控告他。
耶穌彎下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然後又彎下腰,用指頭在地上寫字。那些人聽到這句話,悄然無聲地,從老到少,一個一個離開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個行淫的女人,仍然在那裏。耶穌抬起頭,問說:「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妳的罪嗎?」她說:「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范勃亨從泥土地上站起來,離開了牧師館。那天他感到自己再一次經歷了赦免,就像第一次在教堂受洗的時候。在法庭上,他並不是那個審判的人。「我把審判的權利交給祢。」他輕聲、堅定地,對心裡那個熟悉的聲音說。
在河邊遇到Tagutel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已經原諒她了。Tagutel從水裡上來,看起來就像他第一次愛上她時那麼美。他想起一首歌,試著學當地的居民那樣唱給他所愛的女孩聽。「我妹子,我新婦,你奪了我的心。
你用眼一看,奪了我的心。
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求你將我放在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
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她跟著他唱。因為他們一起在教堂裡聽過這首歌,卻不能明白其意思。Tagutel和其他新港社人一樣,受洗,上教會,成為基督徒,但她卻不能說自己認識這一位神。也不明白祂與尪姨所召喚的神明有什麼不同。有時候她十分懷念小時候,在來到新港社以前,那些熱鬧、奇異的異教儀式,看著尪姨裸身爬上公廨屋頂,不停大叫、呼喊和跳舞,有時候真的比聽尤紐斯牧師那些艱深難懂的講道要有趣的多。有時候他們還是會偷偷向尪姨求問天氣、收成,在路上擺放祭神的物品,只是如果被牧師發現的話,這些祭物一定會被踢掉。
但是此時,范勃亨所唱的歌令她深受感動,熱淚盈眶。這一位她並不真正認識的神,荷蘭人的神,她希望也能夠是她的神。她想要認識祂。
(待續)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