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诞生于这个大时代,反对一切压迫和宰制的青年平台。关注思想交锋、社会运动,关心工人、农民、女性、全球南方等被损害者的真实处境,也通过写作和实践去想象、去创造别样的社会。网站:masseshere.com
“乘风破浪的姐姐”:“下海”的东北女人

文|在长影吃烤冷面的木翮
二十世纪90年代,东北某城市,丽娜做好了晚饭给一家人吃,但她和丈夫似乎都少有胃口,食难下咽。夫妻二人已经从国企下岗多时,日子一天天地捱下去,一直没有着落:整个东北都在精简队伍,重找工作难上加难,打零工也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从头开始做个体户却苦于没有本金。丽娜回忆起白天去人才市场听到的,如果能到法国给华人家庭做保姆,工资将十分可观。她劝动丈夫接受了这个提议。二人借了不少高利贷,终于把丽娜送上了去往法国的路。
不料,法国华人家庭付给保姆的薪资实在过低,远远少于丽娜的期望,无法偿还家里欠下的高利贷。硬着头皮干了几个月,还要经受雇主的克扣和冷眼。失望的丽娜在中餐馆里遇到了东北老乡,在她的帮助下暂时住进了“站街女”的廉价集体公寓。久而久之,走投无路的丽娜也学着老乡,瞒着家人,走上街头,开始“下海”。
这是上映于2017年的电影《下海》的前半部分,已经可以看出,电影在鲜少有人碰触的东北女工历史话题下,又包裹着更为敏感的女性性工作者主题,聚焦重重时代暗影。
女工的“堕落”:历史的债务
电影虽然主要仅仅聚焦一位主人公的“下海”经历与心理,但整个叙述脉络可以说遵循着时代的总体逻辑。9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浪潮中,经商主义和消费主义快速崛起,与其说此过程是利用市场化改革与全球化进程促进社会建设、生产力革新,不如说更多显现为是一场借重权力和跨国资本而进行的社会财富分配的过程。国有企业的转轨使得国家资产可以快速转变为企业资本甚至是个人资本。于此基础上,在市场同质化竞争愈发严峻、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热潮也已不复存在的90年代,没有掌握厂内民主权利的国企工人从生产的主人变为生产的“累赘”,走向下岗或彻底失业的结局,构成了新时期贫穷阶层的一个重要部分。东北作为工业重镇地区,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失业现象尤为突出。《下海》的故事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

对于电影中的主人公和其他更多历史的亲历者来说,失去社会保障系统的庇护,从在城市中当家做主的工人沦为“游民”、“弃民”,在贫富开始急剧分化的时代挣扎,这是一切“堕落”的节点。下岗工人很多会选择进入服务行业打零工,接受劳动力市场边缘的残羹剩饭。女性就更是这样,她们很多选择成为餐厅、歌厅的服务员或者保姆,忍受着低工资、无福利、不合理的体力劳动安排和低社会声望。转而“选择”成为“小姐”,是在某些生活困难依然存在的基础上,再次牺牲掉一部分社会声望来谋求经济收入的增长。如影片中的主人公丽娜,在国内无处谋生,一家老小需要养活,寄望于出国寻求生机。可到了“遍地黄金”的巴黎,她又发现底层女性劳动者的际遇和东北如出一辙,甚至还不如后者。低声下气地做了一段时间廉价保姆后,丽娜甚至还游荡在街头,求一些小店老板打赏一份工作。除此之外,她还要忍受对于东北人“头脑简单”、“又懒又贪”的污名。种种这般,下岗女工们很可能早已在中国,在东北经历了无数次。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性,一再被侮辱、打压和剥夺。在异国他乡迈出“下海”的最后一步,虽然也有过挣扎和煎熬,但说到底也不足为奇。
黄盈盈等性社会学研究者在二十一世纪初针对东北地区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失业之前,她们绝大多数都是国企的熟练工人,由于单位改制而被迫下岗。成为性工作者之前,下岗女工经历的最后三次职业,社会地位往往离“做小姐”的地位越来越近。对她们而言,成为性工作者后如果能得到较高一点的经济收入、更灵活的个人时间安排已经是非常吸引人的“福利”了。整体上来看,她们在下海的最后关头只不过是踏出了职业平移的一小步,而非如大众经常构想的那样是一次根本性的“堕落”。被逐出城市主人翁队伍的那一天起,她们就已经失去了进入劳动力中心地带的权利与可能性,那次的冲击远比后来的一切都要强烈。
“下海”的困境
很多女工流动成为性工作者之后,是希望攒到家里做生意的钱,或者孩子上学的钱就上岸不干。性工作是女性最古老,也最无奈的以零工方式贴补家用的职业。在不断资本主义化的历史阶段,中国只能依靠内部对内部的征用、索取和剥削来达成初步的积累,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如是,新兴产业对旧产业如是,新富阶层对工人阶级如是,家庭对女人的生产劳动、性劳动和情感劳动的征用,也如是。象征着“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经久不绝地在女人身体上重演。
男权社会惯于用“良女/娼妓”对女性进行划分,同时进行无罪或有罪的判定。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顺从性别结构所允许的性供求关系。“良女”在婚姻中供给性服务进行利益交换,是被默许的;而“娼妓”(被迫)出售情欲,是对性供求关系与规则的破坏,需要进行“道德谴责”。本质上,无论良女还是娼妓都无法真正主导自己的性权力和身体,社会文化与制度总有办法压缩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女性空间,使得女性必然或多或少地作为“性资源”而存在。从这个方面来看,性工作者的生存经验就是社会性别文化的一面镜子;她们的案例,是把普遍的女性生存状况以最极端的状况展现出来。
比如,在失业-再就业的过渡期提供性服务获得资金,性工作者的身体面临着各种安全风险。影片中,一位客人强行对丽娜的身体进行手机摄录,被拒绝后一怒之下对丽娜进行施暴。除此之外,性病、怀孕风险等也是性工作与生活中随时浮现的难题。这些难题不是简单地呼吁取缔性服务,用行政手段“扫除”性工作此种职业便可迎刃而解的。首先,依赖行政手段“扫黄”所带有的视角根本不是女性或者女性主义的视角。性工作者被漠视为好逸恶劳或偶然“失足”“失德”之人,性工作被冠以“捷径”的名号,性劳动市场被视为是一切道德堕落之源。在这种修辞下,性工作者被视为秩序的破坏者,背上社会推诿过来的沉重包袱,只能被动地等待管制。这样的管制肯定不会首先顾及到女性性工作者的急迫安全需求。其次,执法的力量甚至可能反过来会进一步恶化她们的境况。比如,过分严厉的执法行动与过量的媒体曝光会加速性工作者的流动,增加她们遇到暴力的风险;把安全用品作为卖淫的证据,会使得性病传染的几率增加,等等。
或许,承认职业存在的社会背景,减少急功近利的缺少女性视角的行政手段,在实践上尽量为女性性工作者争取社会权益,争取性工作的非罪化等——能让女性性工作者变成解决自身安全难题真正主体的方法与措施,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她们面对的困境。提升工作的安全保障并不会如很多人担心的那样,会“引诱更多女性的堕落”。 如我们前面所提到,女性进入这个行业,已经是最后一次职业平移,以身处社会最边缘为代价获取阶段性的经济收入补偿,是退无可退的最后选项,而非所谓“向利益诱惑投降”的选择。更何况,缓解困境并不代表着我们永远接受市场化商品化的性交易的存在。仅仅是所谓性交易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我们追求的女性解放与身体解放的真正自由。
再谈“女工”:等一种真相
从失业到“再就业”,下岗女工丽娜的故事是根据导演在法国街头的真实目击改编而成。相隔二十多年的一场历史挖掘,让姗姗来迟的纪实影像撕开了一道质询过去的口子。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下岗”开始,失业的风险在两性间就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妇女通常首先遭受到失业的强震,女工“回家”往往是权衡利弊后“损失”最小的处理方法。官方宣传更是借重于为“下岗女工”化妆,替她们张嘴说话,把失业建构成女性独有的、偶然性的、不严重的经济阵痛,而非一场社会性的、无穷尽的掠夺。不仅女性的下岗问题在匆忙掩盖下失声,社会性失业的巨大问题也在社会意识层面被尽量掩盖和弱化,这是意识形态宣传在为社会现实寻找解释的必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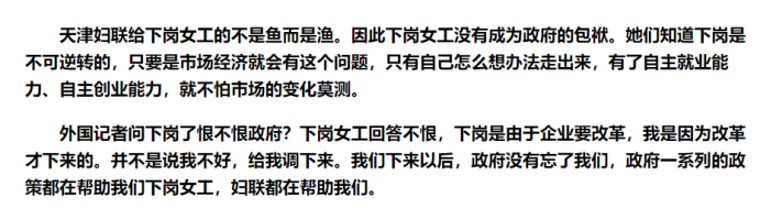
透过90年代对失业女工进行调查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女工的失业经常被包装成“待岗”二字。仿佛脱离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架构的女工,只不过是暂时退一步,随时有岗位供她选择。这种调研文章经常针对女性的心理状况指指点点,表扬那些奋发图强,有信心迎难而上的待业女工,而对“忧心忡忡”或者“满足现状”的女性则报以批评的态度。同时还要指出其“技术生疏”、“行动懒散”等“缺点”,这仿佛在暗示大众,女工的失业也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主要是女性的)个人职业问题或道德问题在社会改革的催化下显露出来了,而改革的大刀阔斧正好在此期间纠正或剔除这些不良因素。甚至被迫回归家庭的“贤妻良母”还要被单独拎出来予以敲打,指摘她们过于“依赖丈夫”、“游手好闲”。女性失业者的问题不仅要女性和家庭自己消化,女性本身还被不断“激励”,要适应市场学一门手艺,以便再度被征召回零工市场,成为廉价的后备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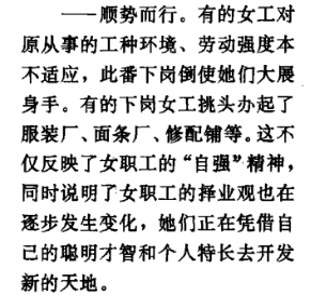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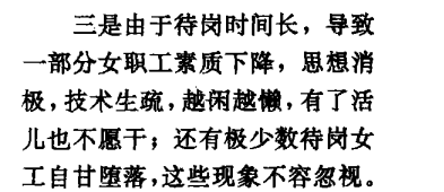
除此以外,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更是不乏对于在失业潮中“乘风破浪”的女企业家故事的宣传。一方面继承了把女工经历渲染成个人色彩浓厚的故事的传统,借重道德规范论述以转移视线,逃避追问;另一方面还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下“白手起家”、“大胆创新”的个人神话。只不过到最近几年,社会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这样宣扬“个人素质”与创业奇迹的故事,已不再如过去那样有效。
如果真正看向更为直接、具体、未经加工的故事,看向最为边缘的大批失业女工,她们的历史境况就是对二十多年来置换真相的话语的绝佳讽刺。她们回家,并不是主动“选择”成为全职太太,那是新富阶层中产阶层的特权;她们出国亦或留在家乡“下海”,也不是改革开放自力更生的奇迹的展演,那是一小部分人才享有的政策红利。如果说唱出“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词是国家最后一次召唤男性工人的阶级力量,让工人忍辱负重,为改制让路;那么,女性失业工人所经历的,很有可能是唱也难以唱出,甚至说也难以说出的牺牲方式。
丽娜挣到的本钱足以让夫妻二人开一间小店做生意,维持生活,但是几经波折下丈夫还是知道了丽娜工作的一切,羞愤难当。一轮争吵、分居之后,丽娜在偏僻的旅馆找到了丈夫。尽管始终沉默相对,二人终于又能在一起做饭。最后,丽娜问丈夫有蒜吗,丈夫还是不说话,抬起下巴指了一下。
——算了吧。
参考资料
黄盈盈,潘绥铭 “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 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黄盈盈 “ ‘结构-关系-主体’框架下的艾滋病预防–扩展‘疾病’的社会学想象.”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47, no. 2.
李晶 “下岗女工如何应对就业难问题.” 边疆经济与文化, no. 2, 2010.
魏漫江 “媒介中的阶级与性别——对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杂志‘下岗女工’报道的分析.” 新闻知识, no. 2, 2010.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多数派正在派送中

诞生于这个大时代,反对一切压迫和宰制的青年平台。关注思想交锋、社会运动,关心工人、农民、女性、全球南方等被损害者的真实处境。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