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丟掉書本上街去
閔恩仇
閔恩仇一刻也沒有喜歡過自己的名字,也許有過,但那也是非常久遠的幼時記憶了。 那個時候他並不理解這三個字所代表的能指與所指,所以應該算不上喜歡。 人可以對不能理解的事物懷有喜歡的情緒嗎? 人類對於自己無法理解的事物只有朦朧的恐懼罷了。 閔恩仇不喜歡自己的名字,不僅是因為這三個字順口的讀音——雙唇合攏緊貼然後向內抿住,接著微張,下壓喉頭的軟肉一邊震動鼻腔,最後併攏雙排牙齒,舌尖輕點上牙:閔-恩-仇。 更是因為這三個字對於任何中文使用者來說,都包含了過分確定的含義,雖說浪漫不一定源於不確定性,但確定性則向來具有排他性。 閔恩仇討厭不容置疑的確定性,也順便厭惡生活中積重難返的一切。
閔恩仇直到不再開口說話前,仍不斷跟所有人都說自己記得出生時的場景,言之鑿鑿。 那是融有太陽的大海般的永恆,從那一刻起,即使黑夜孤寂白晝如焚,他也從未停止用自己永恆的靈魂凝視這個世界。 靈魂永恆,文學永恆,他總要這麼補充一句。 大家總是被他的真誠打動,從來沒有人質疑過永恆算不算一種確定性。 真誠是閔恩仇誕生前便印刻在骨子裡的性格優勢。 當年幫助閔恩仇降生的婦產科醫生陳大夫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不小心透露,閔恩仇就算記得自己出生的場景,那也應該是慘白的手術燈和縈繞的消毒水味。
閔恩仇的成長之路似乎早已確定,至少他的父母是這麼覺得的。 閔恩仇出生於1952年,祖輩世代居住在東部沿海的漁村,父親是當地遠近聞名的捕魚好手,五十二歲時還能徒手扛起一百多斤的海鱸魚,一家五口人,父親母親加上兩位妹妹,除了他都以打漁為生。 約莫兩歲,閔恩仇第一次見到了海上日出,並非沙灘椰樹,而是碣石狂風,太陽從海面裂出,橘紅色的光猛烈晃動著天際,這夢幻般的場景給他終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不妨這麼理解:血肉成型后,是太陽與海給了閔恩仇第二次誕生的實感。

從童年到大學,閔恩仇生活上都是傑·蓋茨比某種不穩定變體式的人物。 從很早開始他便不幹農活了(為此沒少吃父親皮帶的鞭笞,但父親打得越狠,他嘴抿得越緊),每天堅持抄一頁新華字典並堅持不說方言,跑步,每周游兩次海泳。 到了大學報導那天,他已經擁有了連古天樂都羡慕的黝黑膚色和健碩的身體。 正當父親正準備將自己半生的技藝傾囊相授,當一些有見識的村裡人以為他考上的是體育專業時,錄取通知書發放後大家才愕然發現,閔恩仇成了某個遙遠南方城市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開始自己追逐靈魂與文學雙重永恆的坎坷道路。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閔恩仇都是廣州詩人團體白雲詩社的中堅力量。 1979年創作的《鬼臾》是一部充滿超現實注意夢境的具有個人自傳氣質的先鋒長詩,詩中主要講述了一位名為郭羽的青年被天神邀請去天上一遊,前提是自己自願放棄肉身,也可能是這名青年因故 去世了,接著被死神帶去遊覽什麼地方,但這隻是表面上的故事,其實仔細品味就會發現,詩中還包含一條暗線:上述郭羽的故事其實來自一位叫鬼臾的盲眼說書人,這部分解釋了說書人的生平經歷,如何在塵世掙扎。 同為白雲詩社的成員(二人並未同時存在社中),廣東省作家協會的文學評論家的劉大有指出,這位盲眼說書人就是閔恩仇的一個化身。 部分研究者甚至認為,這首詩實際上成為了中國朦朧詩的發端。
《鬼臾》在詩壇獲得巨大讚譽,閔恩仇嘗到甜頭后卻迅速轉向現實主義。 他先後使用不同題材創作了若干反映現實生活的詩作,如關注當代青年人身份認同焦慮的《再會》,詩中"莫對答案視而不見,即使痛苦輾轉浮現"一句一時間膾炙人口;還有質疑文學是否能讓人變得更好的組詩《如果你今天沒有痊癒》。
1986年作為南方地區的優秀詩人受邀參加北京市作協在昌平舉辦的「新詩潮研討會」,同時參加會議的還有舒婷、北島和顧城。 就當詩人同僚們都一致認為他無疑將成為詩壇先鋒、文壇之路一帆風順之時,閔恩仇在那場關於新詩潮的討論之後卻毅然決然地宣佈退出詩壇,並要求曾刊登自己作品的雜誌及報社等永久銷毀作品。 曾有人懷疑他受到了天才詩人們的刺激或是北方文壇的排擠,但沒有可靠信源,也大都語焉不詳。 文壇並沒有惋惜太長時間,很快閔恩仇便作為小說家重返公眾視野。
1990年,歷時五年創作的長篇小說《關於解放西路在7月3 號到8月20號發生的一切》橫空出世,這部被認為是向《尤利西斯》成功致敬、文學基因傳承自《項狄傳》的作品,將閔恩仇立刻推向文壇高處,就連他自己在接受廣州日報的專欄採訪時也表示,"雖然是第一部小說,但你認為這是我的最後一部(作品)也是正確的"。 正如標題所顯示的,小說集中描寫了一座虛構沿海城市島城解放西路四戶人家在7月3日至8月20日短短48天內發生的事情,閔恩仇採取了全景式描寫的策略,讓四條主線並行又相互交織,最終構成一幅龐雜的生活拼圖。 雖然這部作品叫好不叫座,但依然有出版社表示願意和閔恩仇簽約接下來的作品,可就在這時閔恩仇再次莫名擱筆。
1995年12月,閔恩仇在廣州日報上發表了悼念亡父的文章《奔騰的第二條岸》,文中提到自己退出詩壇的歲月,說起自己與從青年時期就開始無休止爭執的父親終究因他的病逝而達成無可奈何的和解,又談到自己儘管不再寫詩卻不甘心放棄文學創作,似乎在暗示自己希望重返文壇。 人們從字裡行間中尋找蛛絲馬跡后發現,閔恩仇父親和兩位妹妹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一直保受一種家庭遺傳性精神疾病的侵擾,嚴重時無法正常生活,而父親終於在95年年初得到解脫,結果是巨額的醫療費和兩位妹妹的生活費用成為了閔恩仇無法擺脫的噩夢。 一度人們在各種劣質產品的廣告上看見閔恩仇的身影,作用杯水車薪,甚至險些讓自己背上官司。

接下來,在千禧年前後,有幾本明顯是拼湊而成的半成品短篇小說集和過分偏激的文學評論集陸續出版,有明顯的趕工痕跡,編輯也沒有顯示出足夠的職業素養,錯別字和排版錯誤比比皆是。 文壇的變化實在太快,當初自己銷毀作品與頻繁擱筆的決定又讓近些年的讀者沒人知道他曾經的存在,所以自然而然銷量慘澹。 2002年,有閔恩仇的老同學在《萌芽》雜誌社任職,邀請他擔任該年度新概念作文大賽的評委和海選篩選的工作,或許是對年輕人的品味嗤之以鼻,也有可能是評委同仁對他沒有顯示出足夠的尊重,結果不歡而散。
年過半百的閔恩仇最終回到了故鄉,開始在中學擔任語文老師,迅速成為語文學科的備課組長和負責人,並常年負責高三的教學工作。
2007年,校長為幾名成績糟糕的學生開了後門,換來的是新校區壯觀的巴羅克式校門,當地知名書法家題字"凱旋門"。 一天傍晚放學時,來自海上的低壓氣旋席捲市內,學生們發現這座凱旋門似乎搖搖欲墜,沒等反應過來,大塊磚牆就落了下來,所幸沒有任何人員傷亡。 閔恩仇公開檢舉揭發失敗后,被同事目睹在校長室內大打出手,和校長與校長助理在地上扭打成一團,誰也不肯鬆手,或者說鬆口。 很快教學組組長換了人選,高三的課堂上也沒有出現過閔恩仇的身影。 校長在晨會上遺憾公佈,由於閔恩仇老師飽受家庭疾病之苦,健康情況不再適合高強度的教學工作,因此忍痛同意閔老師靜養一段時間。
不知何時學校里悄然多了一門叫做綜合藝術的,只為考試排名靠前班級開放的活動課,換句話說,課上的全是好學生。 任課的是一位對於上課紀律和作業要求(活動課按理說不該有什麼作業)比主課還嚴格的老師,他每天開始講一些上世紀文壇的細枝末節,以及自己如何通過飯後長距離散步而治癒了困擾自己多年的靜脈曲張。 這位老師有時會突然憤怒,用眼鏡盒反覆擊打講臺桌,在噪音中學生們艱難辨認出來,老師口中說的是諸如"好學生都是冷血動物,從不回校探望老師"之類的言論。 事實上,多年來只有少數幾位學生對這門課展示出了極大的熱忱,並按時上交作業。 有位叫林百夜的學生時不時會找他探討關於文學的入門問題,拿出的習作也總是深得其心。
退休后的閔恩仇在家中的車庫裡給一些有需要的學生做免費補習,習題是他自己用蠟版提前刻好印刷出來的,上課到亢奮時他會點上一根煙,更激動的時候他要取下假牙大口喝水。 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在網上從挖掘出文壇關於閔恩仇塵封的往事,結尾不外乎是推測他因窮困潦倒而死,偶爾有學生會為他闢謠,而閔恩仇聽說了總是一笑了之,畢竟他打心眼裡討厭不容置疑的確定性。 60歲生日那天他決定不再開口說一個字,長久以來,有一種無名的怒火始終在胸中無法宣洩,連他自己也無法確定這是在向誰抗議,是生活呢,抑或是向自己?68歲時閔恩仇在書房一角孤獨地去世,死因是腦卒中引起的急性休克,陪伴他的是身堆滿著的泛黃詩集和自己沒有賣掉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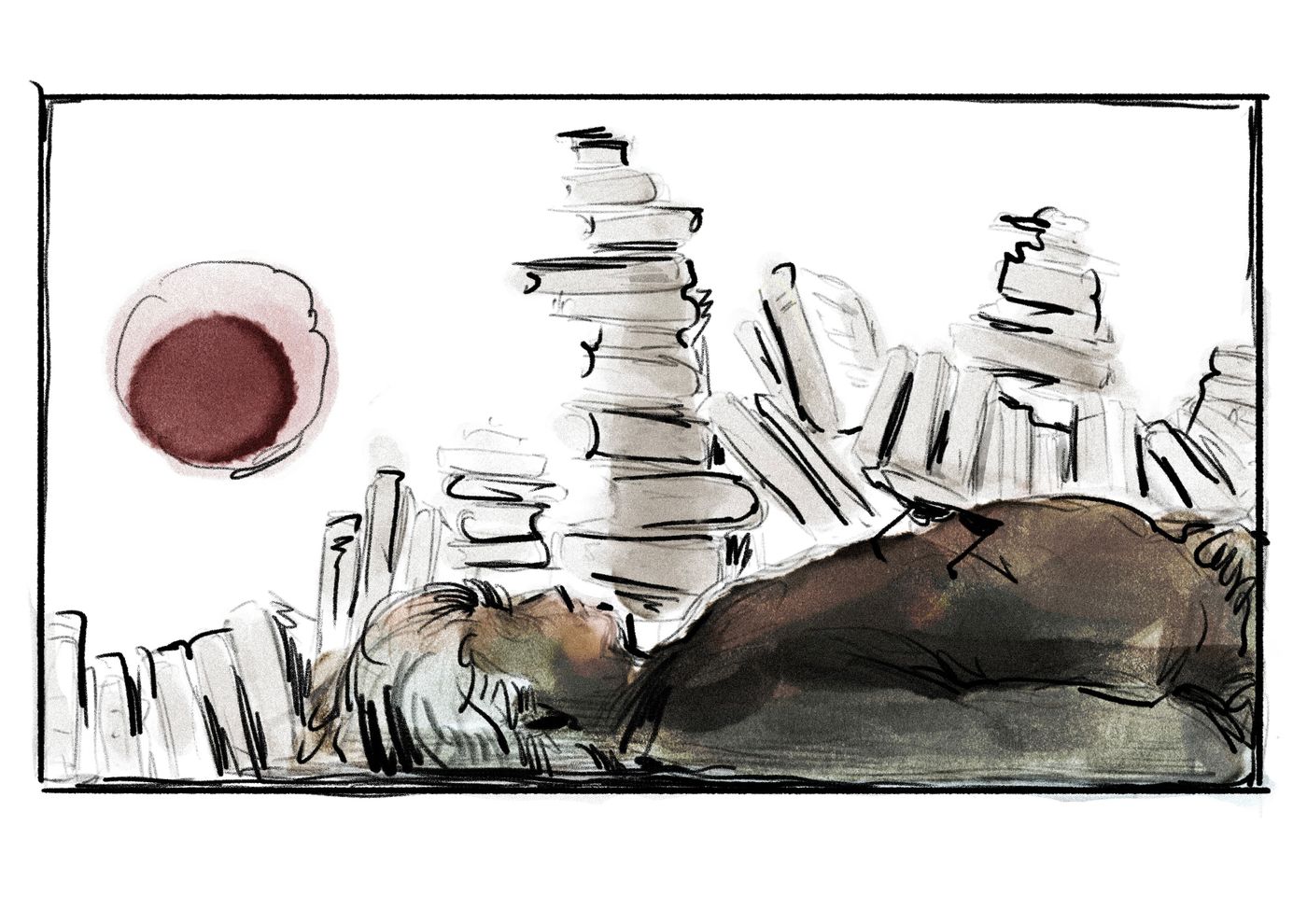
圖:乙己
本文涉及人物與情節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