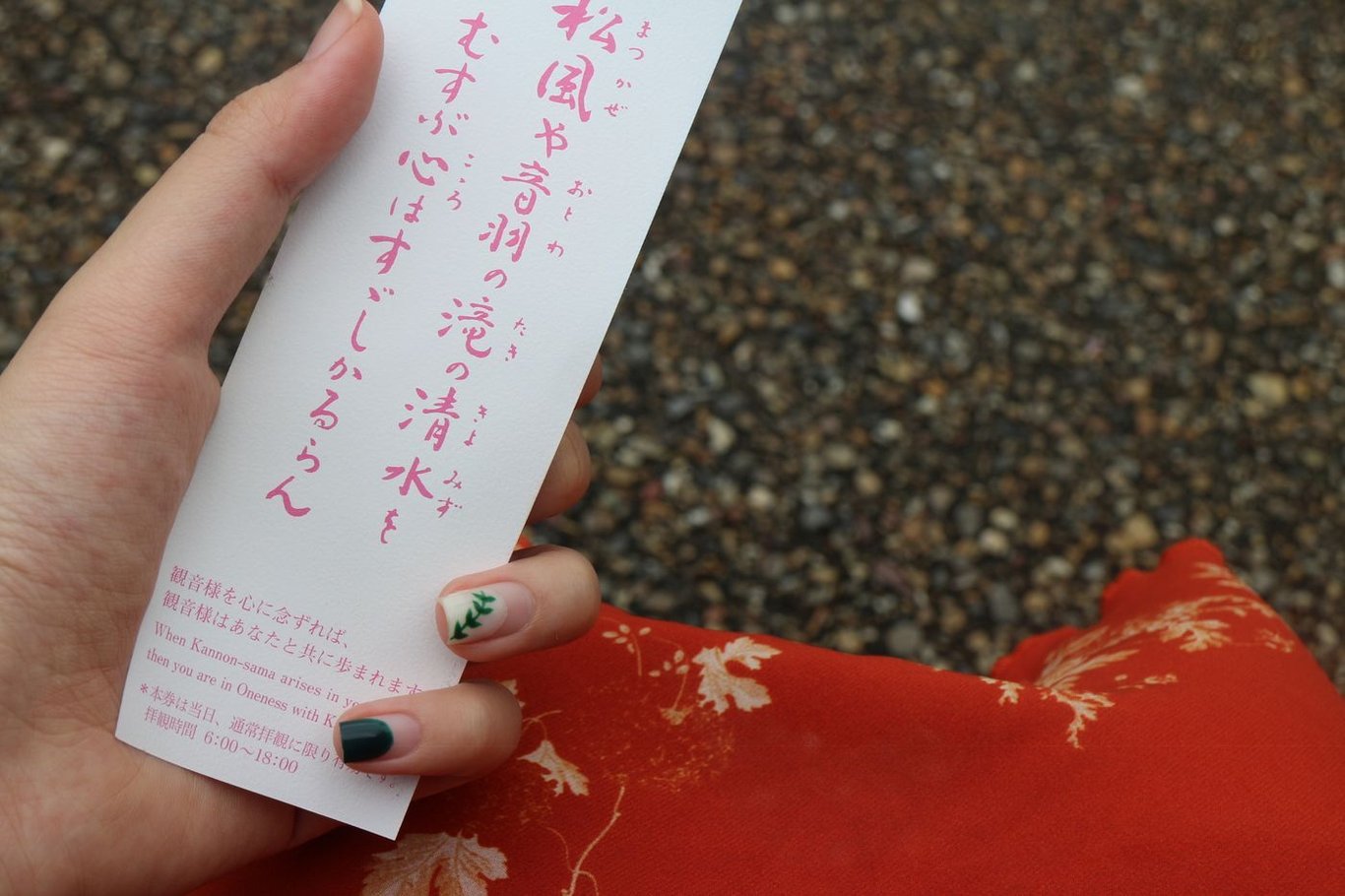
公共政策|中美关系|东亚文学|世界历史
台风与溺水者
小时候在家里等台风。妈妈“啪”地一声把门窗全关上之后,屋里好像桑拿室一样从地底缓缓升腾起一阵闷热。窗外还是风平浪静,手机里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橙色红色预警消息,颇有一种敌军压境,坐在帐幔里听四面楚歌的味道。
人们每年给台风抽签取名字,气象监测系统里的那团白色气旋像个初生的胚胎,在她母亲太平洋的子宫里缓缓向阴道挪动。比起名字,更为人瞩目的是它们按风力等级被贴上的标签。气象局的观察员报道起来像拎着新生儿过秤一般娴熟。
在五次三番探头探脑之后,在一阵长长的屏息之后,风终于像笨重的巨大引擎一般慢慢发动起来了。首先是蜻蜓点水一样掠过树梢,没有声音却把细细的枝掰扯成奇异的角度,然后是铺天盖地的一席风沙,雨在这时候斜斜地倒下来了。
我们爬到铁窗的第二格,津津有味望着外面,像在看旋转起泡沫做的雪花的玻璃音乐球,只是分不清到底谁在球里。小学老师打来给家长的停课通知早已成了愉悦的背景音。一切好像某种灾难美学。
不像在科技馆里看到的那些甜筒一样一圈圈卷到天际的热带风暴,台风更像是一个走到绝路的壮汉在往薄薄的玻璃窗上猛敲,好像打开一道小缝他就会奋力挤进来。若是感到受阻,就会马上撞上另一处。它要是有躯干一定会在各家阳台上碰得头破血流。
即使是见惯了台风的闽南人,只要是在风来时共处一室,总会油然生出一种对彼此的眷恋感。雨一下,屋里的避难者们就突然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有的检查浴室,有的去贴胶带,有的煮上囤好的泡面;谁都没忘了一边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然而风一歇,这种短暂的“社区感”倏然消逝,大家把门一开各干各的去了。
雨后的太阳像纤细的银针一样在卧室的窗沿边掉了一地。若是晚上,则有一大颗一大颗挂在草上的露珠,像宇宙里的星辰闪烁。此时一些关于这场灾害的坏消息才陆续传来:谁家的小孩偷跑出门在海里淹死了,然而只是众口相传,没有人说得清他们是谁。
想起那一天在室外游泳池里游泳,上岸的时候听说刚刚有个醉鬼在深水区淹死了。蓝莹莹的水和孩子们扑腾起的愉快的浪花,是落入我们眼中的美丽景象,在区区十米外的他人眼里却是生命的最后一幕。就像一阵台风刮过,我们爬上岸把身上的水珠擦干,他们的生命就像一片水雾一样凝结在窗玻璃上然后又迅速挥发了。
有时候想,溺水的人是不是像书里写的那样,一点点变回年轻的模样,跟着他们溺死的湖塘漂进大海,然后会乘着洋流环过世界,带着所有经过的鲜花和水草回来。
然而谁也没有再听过他们的消息。他们是确确实实死在了我们趴在窗板上看风景的那个台风天。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