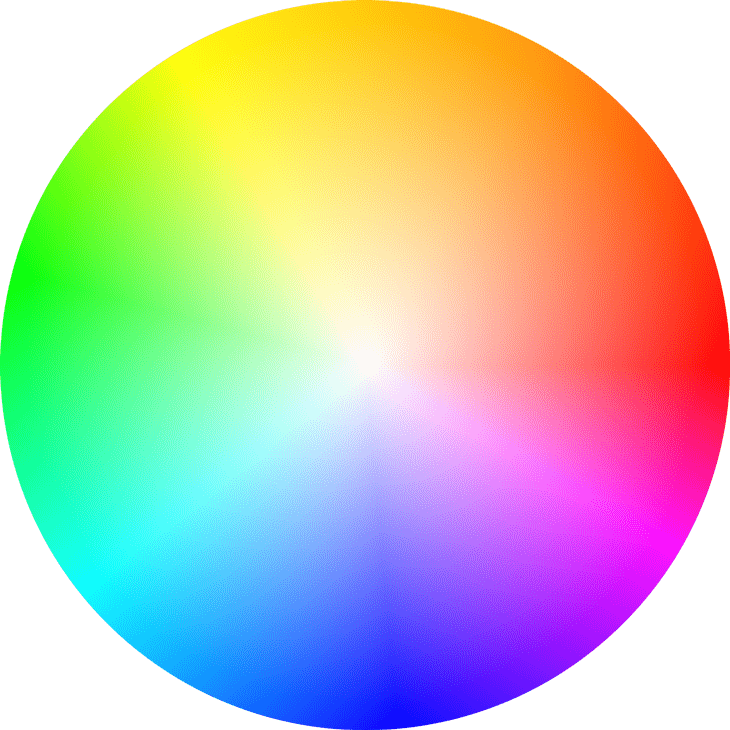
Coder, reader, runner, photographer.
书摘 |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活著活著,慢慢地活成了錢鍾書的樣子。這算是無奈還是智慧?有人評價錢鍾書只是記憶力好而已,沒有寫出很好的作品;要是活在今天的世界,記憶力就沒有多少價值了。錢先生不僅僅是記憶力好。
對於哈夫納 (Sebastian Haffner / Raimund Pretzel) 90年前的選擇,換成此時此地,我們能做出更好的選擇嗎?存在更好的選擇嗎?
關於第三帝國的書很多,以第一人稱當事人視角的回憶錄中,本書不可多得。更不可多得的,是作者的觀點。
非常感謝@Wu Ming 的推薦🙏。
哑谜
▪ 他虽然身为受害者,却没有做好太多反击的准备。他绝非天生的英雄或殉道者,而只是一个具有许多弱点的普通人,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危险时代的产物。但他不愿如此忍气吞声下去,于是走上了决斗之路——心中既无激情,甚至带着几分无奈,却默默有着绝不退让的决心。
▪ 凡出于善意而努力捍卫个人的和平与自由之德国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同时捍卫其他的事物,那就是世界的和平与自由。
一场国家大戏
▪ 每当纳粹报刊宣传真相的反面时,都十分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只要德国人不想被说成是因为卑下的进食欲而心生不满,那么他们就完全不敢再开口了。
“十一月革命”与德皇退位
▪ 我对和平已经缺乏正确的概念,却对“最后胜利”仍持有自己的看法——“最后胜利”便是战情快报所列出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胜利,有朝一日合并计算以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总账。... 它将是所有胜利报道令人难以置信的升华,以致让俘虏的人数、所征服的土地及缴获的物资完全相形失色。
▪ 如果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最后会导致战败,而真正的游戏规则却无法事先公布,非要等到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以后才会被披露出来,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和信赖心呢?我仿佛看见了万丈深渊,我的内心对生命出现了恐惧。
内战的“战火洗礼”
▪ 犹太裔的同学跑起步来,就跟我们其他人同样“反斯巴达克斯”、同样地爱国。有一位犹太人甚至还是我们当中的佼佼者。我敢对天发誓,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勾当。
卡普政变
▪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纵使政府要求他们向自己的平民同胞开枪,他们几乎也永远会服从这样的命令。但如果要他们起而反抗当局,那么他们就胆怯得跟兔子一样。反抗的念头才刚刚冒出来,他们就会像着魔似的,眼前立刻浮现一个枪决行刑队的恐怖景象。
拉特瑙部长遇刺身亡
▪ 短暂的拉特瑙时代所留下的余波,再度证实了1918年和1919年时的教训:凡是左派人士所进行的事情,都没有一样会获得成功。
群魔乱舞的1923年
▪ 1923年使德国濒临绝境,这不仅对纳粹有利,同时也为各种千奇百怪的冒险者带来了大好机会。
▪ 凡持有定期存款、抵押担保或其他投资理财形式的人,皆发现自己的钱财已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久以后,积存的小笔零用钱与巨额财富之间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差别:一切均已化为乌有。
▪ 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安全的岛屿,那就是股票。... 每个小公务员、每个公司职员、每个轮班工作的工人皆持有股票。每当需要支付日常开销的时候,他们便卖掉几张。到了领薪水的日子,人潮就拥进银行,股票行情于是如火箭般一飞冲天。
▪ 到处都有人兴致勃勃大谈恋爱,所以连爱情也沾染了通货膨胀的色彩。... 在那些日子里头学会谈情说爱的年轻人,都省略了浪漫情调,拥抱着没有繁文缛节的方式。
▪ 到了8月,美元汇率已冲至1比100万以上。... 在9月间,100万马克已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10亿”开始变成计价的单位。10月底的时候这又变成了“1兆”。
▪ 依据各家报纸的消息,慕尼黑有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家伙作风与之类似(在街头张贴宣传海报并举办群众集会,而且追随者众多 )。不过,希特勒的演说与前者不同,他以激情的方式发表卑劣言论,语气中充满威胁恫吓及赤裸裸的血腥暴力,其夸张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施特雷泽曼之猝逝——末日的开端
▪ 不过,有一件事情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也就是大约在二十岁的时候,爱情的经验和所选择的恋爱对象比其他任何时期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及性格。
严峻的布吕宁时代
▪ 一切有效的障碍物皆已被清除:宪法早就形同虚文、法律保障已不存在、没有了共和国…
我的父亲——普鲁士清教徒
▪ 无论是高高在上者,还是任其摆布的弱者,二者都只不过是人而已,并且都是同一部戏之中的角色。
▪ 真正对我产生保护作用的东西,那就是我的“鼻子”。我具有相当发达的精神上的嗅觉。换句话说,这种感觉可以根据美学上的价值(或者没有价值!),来判断别人在道德上及政治上的态度或观点。只可惜,大多数德国人完全缺乏这种能力。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有办法使用大量的抽象概念和演绎法来进行愚蠢的辩证,借此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好坏。可是,这往往只需要用鼻子一闻,就可以确定它是否发臭。那个时期,我已经养成了习惯,用鼻子(即感觉)来决定自己当时还为数不多的坚定信念。
国会大厦纵火案
▪ 凡事都可以看情况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解释,这就是政治,可不是吗,邻居先生?幸好我们对政治一窍不通。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危机已经解除,我们又可以放心蒙头睡大觉了。晚安。
▪ 每个人都对一个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那就是到底谁在国会大厦放了火,同时不止一个人对官方的说法不表苟同。然而却没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从此我们的电话交谈可以被窃听、信件可以被拆阅检查、书桌可以被外力强行打开,仿佛那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第三帝国”的诞生(1933年3月)
▪ 1933年3月总共带来四样东西,最后制造出坚不可摧的纳粹政权:恐怖措施、庆典和慷慨激昂的宣言、变节行为、集体崩溃——也就是千百万人同时发生了精神错乱的现象。
▪ 纳粹党徒则不然,他们从头到尾所表现出来的,不外乎一派谋杀者躲躲闪闪、惨白丑恶和欲盖弥彰的嘴脸。他们在系统地拷打及杀害手无寸铁者之际,却天天刻意摆出高贵的姿态和柔软的语调,声称任何人皆毫发无伤,而且从来就没有任何革命能够进行得如此人性化和不流血。可是,那些令人发指的事件开始了不过几个星期以后,官方即已通过法律,有权对任何讲述那些骇人听闻事件的人士进行严厉惩罚,即使讲述的地点是在自己家中也不例外。
▪ 一个再简单不过,而且几乎普遍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理由——畏惧。与其被围殴,那么倒不如跟着他们一起去揍别人。于是出现了一种没头没脑的飘飘然感觉,接着是万众一心所形成的如醉如痴感觉,有如磁铁一般进一步对群众产生了吸引力。
除此之外,... 德国式的思维过程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纳粹的对手所作的预测全部都没有实现。他们曾经声称,纳粹绝不可能获胜。可是现在纳粹已经赢了,这就表示前者无理,而纳粹是有理的一方。”同时某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另有一个观感,以为只需要现在加入纳粹党,就可以改变其面貌,将该党引导至另外一个方向。
最后,在那些比较感性、随波逐流、思想比较单纯的人群当中,还普遍出现了一种较原始的神秘主义想法。那就仿佛一个被击败的部落抛弃自己乏善可陈的部落神祇,转而信奉敌对部落的神明,将之作为自己的保护神。长久以来为人所信奉的圣马克思并无帮助,圣希特勒显然要来得更为有力。于是,我们把祭坛上的圣马克思像捣毁,把圣希特勒的神像供奉上去。让我们重新学习祈祷的方法,将“一切都是资本家的错”更改为“一切都是犹太人的错”。或许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救赎。
由此可见,这一切演变过程均非违反自然的现象。它们完全位于正常心理作用的范畴之内,而且几乎可以把所有看似难以解释的事项都说清楚。唯一剩下来有待澄清的事情就是,为何当时没有出现“有种”的举动。
▪ 整体看来,他们是一个不可靠、柔软懦弱和没有中心思想的民族。
▪ 千百万人一起神经崩溃以后,便出现了一个团结一致、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民族。今天它就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梦魇。
生活正常如昔
▪ 当时人们作出的解释是那么无谓、所提出的辩解是那么愚蠢、所做的尝试更是肤浅得不可救药——虽然已清清楚楚嗅到了恐怖与讨厌的气息,自己的理智却匆匆削足适履来适应一切!甚至连我们套用的各种“主义”也都完全脱离了现实。
真革命
▪ 纳粹运用同样的伎俩,在国际上针对许多其他的“问题”获得丰硕成果:他们可以向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特定的人群发出死亡威胁。结果,不是纳粹自己,而是对方的生存权突然成为普遍讨论的对象——也就是说,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 每个物种皆有与生俱来的团结本能,使自己得以在生存奋斗中存活下来。纳粹的意图却是要把这种本能连根拔除,同时让人类原本仅发泄在动物身上的猛兽天性,转而被用来对付自己同类当中的对象。于是,他们把一整个民族变得像是一群恶犬,而且还要“放狗咬人”。
▪ 等到国民变得随时准备对同类进行谋杀,甚至将此视为自己的责任之后,更换“被咬的对象”就只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了。
查莉——两段奇特的插曲
▪ 施暴的一方没有凶手,受难的一方则无烈士。此即一切都发生于半麻醉的状态下,而客观存在的恐怖事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肤浅而可悲的心理。于是将谋杀的行为比拟成不良少年滋事,将自己所受的屈辱及道德的沦丧视为不痛不痒的小插曲。即便有人壮烈成仁,基本上那也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已。
抵制犹太人的行动与弗朗克·兰道之流亡
▪ “总该有人过来向我说清楚讲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撒谎。”他仍然毫不松口地说道:“为什么他们在大权在握、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还要继续撒谎?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 “恐怕以后不会再有任何值得我们捍卫的事物。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形同囚犯,唯一剩下来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脱逃。我自己也巴不得能够离开这里。”
三种“置身事外”的诱惑
▪ 每个德国人处于逆境时——无论是在个人或国家的生活领域之内——都逃不出这个诱惑的折磨:完全放弃一切,以一种意气消沉的无所谓态度,把自己和世界拱手交给魔鬼。同时,他们更以执迷不悟的乖戾态度来进行道德上的自杀:
我开始对阳光感觉厌烦。
啊,寰宇即将全面崩坍!
▪ 司汤达写道:现在唯一值得努力一试的做法,就是要“让自我维持神圣与纯净”。
一群朋友的分崩离析与“科佩尼克大屠杀”
▪ 霍尔兹还信誓旦旦向我表示,既然犹太商店将受到有纪律的抵制,那就不可称之为“杀人”。
“这怎么不是杀人呢?”现在换我怒气冲冲吼了回去,“如果某人遭受有系统的迫害而破产,并被剥夺了一切谋生的机会,最后他岂不就会饿死吗?在我看来,如果有谁存心让别人饿死,那就是杀人的行为。难道你会有不同的看法吗?”
▪ 他继续表示:“您只是在那边鸡蛋里挑骨头,对当前‘德意志民族成形过程’出现的伟大事件始终避而不谈。(即使在今天,我耳边还不断响起他所谓的“民族成形过程”!)只要出现了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您就死咬着不放,并且在法律上大钻牛角尖,想借此来吹毛求疵。我只怕您还不怎么清楚,像您这种人今天已经对国家构成了潜在危险。国家有权,也有责任来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至少也要在你们当中有人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公开进行反制行动。”
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 不问世事的做法,到头来只是徒劳无功而已。不论退隐至何处,都躲不开自己原本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我终于明白,政治事件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分野,已被纳粹革命连根铲除,此后即无法再将那场革命视为单纯的“政治事件”。它不但发生于政治领域之内,也出现于每个人“私底下”的生活当中。其作用能力就像毒气,可穿透任何墙壁。而若想彻底摆脱这种毒气,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溜之大吉。这意味着移民国外:告别自己的出生地、自己的语言和所接受的教育,尤其必须切断与祖国的联系。
▪ 这种告别——心中对自己国家的告别——实在令人难以消受,而且痛苦万分。它来得断断续续、时进时退。有时我根本难以想象,自己终究会鼓起勇气拂袖而去。
▪ 他们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彩色斑块,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大。各式各样的“胜利”,为他们带来了获胜者的快感。别人低声下气所承受的屈辱,使他们乐在其中;别人心头出现的恐惧,成为其津津有味的享受对象。他们以“纽伦堡名歌手”的方式,极力自卖自夸其民族特质。他们更仿佛自慰一般,大肆宣扬“德意志”之心、“德意志”之情、“德意志”之忠诚,还鼓吹人人当“德意志”好汉,而且“要德意志本土化”。
▪ 我与任何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并无二致,如果自己的同胞,甚至整个国家做出了有损形象的行为,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反之,倘若别国的民族主义者以言论或行为来侮辱德国之际,我会感同身受。可是,当别人出乎意料地赞誉我的国家、谈及德国历史上美好的一面、称道德国人某些优良民族特质的时候,我又引以为荣。
▪ 我并不“爱”德国,那就好像我并不怎么“爱”我自己一样。如果真有让我喜爱的国家,那就是法国。但无论如何,即使没有纳粹存在,我对其他国家的好感,仍可能胜过我对自己国家的爱意。然而,自己的祖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这并非我所喜爱的任何外国能够取代的,因为它正是我自己的国家。如果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喜爱其他国家的资格,就会失去一切攸关国与国友好互动的先决条件——民族交流、异国间的情谊、彼此了解与学习、相互向对方展现自己的国度。
▪ 我与志同道合者眼中的德国,不仅仅是欧洲地图上的一个彩色斑块而已。“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由某些特质所共同组成的架构,其中包括了人道主义、全方位的开阔心胸、探索问题时的苦思冥想及深入彻底、对世界和对自己永不满意的态度,并且有勇气不断改弦更张进行尝试。它同时具有自我批判、热爱真理、就事论事、精益求精、追根究底等精神,于多样化的面貌之下略显笨拙沉闷,不过对即兴自由创作兴致勃勃。其行动迟缓而严肃,却又能够像玩游戏般富于创造精神,不断为自己塑造出新的形式,然后又觉得此路不通而另起炉灶。它除此之外的特质,还包括对于择善固执和特立独行作风的尊重、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多愁善感、具音乐才能。尤其重要的是,它享有很大的自由挥洒空间。
▪ 民族主义——此即民族的自我吹嘘和自我崇拜——无论何时何地都绝对是一种危险的精神疾病,足以扭曲和丑化一个民族的面貌。其情况就类似虚荣心和利己主义对个人特质所产生的作用,能够颠倒是非、使一个人丑态毕露。
异族统治是否胜过纳粹统治?
▪ 我不时看见家父坐在书桌前面久久不起身。桌上并没有纸张,他光是用空虚绝望的目光凝视远方,仿佛眼前只有一大片残破的土地。
▪ 对那些不习惯于压抑自己的动作和语言的人来说,如果压力实在太大,迟早会有某个身体器官把心灵的痛苦承接过来,而导致疾病发生。有些人会心脏病发作,而家父则是胃部出了毛病,让他痛得难以消受,而且会痉挛呕吐。此后,他几乎就未曾再坐回书桌前面。
不真实的夏天
▪ 我并不怎么觉得自己是虔诚的教徒。多少年来,我始终对教会抱持“尊重而不渴慕”的态度。无论如何,我的立场非常坚定:即使不渴慕教会,仍必须加以尊重。
于特博格的“世界观教育”
▪ 我们在这里学习射击,以便通过国家中级文官考试!
“我”而今安在?
▪ 在眼前的时刻,凡事只不过意味着冒险犯难和人生历练。有些东西当然是我绝对不能做的:不主动说出将来会引以为羞的话,只打靶而不开枪伤人,不让自己被套牢,不出卖自我……再来还能剩下多少事情可做呢?其他的一切早已拱手让人或抛弃得踪迹难寻。我已经穿上了扎着万字臂章的制服,我立正站着,而且我还擦枪。不过,这些都不能当作一回事,因为在那么做以前,可没有人征询过我的意见。真正那么做的人并不是我;那只是一场游戏,我只不过在里面扮演小角色而已。
▪ 可是天晓得,说不定有朝一日会开庭审判,而且那个法庭不接受这种借口,只是铁面无私记下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开庭时,法庭不会直视我的内心,反而只是盯着我的万字臂章仔细端详。面对这种审判时,证据对我是非常不利的。老天!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该如何回答法官的质疑?他会向我问道:“你套上了万字臂章。你表示根本就不想要这个臂章?好吧,那么你为什么还是那么做了?”
难道非要我在抵达营区的第一天,当他们把臂章发给我的时候,马上公开表态:“不行,我绝不佩戴这种东西。”然后把它踩在脚底下?可是,这只会显得既疯狂又可笑,同时也将意味着:我会被送入集中营,没办法前往巴黎。我将再也无法通过考试,以致违背了当初对父亲作出的承诺。甚至我就此一命呜呼,不但死得轻如鸿毛,而且是为了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而亡,连观众也没有。那未免太离谱了!
▪ 我努力想找出答案来,可是想来想去都不得要领。看来沉默才是上策。
被“同志化”的德国人
▪ 当人们为了乐在其中及获得麻醉——亦即纯粹为了追寻“同志情谊”——而过着“同志般的团体生活”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毒瘾。它只能带来一时的幸福,却无法造成任何改变。它比酒精和鸦片更能让人堕落颓废。它使人再也无法独立过着负责任的文明生活。它甚至变成了“去文明化”的工具。
▪ 我们绝不应忽视,“同志般的团体生活”可以是多么可怕的一级毒品。我只想再强调一次:毒品能够让人感觉幸福,所以肉体和心灵都可能对它产生依赖性,而且毒品也可以带来某种疗效以致让人上瘾。这就是其之所以为毒品的原因。
▪ “同志般的团体生活”为了凌驾一切之上,于是彻底移除了个人的自我责任心。
▪ 更不幸的是,“同志般的团体生活”会让人不再信赖自己,失去在上帝之前和面对自己良心时所应具备的责任感。
▪ 为“同志般的团体生活”正意味着,集体的智力水平被锁定在最低阶的程度,而且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讨论。
▪ 在“同志般的团体生活”里面,思想缺乏立足之地,所存在的只有群众的原始妄想,而且那是想躲也躲不掉的。如果有谁打算摆脱它,就等于自绝于“同志情谊”。
▪ “我们”是集体的动物,而且一旦加上了心智上的怯懦与团体生活的虚伪以后,只要看见会扰乱集体满足感的事物,便会出于本能一概加以忽视……那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第三帝国”。
▪ “同志般的团体生活”以引人注目的积极方式,将所有攸关个人与文明的事物腐蚀一空。
▪ 德国人因为生来就比较缺乏塑造个人生活、追寻个人幸福的才能,于是欢欣鼓舞加以接受。他们是如此心甘情愿,以致舍弃了柔嫩而香气四溢,但高高在上看似危险的自由之果实。他们宁可采撷身旁垂手可得、枝繁叶茂且浑圆多汁的毒果,结果换来了不由分说针对每一个人,而且会让人变得卑鄙可耻的“同志般的团体生活”。
▪ 人们在里面觉得幸福至极,同时却以骇人的方式丧失了自我价值。他们洋洋自得,同时却丑陋得无以复加;他们趾高气扬,同时却变成了极端卑贱的下等人。人们自以为在山巅漫游,事实上却爬行于泥淖之中。当那个魔咒继续有效的时候,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可加以破除的解药。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