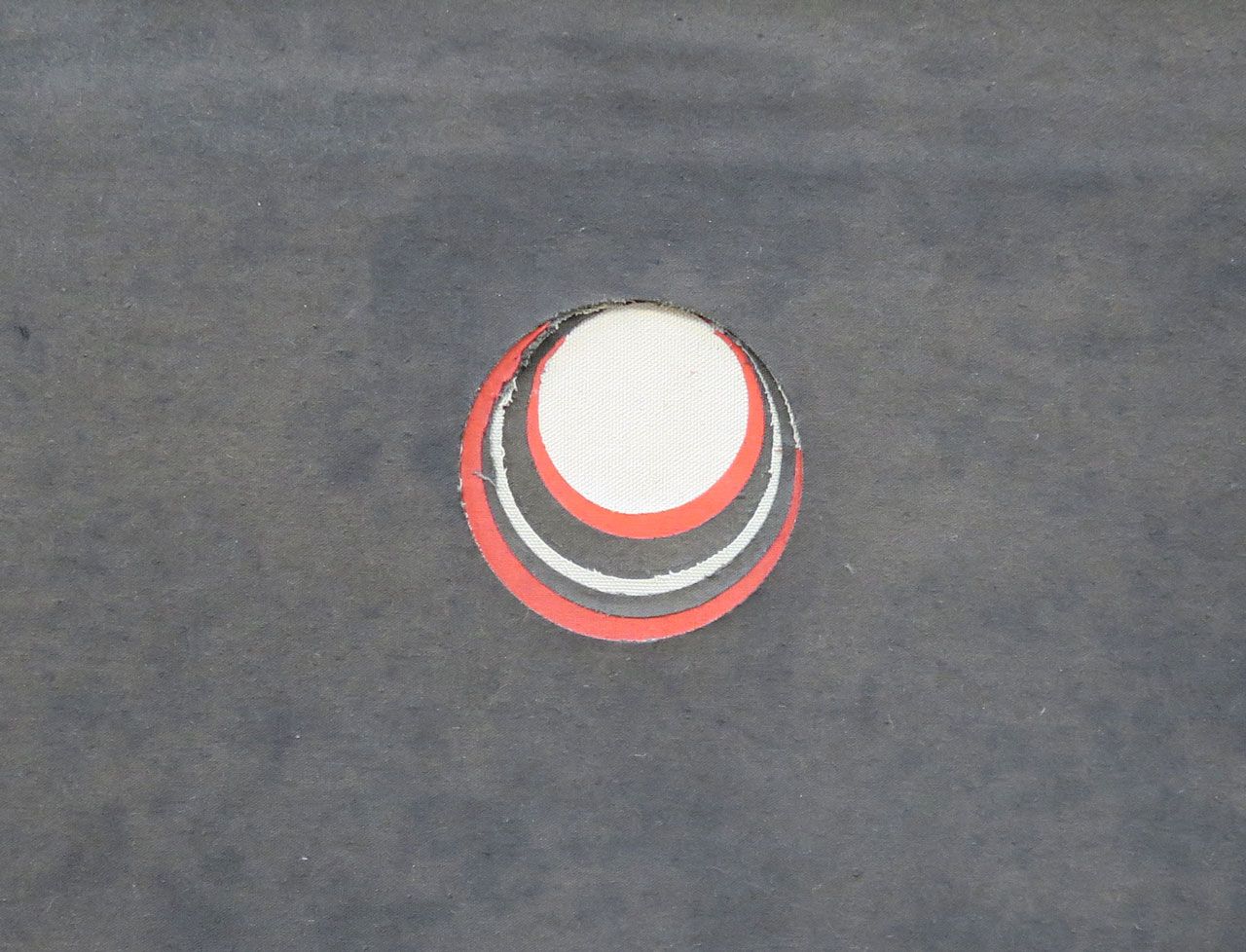
遊蕩人生,漂浮不定。
逐字稿
最近因為工作的關係,打了很多逐字稿。
我打逐字稿已經很有心得,雖然還不到邊聽就能邊打的流暢程度,但至少聽得懂,也能在模糊的聲音中猜出五六成意思。
打逐字稿其實很傷神,一則有時錄音聽不清,一個句子要反反覆覆的重播,很累人。再則若講者說話顛三倒四,我得另外花精神潤飾。我的逐字稿並不追求絕對的準確,而是要約化成可以閱讀的流暢句子,要是內容口語太支離破碎,我還得花很多工夫改成通順的句子,很花時間。常常一天下來,能打的量很有限。一直用耳機聽錄音,對耳朵也很傷。
因為我聽的都是藝術家訪問,每次打都有很深感觸。老一輩的藝術家,比如50年代就很活躍的,我發現他們條理不一定清晰,心思也不見得縝密。要說他們年紀大了記憶有點退化,我也碰過那種年紀很大,但耳聰目明的那種。這讓我感覺,聰明才智確實是有點影響的。但這些話都有點講不清楚的人,往往位高權重,我就覺得,唉,該不會他們當年也有有沾到什麼點好處吧。我聽到最有趣的內容就是,有位老畫家歷經秦松事件,但不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也不覺得自己的創作受到什麼限制。他大學剛畢業時初得大名,就自己跑去美國,當了華裔藝術家。如今我不免懷疑,這應該就是在黨國照拂下,享盡黨國特權的人。國民黨統治底下的台灣,並不是全然沒有自由,只是有這樣自由的人,少之又少,我想老畫家可能也是其中一位。
然後就是聽訪問的人(就是主持人)問問題,又覺得,人真的受限於自己的所學很深。比如最近打的逐字稿,藝術家一聽就知道是那種小時候不學無術,但鬼點子很多的人。這種人當藝術家最好,只要讓他們對這事情有興趣了,以他們天馬行空的腦袋,做出來的都是新天新地。但碰到主持人這種從小一路念好學校上來,標準乖乖牌,就算要搞怪也是一本正經的學者,他們就很難理解鬼馬型的天才不受控制的天賦,天生想要顛覆、挑戰既有定義的自由人格。學者一定要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定要條條框框很清楚,覺得這不是A就是B,至少是又A又B,絕不會是非A非B。這固然是做學問訓練時的養成,但碰到任真天然的藝術家,就顯得窠臼太深,套句台語講的,「胭脂馬遇到關老爺」。
當然,問問題是有技巧的,有些人會問一些很笨的問題,好引出對方講出他平素不會說的一些隻言片語,我覺得蔡康永就是這樣。也有些人會老問些天氣好不好之類的問題,其實是要從蛛絲馬跡中窺探真正想要知道的八卦,這是很多老式新聞記者的套路。但有時候我覺得那些問題,只是很明顯看到一個人的侷限,那種畫地自限的侷限。
我也找了一些學生幫我打逐字稿,每每傳回來的內容,我都得大改特改。現在的八、九年級生,可能因為又過了一個世代,很多稍微有點年歲的用詞,在他們的語境裡已經不再存在,打出來的內容荒腔走板,實在是稀鬆平常。特別有些畫家經歷白色恐怖時期,戒嚴期間的一些特殊用語,我其實還可以理解,到現在二十幾歲的人,大概根本毫無概念,不禁讓我感嘆歲月流逝之快,時代斷層之大。
而且有時畫家講的內容,是戰後現代藝術或當代藝術的過往,照理這已經進入台灣美術史的範圍,但顯然他們雖然出身美術相關科系,仍舊一無所知。這種知識的空白,一直是美術科系學生的最大罩門,雖然無法全然責怪學生,但一方面也感嘆,我們對自己的認識真的少之又少。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