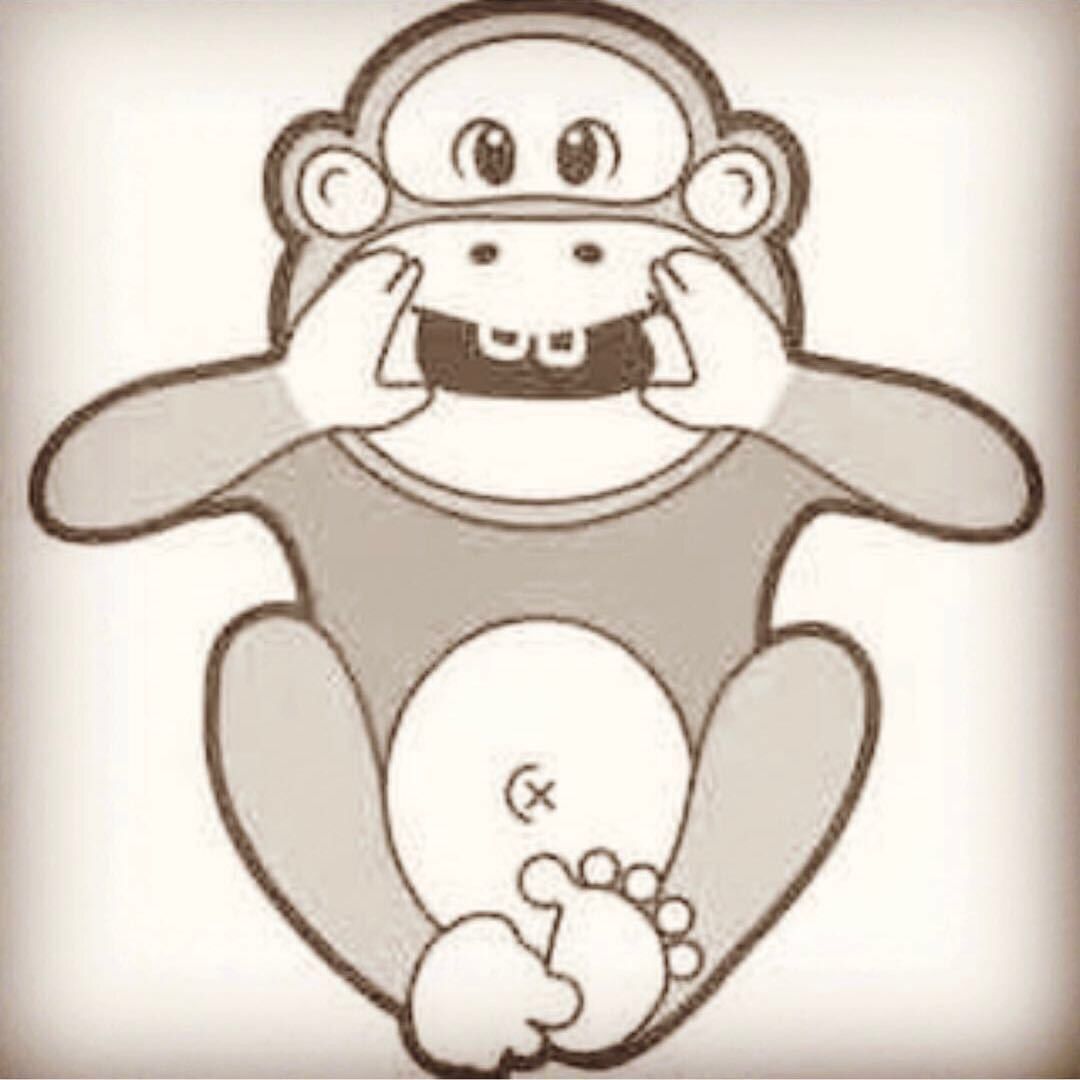
這裡漂浮一個節點,留存那些不甘心。或者是沈溺在自我世界時,基於語言的日常文藝實踐。
如何自焚才能惊人?
我们可以留三分钟,让每个人想象一下:如何自焚才能够惊人?接下来,我们再留出十分钟,请大家认真想想,火如何烧掉自己的汗毛,烧掉皮肤,烧掉血肉,烧在筋骨上。
这个题目来自“语不惊人死不休”,它是写作者的追求。无数杰出的人类殚精竭虑地创造了很多语言的杰作,站在这样辽阔厚实的基础之上,一个有丰富阅读又有写作追求的新人会益发困窘。
这种窘迫有时候是美妙的,但很多时候是是羞耻的,尤其是是它跟“如何自焚才能惊人”这个问题并列时。
我年轻时,《南方周末》也还有些力量的时候,听朋友聊天,有强拆还是冤案来找记者,希望有“伸冤报道”。同类题材太多了,很难找到“新闻性”,当事人表示可以自焚(大概也包括了要被救下来),大概是知道某些个事件因为自焚引发关注最后得到妥善解决吧。
最后记者还是没有同意,这种预先设计的事件本身有新闻伦理的争议,但这还是其次,而是从从业者的角度来说,“自焚”也不新鲜了。
“第一个自焚是大事件,第二个自焚还能报道出来,第三个自焚恐怕就难以上报纸了。”
这句话给我强烈的熟悉感,小时候,作文书也是这么说的:“第一个把爱情比作玫瑰的是天才,第二个把爱情比作玫瑰的只是庸才,第三个把爱情比作玫瑰的则是蠢才了。”
那,除了自焚还有别的办法吗?
甚至更为苛刻的情况出现了。自焚,变成了某个民族抗争的仪式性表达,一方面,“自焚人数”这个词出现以后,数字取代了真实的人,或许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持续的表达,一次一次构成了巨大但无声的呐喊,让人内心无法安宁。
受者需要有相同的仪式。每当数字新增时,每个人都应当给自己留出十分钟,处于安静黑暗的房子里,缓慢想象,大火烧掉自己的汗毛,烧掉皮肤,烧掉血肉,烧在筋骨上;想象有火持续的小声叹息,或者是骨头烧裂的细细嘎吱声;想象或从脚面烧起,烧掉小腿,站立不住的人垮在火堆里,巨大的痛感已经让人无法闻到血肉烧焦的臭味,想象火烧到半个身体上方的眼睛了。
在一切都被取缔的时候,社交媒体成了抗争、伸冤、哭诉的最后场所。铁链女和唐山暴力伤害,因为视频,使得事件得以广泛传播,“惊到了人”,但是,如果没有现场视频,我们如何依赖语言呢?
“人在方舱,警察拦住”八个字,其力量约等于诗经或者更为甚之。一个村支书加人大代表,完全可以一手遮天了。这个传言有效的勾勒了信息点“村支书”、“人大代表”、“强奸 12 岁幼女”,同时,作者知道如此巨大的词汇在这个时代毫无意义,所以创造性地演绎了“人在方舱,警察拦住”。
它的广泛流传,是因为村支书人大代表强奸 12 岁幼女吗?如此巨大的事件必须借助于“人在方舱,警察拦住”才得以传播。作者才情无与伦比!我们各自也可以扪心自问,“人在方舱警察拦住”是否击中了自己,是否相信它大概率可能发生?
这个才情不断被再证,比如在警方的通告里更在意后者;比如大 v 胡编一句带过强奸,数段抨击“制造舆情”。所有的部门和舔狗都第一时间承担宣传部的职责,对“语言”充满了愤慨、澄清、批评。其实,人们还期待更多事实,如何做的人大代表,如何通过基层选举做的村支书,父母到底在哪里和为什么在那里……当然,在这个时代这是不恰当的期待。
语言的悲剧就在这里,它产生关注,又无法脱身。
语言可以不在场吗?事实能自己把钟敲响吗?很可惜。不能。除非,你是第一个自焚的,你是第一个哮喘不得救治而死的,你是第一个被发现活人送去火葬的,你是第一个锁门饿死的。那样,或许有机会占据社交媒体 15 分钟或者 15 天的注意力。
15 天是一个抽象的上限。比如铁链女不见了,声援的人不见了。比如唐山四个被打当事人不见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也都不见了。有趣的是,我分享了听到的一个恶性事件,说没有在网上找到任何资讯,得到的留言是,“我这儿也有一个这样的事”。
那些没有语言加持的事件,将永远消失。那些没有被“人在方舱警察拦住”赋予力量的被强奸的幼女们,永远无法伸张权利和寻求正义。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还少吗?某个民族一个又一个的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争,都完全无法获得传播,形成舆论。骨头,在细细嘎吱地响着,火一直在那里小声叹息。
只恨语不惊人。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