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职业转型研究者,前媒体工作者,致力于中国政治、文化和心理的转型研究、创作和教育。
“对话”到底是什么?回应项飙×陈嘉映关于对话的蹩脚阐释
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三个多月前,看了一篇“项飙×陈嘉映”关于“对话”的对话,本没抱什么期望,但还是很大跌眼镜,不吐不快,于是想写一篇回应,但由于正赶上搬家和后来又关注跌宕起伏的美国大选就拖了下来。
近日,我在”未来志iMeta社群“里讨论主体性问题时触及了“对话”概念,便想起了这个茬儿,因为是概念问题,没什么时效性,那就再补上吧,正在写一篇长文,也算是一种调节吧。由于这个讨论还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先引述如下,不妨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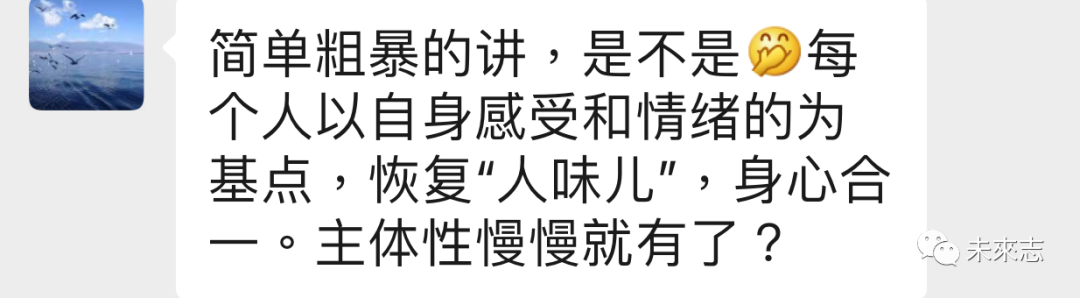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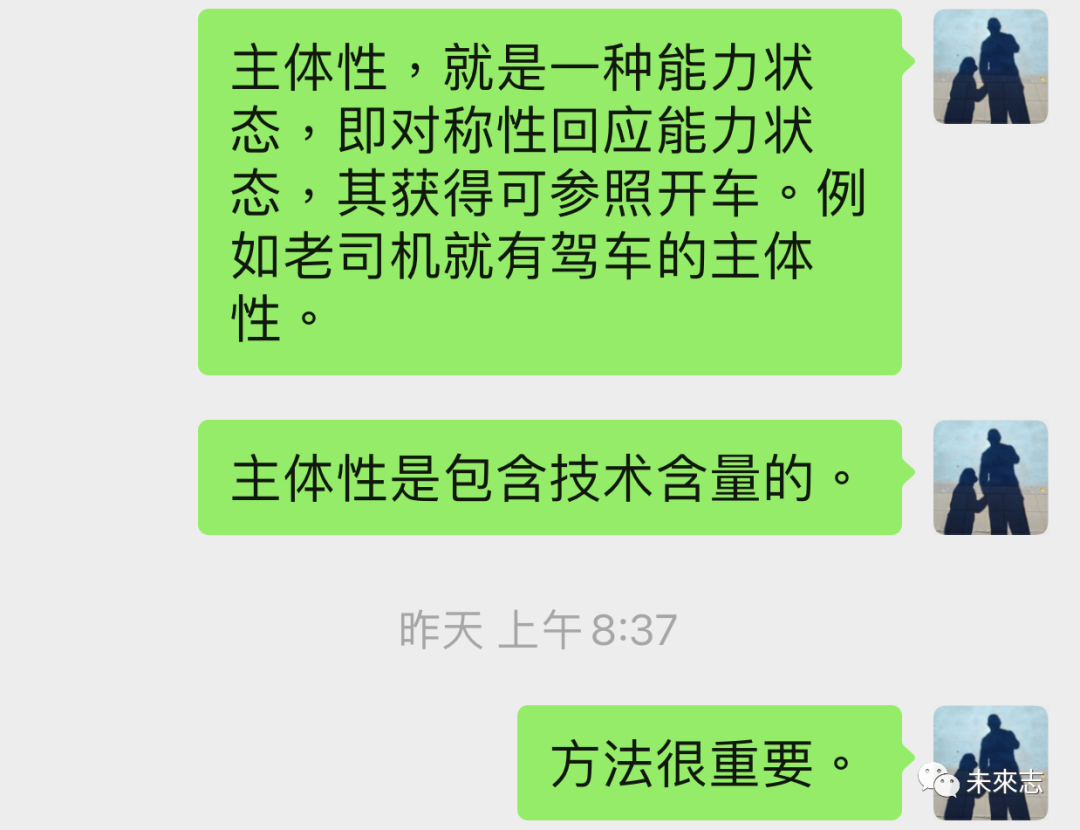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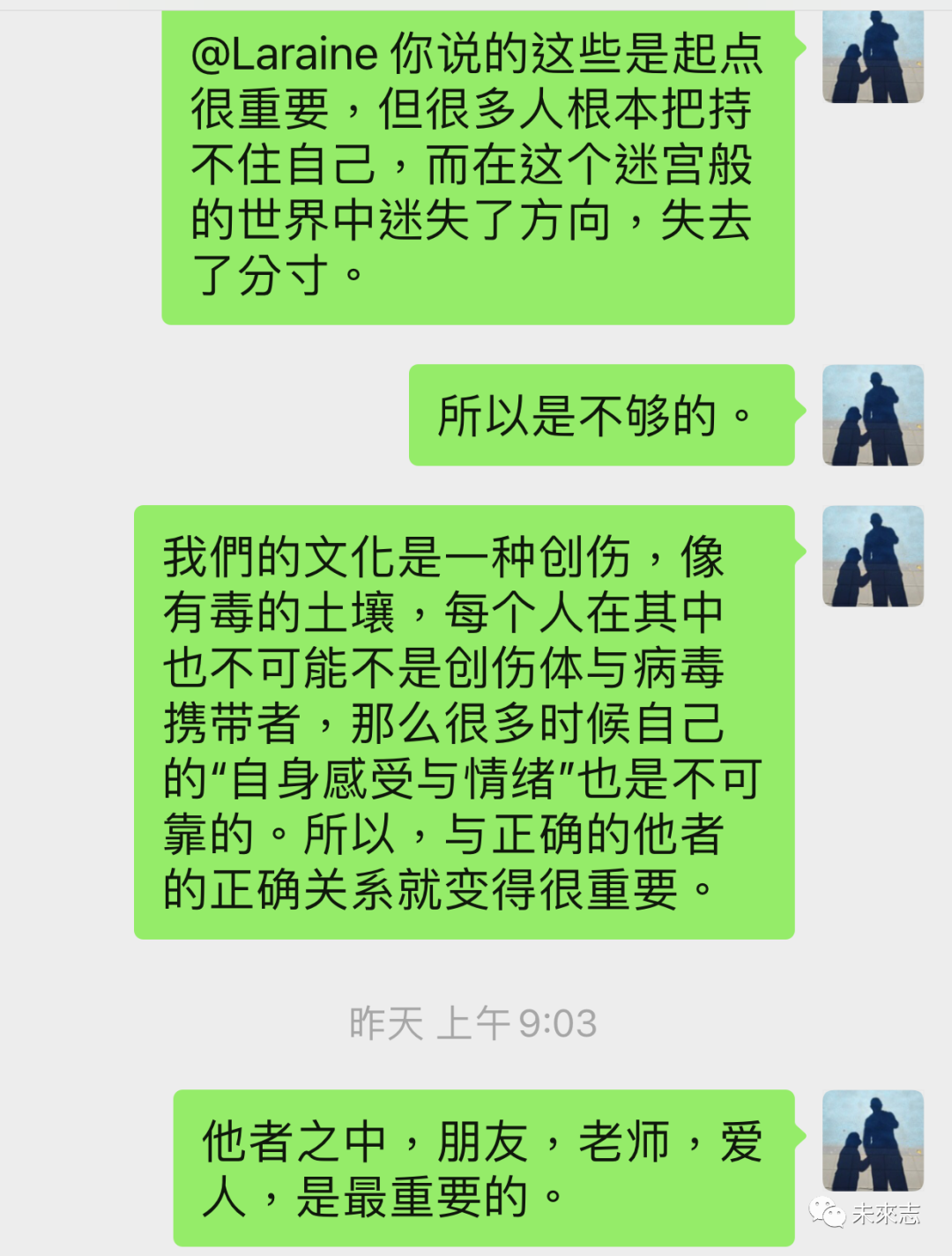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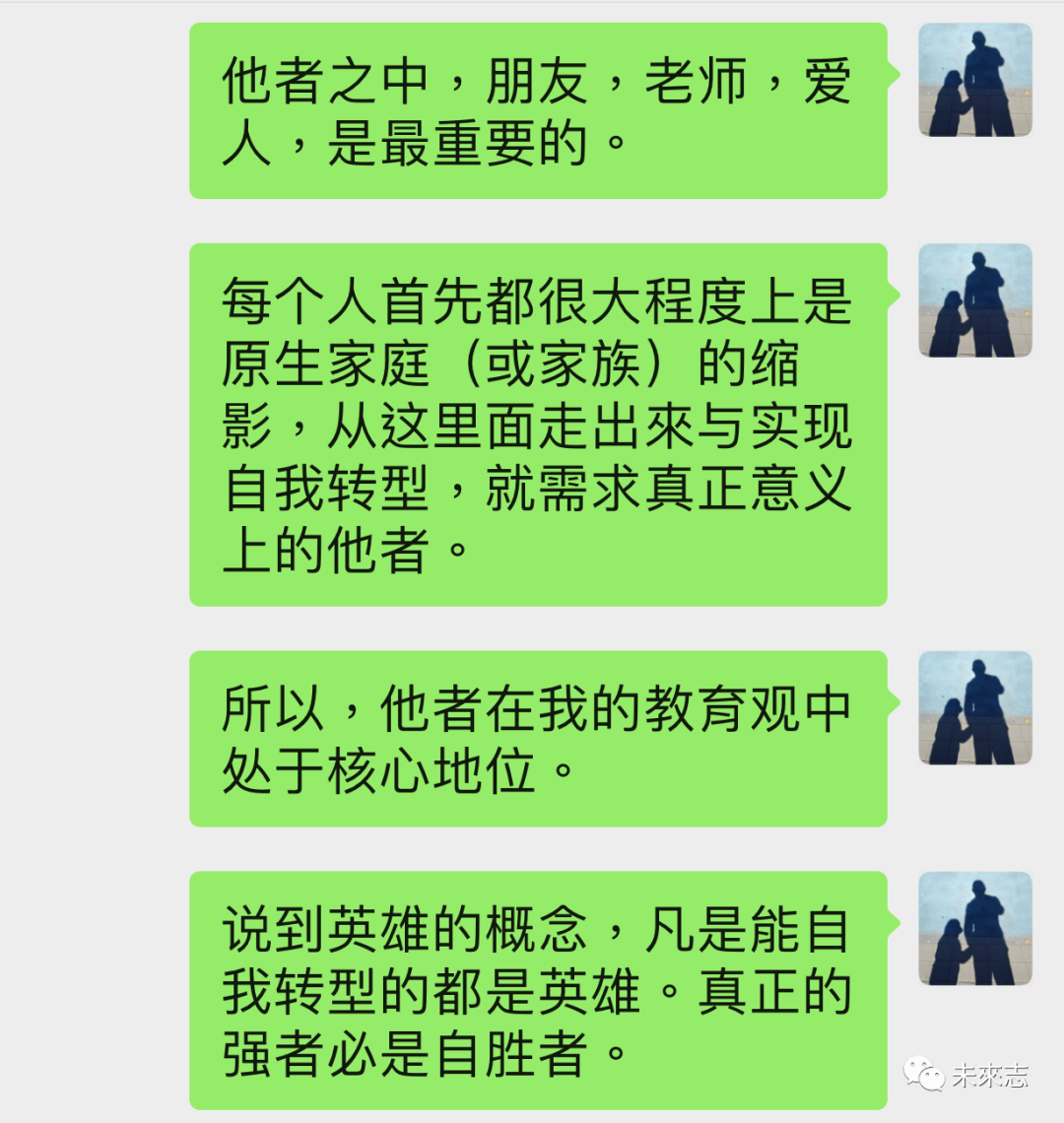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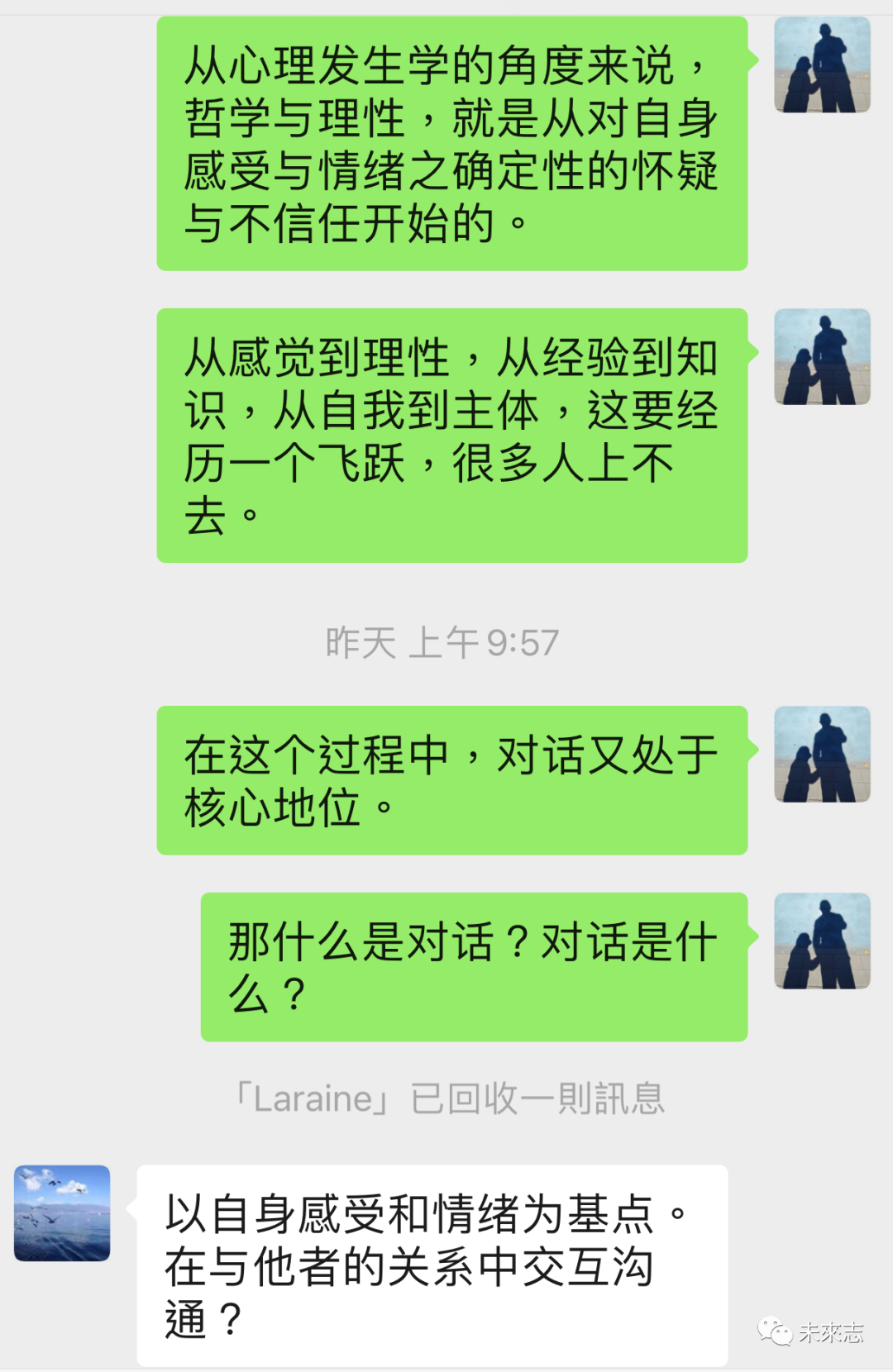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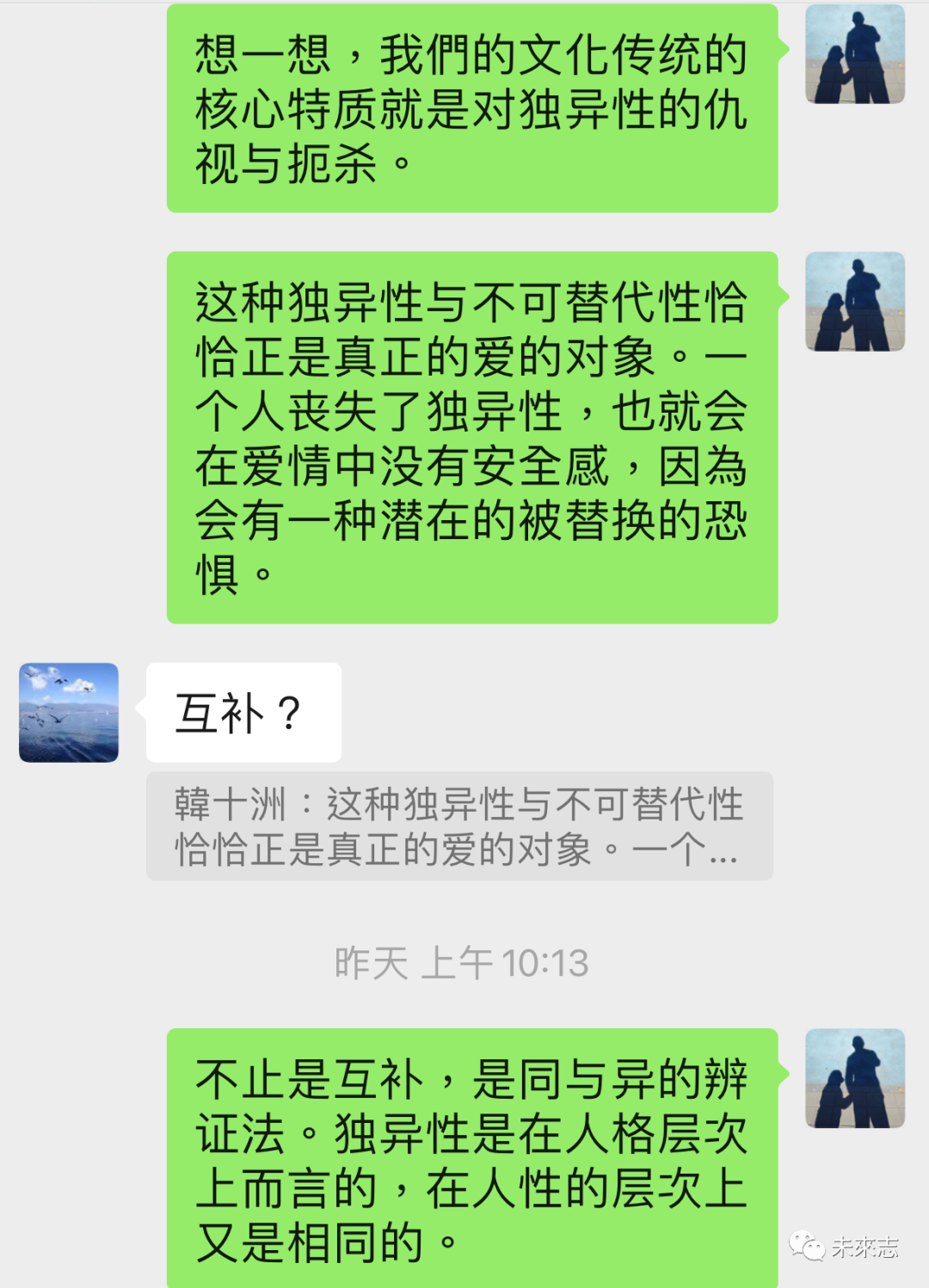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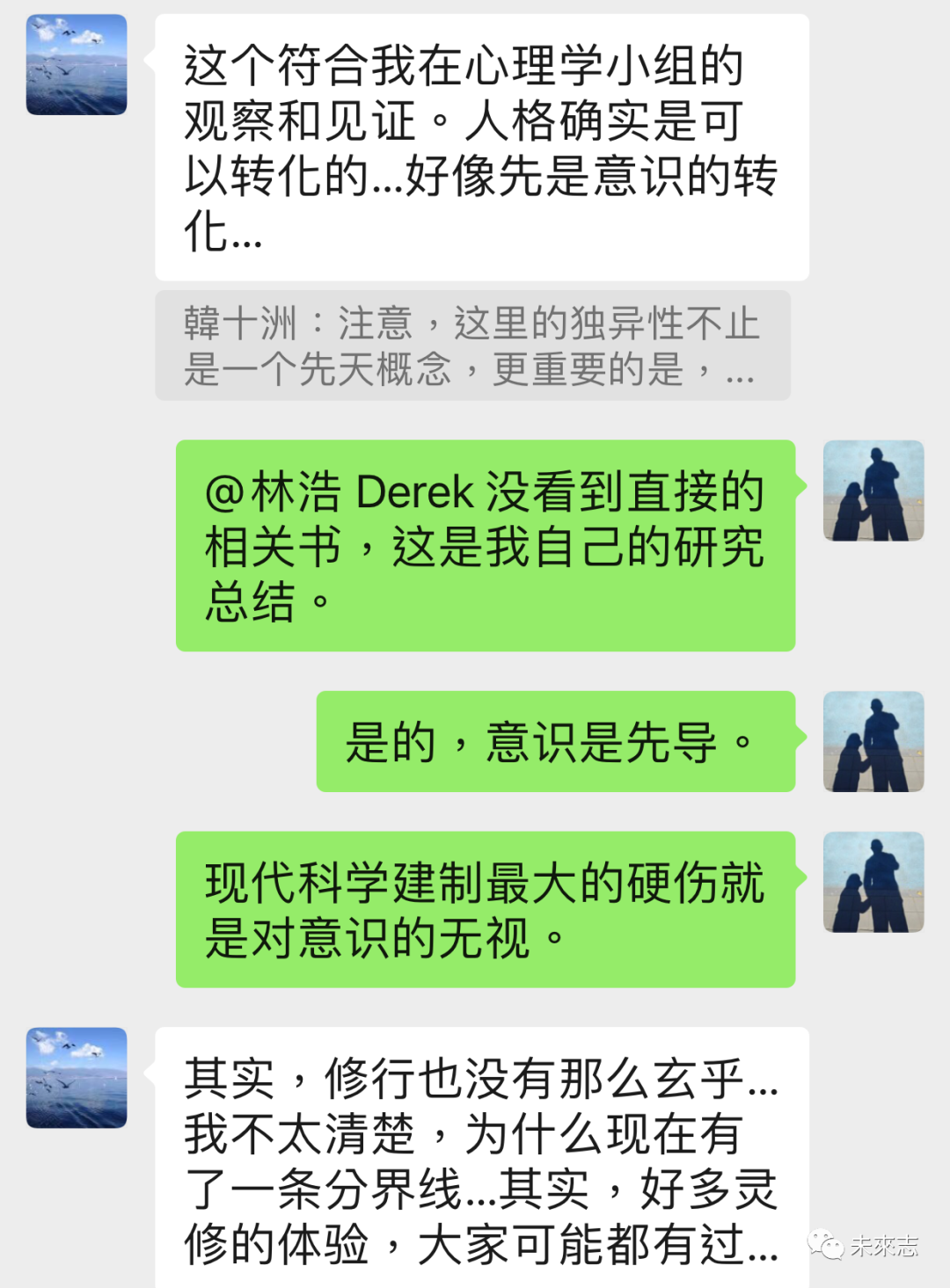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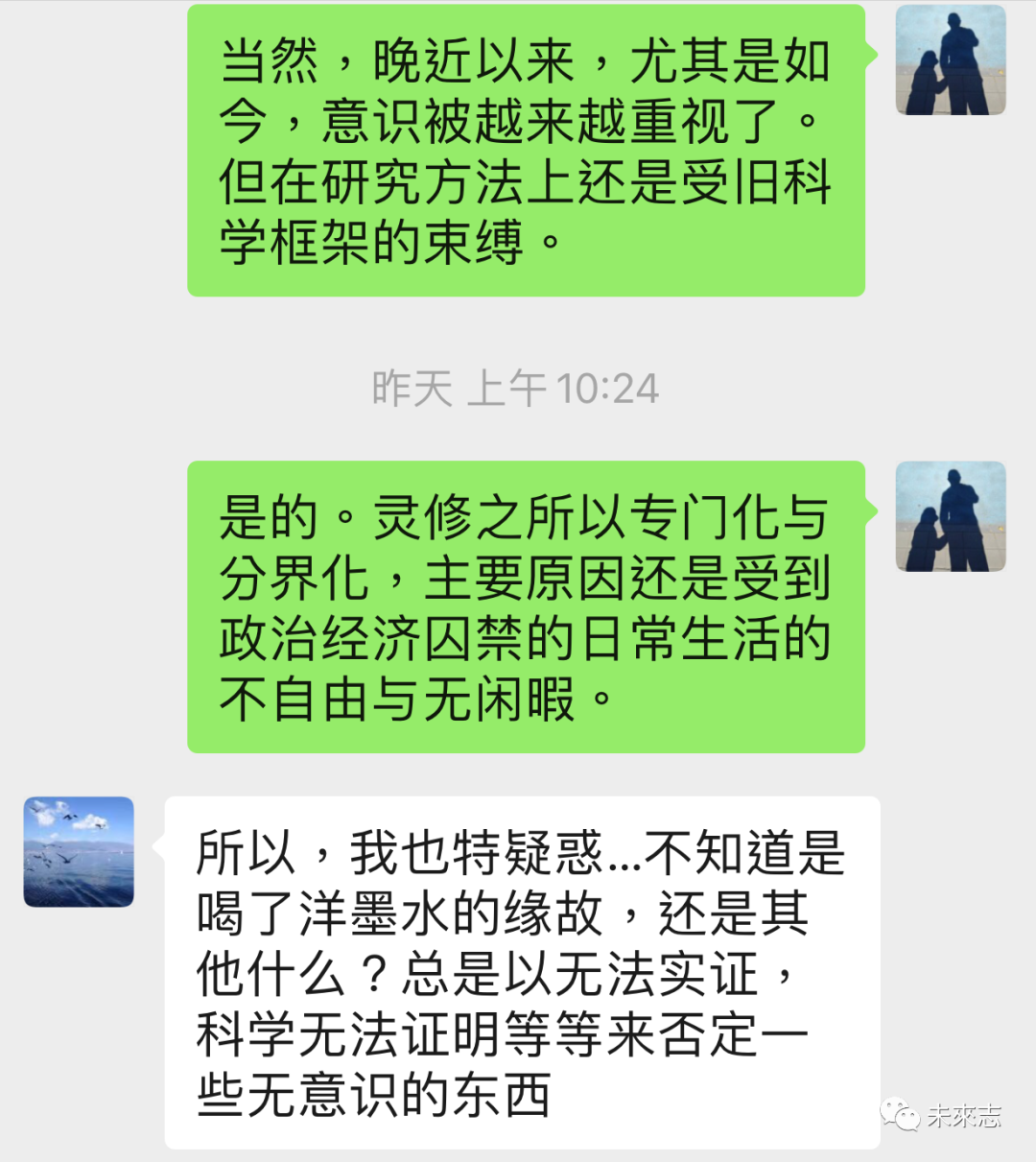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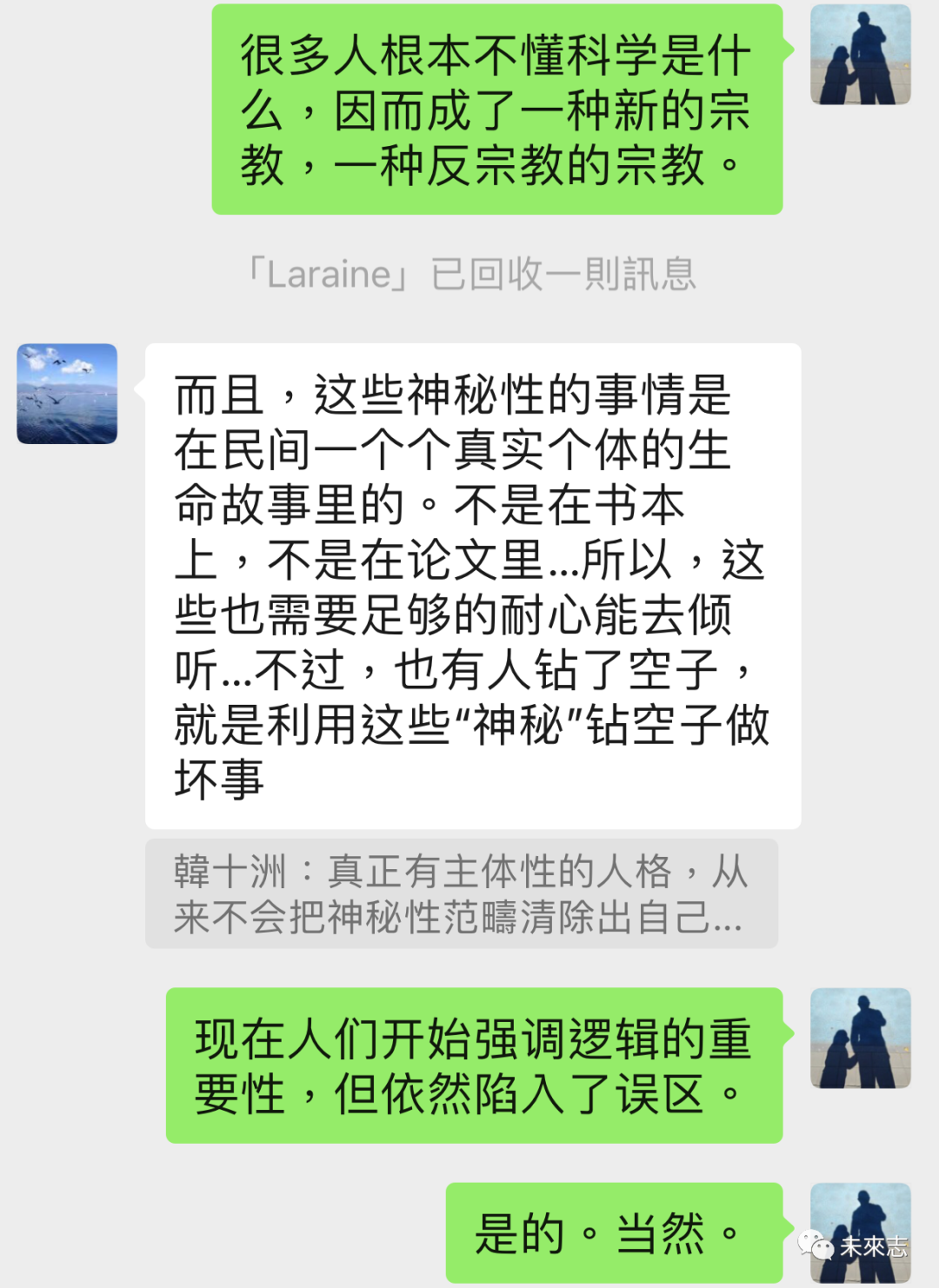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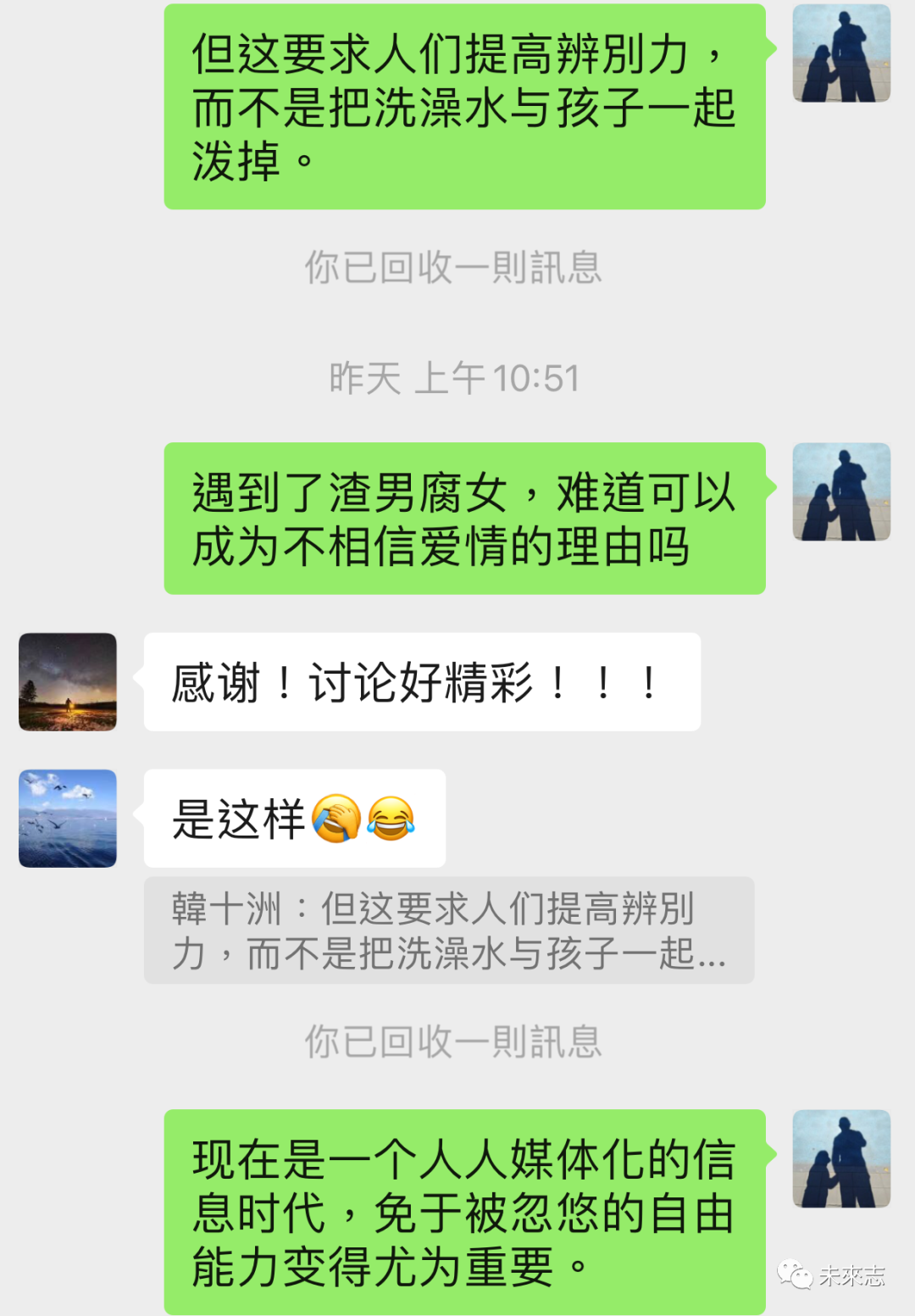
对话,不管是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还是作为一种探究方式,或是作为一种文体形式,一向是我十分关心的。十几年前我手头就有一本书《全球对话的时代》,后来在做记者时,我在所在媒体推动开设“时代议题”栏目时,心中有两个促进目标,一个是理解,另一个就是对话,遗憾的是,栏目是开了,但目标未遂,如今依然是“念兹在兹”,因而也常常思考:“理解”究竟是什么,“对话”到底是什么?如何抵达理解,如何实现对话?
现在,我说说自己此时对于“理解”与“对话”这两个彼此相关的概念的阐释。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框架,我们可以把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这个宇宙划分为三个层次:事、理、道,这显然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但可以对应西方思想中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启示神学或神秘主义三个层次,关于“事”与“理”这两个层次,也可以对应莱布尼兹关于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的区分:“真理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真理,一种是事实真理,前者是必然的,其对立面不可能成立的,而后者是偶然的,其对立面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一个真理是必然的,人们便可以通过分析而找到它的理由,即通过将它解析为更为简单的理念和真理,最终达到原初性的基本真理。”
那么,可以说,“理解”对应就是这种“理性真理”,意谓着是对于事物之纹理性、结构性和必然性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显然也必定是一种整体性把握,宛如庖丁解牛,必定是顺“理”而“解”之,虽说是“目无全牛”,但必定是“心有全牛”,因而能“得心应手”,而此时之“心”则必定是抵达了“道”的层次。那么,我们不妨说,人的三种官能:心(悟性)、脑(理性)与眼或手(感性),正好可以对应道、理、事这三个层次,而且,这三个层次是“三位一体”或“三维一体”的,三若缺其一便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数学上有一个纽结理论(knot theory),其中一个基本含义是,“一个n维球,只可以在n+2维空间扭成结,而且必定在n+3维空间解结”。我们把这翻译成通俗语言就是,在低维或低阶中的不管是什么“结”在高维或高阶中就自动“解”开了;再如塔尔斯基(Tarski)的逻辑,“一个语义系统不具备解释自身所必需的全部手段”。其实,在隐喻意义上,这可以对应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陆游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以及歌德的“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
这什么意思呢?我的解读是,我们要想理解一个对象,就必须首先整体性地把握这个对象,而这进而要求我们必须站到比这个对象所在的层次更高的层次上才能做到。这就是我在前一篇文章《iMeta报告 | “内卷化”成热词の病理分析:一场全球化下的中国式集体“叫魂”》中所说的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结构:“跳出X才能理解X”或“站在X之外或之上才能理解X”(Meta-X)。要想“跳出来”或“走出去”,那就必须“破界”、“出圈儿”或“冲决网罗”,进而才有可能“升维”和“进阶”,那么,此时此刻,“他者”概念便出场了。
我们要想理解一个对象(object),就必需这个对象之外的他者(other),我们要想认识自我,就必须认识他者,正如诺瓦里斯所说,“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又如伽达默尔所说,”他者是通往自我之路“,再如柄谷行人在《跨越性批判》中特别强调的康德的“强烈的视差”。那么,至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的概念也便呼之欲出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想真正地“理解”,就不可能不需要“他者”和“对话”。
那么,什么是对话?对话是什么?首先要说的是,这两个问句的内涵,其实是不一样的,尽管通常人们对此不做区分。前者是把一个事例赋予“对话”这个概念,例如,苏格拉底的问答就是一种对话,而后者才是追问“对话”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或者说定义。
关于“对话”的定义,我在9月中旬与国内教育戏剧的倡导者、戏剧编剧、导演曹曦先生在他非常用心耕耘的“这是真的么IsThisReal”播客中的一个对谈《#14 地板和天花板的差别——谈谈中国的转型》中做过一次阐释:对话是一种关于共同的主题或问题而在主体之间进行的同与异的辩证法,没有“同”,对话便不可能,没有“异”,对话便无意义,而“辩证法”的含义是,对话主体彼此之间就像是双人舞,既要有相互启发,也要有相互批判,又像是阴阳鱼那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对话呢?因为,对话具有存在论、认识论和主体论上的根本意义。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丧失了对话性,那么,他或她的存在便会陷入一种自我封闭的停滞状态和“躁郁症”。当今这个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抑郁症或躁郁症,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者的消失”(自恋主义)和“对话的消失”(相对主义)。反过来说,我们要想走出精致而封闭且空心化的“自我”(ego),寻找命运的主题,创造生命的意义,感受自己的“存在感”,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那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以上所说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再来看项飙和陈嘉映先生在“对话的精神”主题之下是如何阐释“对话”的。我的评价是:未得要领,混淆范畴,荒腔走板,肯定不能说是全错,但基本上可以说是bullshit。例如,项飙先生说,“我就是将对话作为聊天”,这显然是把“对话”概念的范畴搞得过于宽泛了,如果“对话”与“聊天”可以等同的话,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词汇而不是只有一个就好了呢?同时,以“聊天”来替换“对话”也把“对话”(dia-logue)概念中自带的“逻辑性”(logic)和“理性”(reason)的要求给抹除了。
查阅wikipedia,我们可以看到,dialogue的词源是古希腊的διάλογος(dialogos),“dia”是“通过”(through)的意思,“logos”是“讲话”(speech)和“理性”(reason)的意思,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达到前面所说的“理”的层次、相对来说比较聚焦并且具有“逻辑推进感”或“理性的质感”的交流才能称得上是“对话”,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东拉西扯或漫谈式的“聊天”或生意上的讨价还价不应被称为“对话”(我就奇了怪了,项飙先生作为“对话的精神”的系列活动的主嘉宾为什么不备备课去了解一下“对话”概念的真正内涵呢?),否则,这次“项飙×陈嘉映”的交流活动的主题为什么不叫“聊天的精神”而叫“对话的精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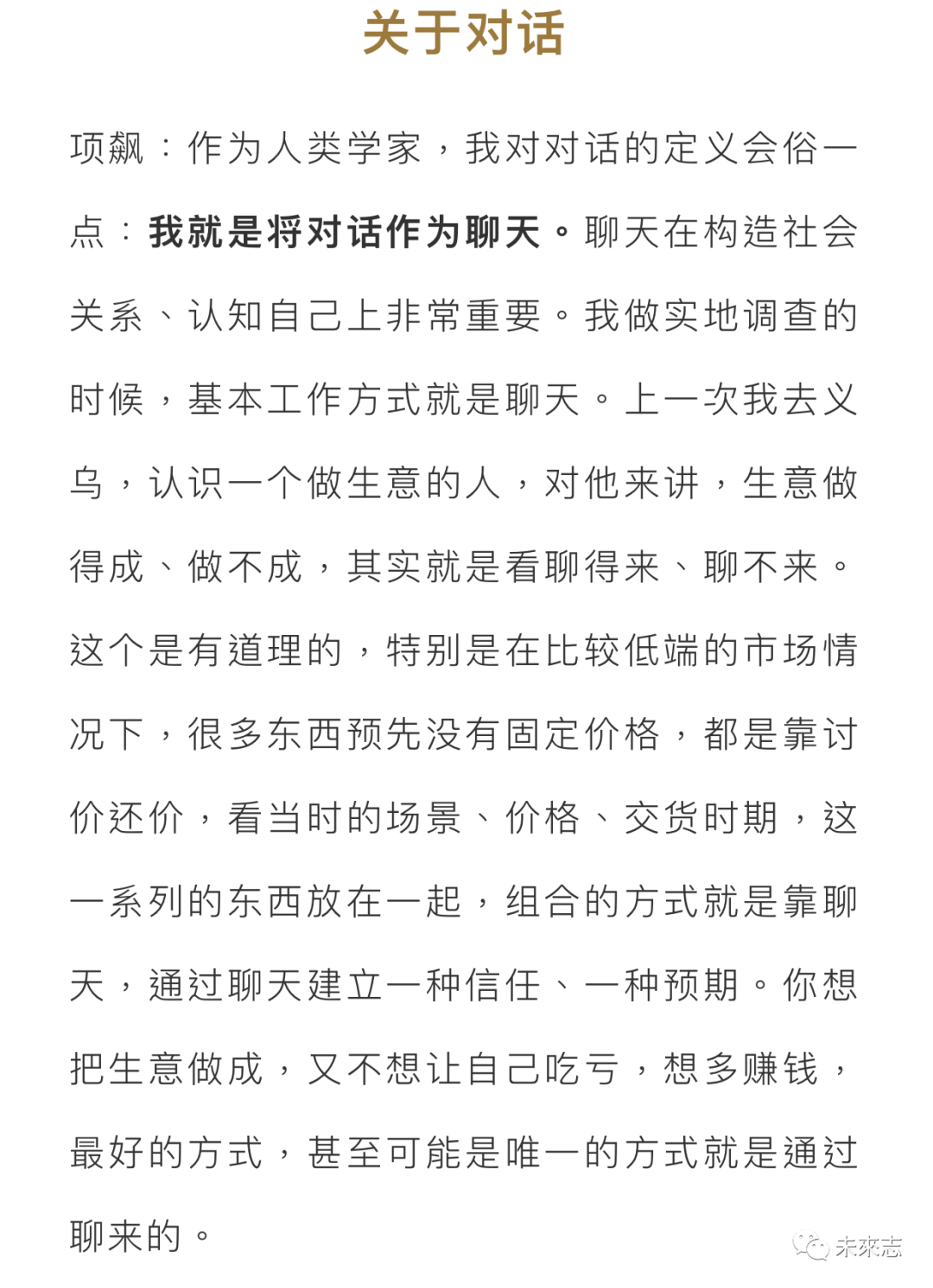

而陈嘉映先生,作为被媒体誉为“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对项飙先生的阐释却并未提出自己的批判和引导,实在不是“对话的精神”主题下的一位足够合格的对话嘉宾,因而成了“没有对话性的对话”和“没有主体性的主体”,徒具形式与皮囊。陈嘉映先生说,“对话不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甚至可以说,思想层的对话基本上不能以达成共识为目的”。陈嘉映先生并没有完全说错,但会让人感到似乎哪里有点别扭(这似乎是陈嘉映先生的“哲学话语”的风格),的确,共识可以不是也不必然是对话的目的,但正如我们前面的定义,共识其实是对话之所以可能的构成要件和“逻辑台阶”。没有“共识”或者说被认识到或被挖掘出的“同”,对话其实是不可能的,那就会陷入人们经常说的隐喻,“鸡同鸭讲”,或“对牛弹琴”。只要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一定离不开“同”与“异”的辩证法(双人舞,阴阳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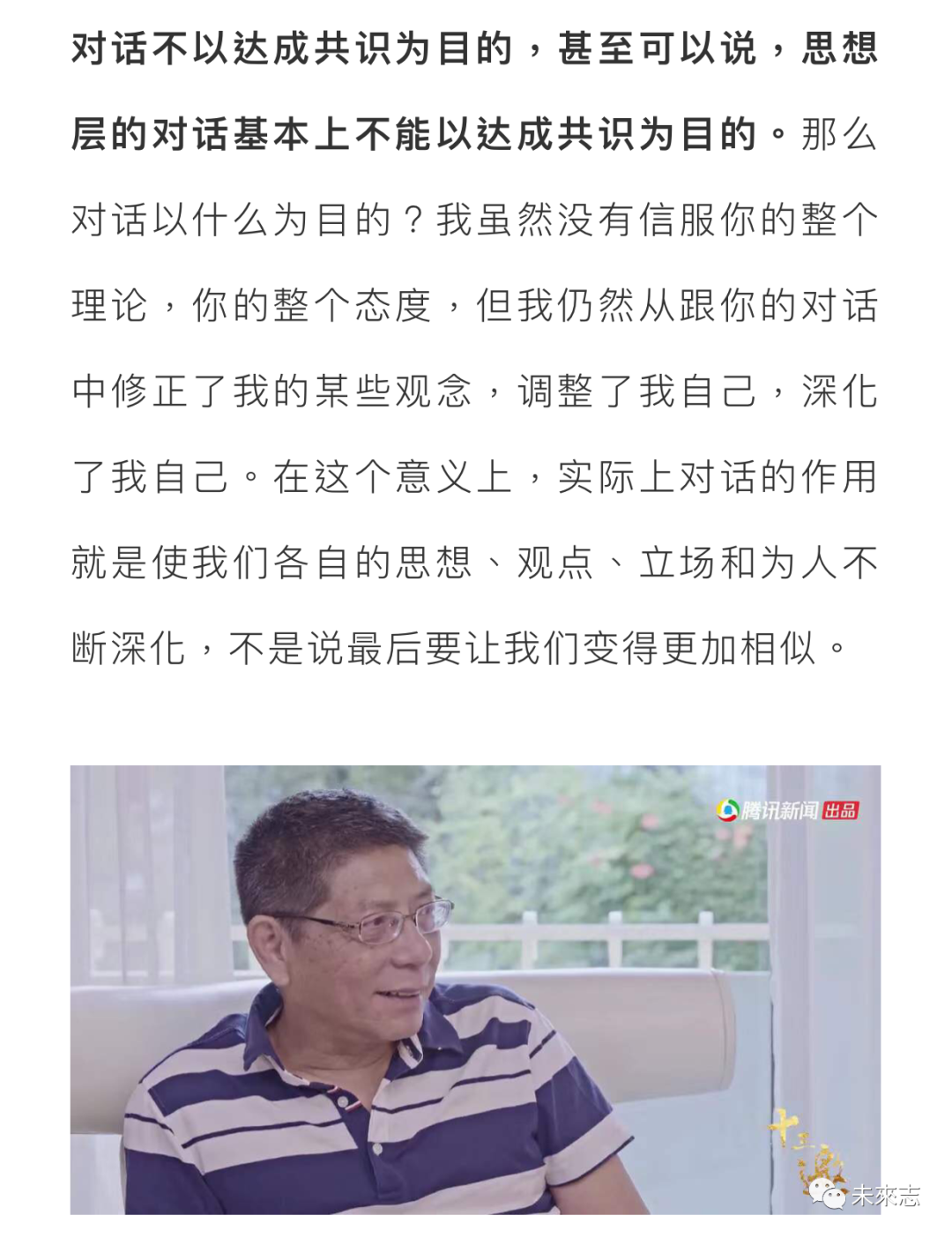
我们知道,对话是哲学的最初形式或者说“母体”,而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洞见”(insight)和“澄清”(clarity)以及“理解”(understanding),换成隐喻的说法也就是,也就是启发和引导人们“看得进”、“拎得清”和“站得稳”,正如“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立得定,方见脚根”这句话所刻画的高阶境界。
作为在国内有广泛知名度的两位学者,尤其是其中一位还是被媒体誉为是“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对于“对话”的阐释竟然是如此得“看不进”、“拎不清”和“站不稳”,实在是令人不安。那么,我们可以说,由于事实上项飙与陈嘉映两位先生并没有达到这次“对话的精神”主题所内在要求的主体性水平,反而是叫“聊天的精神”(东拉西扯)会更贴切些,不是吗?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