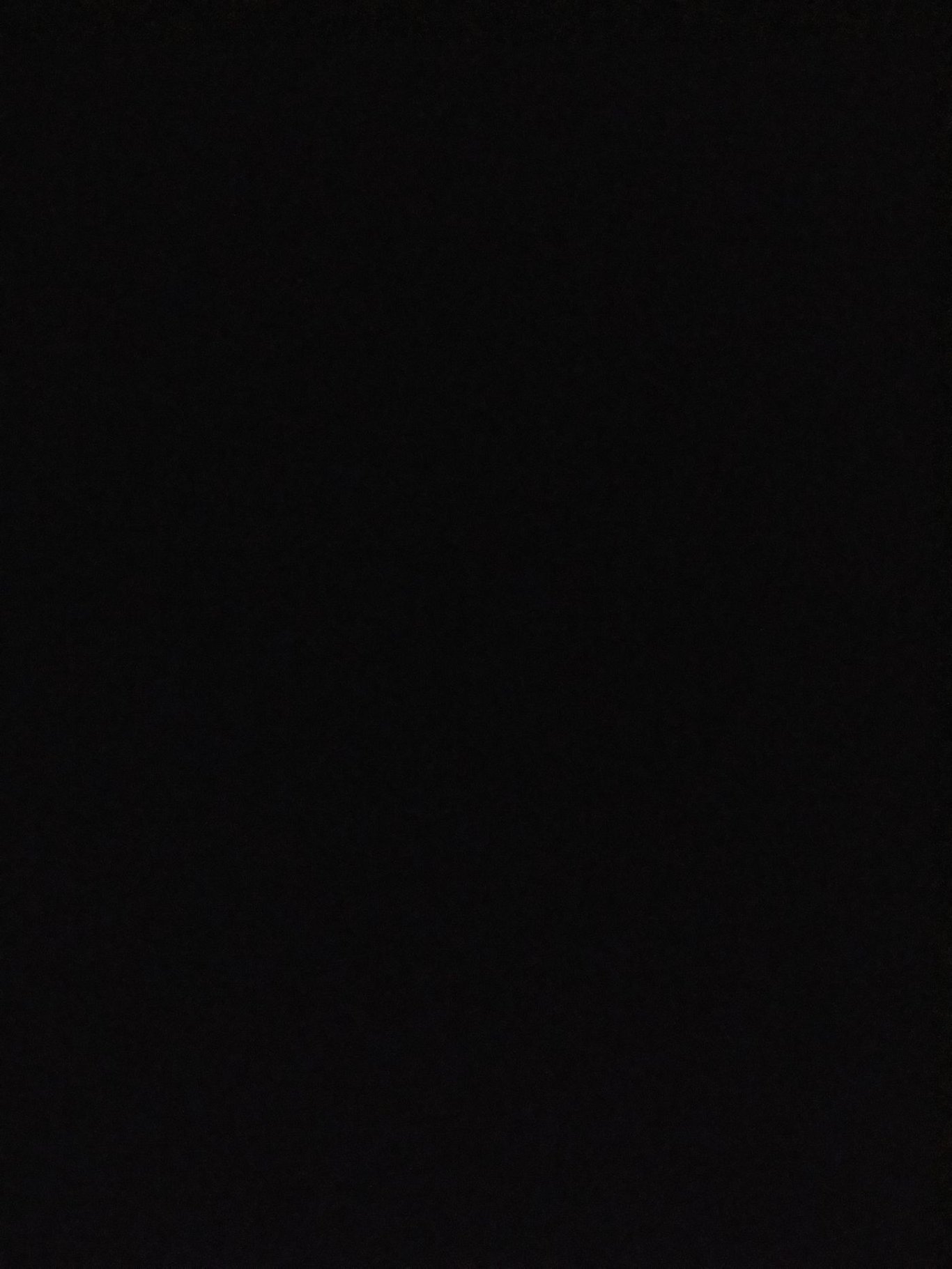
写点小说
一刻也不能分割
这是他第一次来乌镇。
虽然这里离自己待的城市并不远,整个旅程只需要坐上半小时的火车,在桐乡高铁站下车后,再坐上塞满旅客的景区专线公交,沿着尘土飞扬的环城公路花上个把小时穿过城市边缘的工业区,总共不用两个钟头——但他还是第一次来这里。
在景区附近的小镇车站下车,他站在路边举目四望,南方小镇的街道上来往着全国各地的不同口音,街道两边的店铺大多是当地人开的,他掏出烟来,可是看看四周,宽广的街道上难找一个垃圾箱,想到这里是著名的国家5A级景区,他想了想还是把嘴上的卷烟放回了盒里。
他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旅游。半个月前,卢边月给他发来一条微信,说是过些天从北京来杭州出差,忙完后想去乌镇玩玩,问他有没有时间同往。他本没想来,只是客套而随意地回复道:到时候再说。
晚春的风吹来,天气已经有些偏热,在太阳下站了没多久,他就觉得皮肤上有些黏滋滋的。他掏出手机来,在街上拨通卢边月的电话。
“你在哪呢?”
电话那边声音非常嘈杂,人声、扩音喇叭的嗡嗡声,还有流行音乐的旋律,她大声说着,“我在景区里面呢,人特别多,你到了吗?”
“刚到镇外的车站。”他看看时间,说,“你什么时候出来?”
卢边月说,“你进景区来吧,我订了这里的饭店,一会一起吃饭吧。”
他都快想不起来卢边月的样子了。他只依稀记得她走的那个下午,天光暗淡快要下雨,他们甚至都没有怎么说话。卢边月在前一天晚上就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他看着她刚洗完澡的身体在房间里转着圈,从架子、书桌、洗手间里一件件收起书本、电脑、充电器和电动牙刷等等等等,他突然站起来拉住她,吻着她,她只象征性地挣脱了一下,很快就和往常一样和他倒在了床上。
那一夜他们做了一次最漫长的爱,两人都精疲力竭地睡去,以至于第二天下午醒来的时候,他看到她已经拉着行李箱准备出门。
他问,“这次去多久?”
她说,“说不准,应该不回来了。”
他又问,“吃饭了没有?”
她说,“路上吃吧,快来不及了。”
他还想说点什么,但还是有点困,他眯着眼听见窗外传来一阵阵闷雷,于是说,“带伞没有?”
她说,“你那把伞我先拿走了,回头给你寄回来?”
他说,“不用了。”说罢又倒头睡着了。
他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不时有松散的旅行团队伍、三五成群的散客和结伴而行的情侣从他身边走过,也有拿着手绘地图的野导游凑上来,主动而热情地介绍当地有名的饭馆和民宿旅店。他对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样的镇子在南方随处可见:上世纪80、90年代的建筑风格,墙面贴满马赛克的矮楼、用美工字体刷在墙上的化肥广告、供销社开办的五交化商店、在坐着无所事事的老人的茶馆门口,几只煤饼炉子上坐着的钢精罐里,堆满散发出香料气味的茶叶蛋。站在街上一眼放去,社会主义美学风格和当下的新农村景观相得益彰。
他想起自己老家的那个小镇子,比这里要小一些,人口也少得多。每天早上露水还没在青石板路上消失的时候,街上的人们就要开始一天的生活。只不过那里并没有什么著名的旅游景点,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陌生人,谁家出了什么事情不消一天的工夫,就能从街口传到街尾。他那会只有十岁,经常在下午的后两节课逃出校门,溜到镇上唯一一家有三台游戏机的杂货店里,把省下的早饭钱交给老板。后来因为父亲调动到了城里的国营工厂,他和母亲也搬到了父亲单位分配的筒子楼宿舍里,他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第一次学会了饭前便后要洗手,也第一次开始自己一个人睡。
工厂宿舍的大院里,没有男孩,他只能跟一群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一块玩,她们嫌弃他的口音粗野,不讲卫生,所以在游戏的时候,他往往在边缘的位置——女孩子们跳牛皮筋的时候,他负责撑住皮筋;她们在阅览室读故事书的时候,他读那些大爷们才看的报纸。
他并不在意,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他是一个男孩子,自然要玩男孩子才玩的东西,城里的游戏厅比小镇上的豪华、热闹得多。只有在零花钱花完,或者下雨天的时候,才只能将就着跟这群小姑娘玩。嘴上薄薄的绒毛和渐渐突出的喉结,让他根本不屑于那群女孩的嫌弃态度。
他一边看着手机上的导航软件,一边往乌镇景区的方向走着。阳光强烈,空气干燥。卢边月在微信里发来一个定位消息,她的位置刚好在离景区入口不远处的地方。越接近景区入口,路上的游客就越多,各种口音交杂在一起,聚集成一条无形的河,在离地两三米左右的高度,缓缓流淌。路边不时还出现一些零散的小型工地,大多是做市政管道维护和路面整修的,手持打桩机、柴油抽水机、压路机的轰鸣,这些声音突然激荡起一道巨浪,扑过街道上两边低矮的楼群,又漫过镇子外缘那些还顶着黑瓦的老房子,浩浩荡荡地向四面八方外一望无垠的田野、水系网络和少女刚刚开始入熟的乳房般隆起的丘陵奔突而去。最后像露水一样,消失在杭嘉湖平原的每一片草叶、每一瓣苞芽、每一片水田旱地的塑料大棚上。他看着它在自己的眼前打着旋儿聚拢,然后又慢慢松弛,散漫地降落在地面上,被人踩在鞋底,发不出一点声响。这一刻,他感到舒服多了。
在景区的入口,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他随着进门的人流向前游动,他自幼会水,但是泳技却算不得多好。上大学时,曾有来自北方的同学问他学游泳要多久才能练到“中流击水”“弄潮搏浪”的境界,他狡猾而负气地说,“聪颖如君等,自然是多多益善。”那同学不服,立时与他打赌。一天夜里,两人趁着夜色,私自潜入泳池比赛闭气。万万没想到,那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一下水居然灵活得像一条鱼。他埋头在水中,睁眼瞧去,见到那同学贴着泳池底部的瓷砖,双腿上下摆动,在他面前转着圈。一道月光铺在水面,水中光影交错,耳边似乎传来遥远的歌声,仔细辨认,旋律有些熟悉,再一想,居然是《我和我的祖国》。那首歌他自然是熟悉的,从小到大每一次学校组织文艺汇演,都是最有生命力的保留节目。水面上有风吹过,晃动的波痕搅动了水下的世界,那同学回头也看着他,突然笑了一声,他有点不敢相信,但确确实实在一池子清水里听到了混混沌沌的笑声。然后,那同学居然张嘴在水下唱起歌来,“......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入耳中,只是在水中比平日听到的更低沉厚重,虽然歌唱者近在眼前,可听起来是那么遥远绵长。渐渐地,人声越来越小,只剩下一段重复着的旋律不停回荡,池水随着旋律也摇晃起来,碎裂的月光跳动着,闪耀着,四周渐渐黯下去,只剩下那些跳跃的光点,好似一道浩瀚的银河。他不由地想跟着耳边的旋律接着唱下去,刚张开嘴,一大口凉水灌入肺里,火辣辣地痛疼起来,他再也看不清眼前的一切。又过了一小会,慢慢地肺里凉润了起来,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浑身肌肉都松弛开了,他在水中感受到了小时候在乡下野地里奔跑,清凉的微风拂过他光溜溜的身体时的熟悉感觉。他终于可以哼唱出刚才没有唱出口的歌了,他虽然无力出声,但可以在心底用力而无声地歌唱着,那星光、那缓缓转动的宇宙也渐渐清晰起来,他正向无限深邃的银河深处渐渐飘去。突然,一只海豚托住了他软绵绵的身体,他下意识抓住了它,直到被它驮出了水面。
越靠近检票口的队伍越显得臃滞,过了很久,他才艰难地从两台检票机中间那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通道钻出,赶紧快走几步,拥挤的人群快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像脱水而出的鱼一样坐在一条长椅上大口喘气,有一个负责维持秩序的志愿者上来关切地询问他是否不舒服。他摆摆手,用一个微笑回应着。然后掏出手机,打开地图,检索着卢边月所在的那个饭馆位置。身边接二连三地走过许多游客,有不少父母带着蹦蹦跳跳的孩子一起来玩的,大人们一手撑着阳伞,一手牢牢抓住孩子的手,也有情侣或者朋友结伴而走,举着造型古怪的自拍杆,像手持望远镜登上新大陆的殖民者,时不时地在路边停下来自拍。
这时卢边月打来电话,问,“你到哪了?”
他说,“刚进景区大门。”
她说,“你看到我发你的定位了吧?怕你找不到地方,这里人有点多。”
他说,“我看了,离得不远,大概再走几步就到了。”
她说,“行,你进了饭馆上二楼,我订了靠窗的桌。哎,你要不也点几个菜,我把菜单照片发你?”
他说,“不必了,你点好就行。”
她说,“那行,你看看喝点什么?橙汁?啤酒?要不整口白的?”她笑了出来,她知道他的酒量一直很差劲,基本属于一口就能交代的类型。
他说,“别,你知道我喝一口就得倒。”他也笑了,他想起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在朋友家吃饭,喝多了几杯。回来的路上内急,找了根电线杆子解手,完事后居然用皮带把自己扣在了电线杆子上。
她说,“行,那你快点,这饭馆人太多了。”
挂了电话,他起身钻进人群里,沿着一条河边的观光步道向前走去,不停地有年轻女人的笑声、聊天的对话、尖细的童音、老人的咳嗽,从他的头顶飘过,它们聚集成一个如胎儿般微微颤动的漩涡,只有正午暖热的阳光照耀着他,也无声地照耀着他们。
趴在水池边的地砖上,他一口一口把身体里的水艰难而痛苦地吐出来。北方同学用力拍着他的背,让他舒服了不少。眼前渐渐明亮起来,月光照着两具湿漉漉的肉体,他看着那同学身上结实的肌肉,黝黑的皮肤上挂着一层亮晶晶的水珠。他脑袋昏沉,伸手一巴掌拍在同学的背上,那同学说,“你他妈吓死我了,撑着点,我背你去医务室。”他趴在他的背上,手按在一块嶙峋的脊骨上,那突起的弧线,分明是一块鳍的形状。一路上,校园广播的大喇叭还在播放着晚间的节目,一个女生念着节目的收尾词,“忆往昔峥嵘岁月,寄来日锦绣未央,在此新中国60周年的伟大日子里......”寂静的校园里没有了行人,那声音陪伴着两人一路向着远处校医务室慢慢走去,它在夜空里盘旋上升,消失在9月的沉默的星空里。
此后两人成了朋友,只是再也不敢靠近运动场边上的那片泳池。
卢边月坐在他对面,临河的窗户里飘进蒸腾的水汽。她说,“看来我没挑好时候,这里到处都是人挤人。”
他说,“这鬼地方一年四季都少不了人。”
她问,“你现在还在那个美术馆上班?”
他说,“嗯,混口饭吃。”
她又问,“平时还拉私活?”
他说,“别说那么难听,这个叫独立策展人。”
她笑了,说,“几年不见,你还是这个样子。”
他说,“倒也有些变化。”
她示意服务员上一壶茶水,顺便去催问下厨房快些上菜。那服务员小姑娘,穿着一身蓝碎花左襟衫和灰色直筒裤,利索地应了一声,转身下楼去。他抬头瞥了一眼窗外,深绿色的河水飘着一层新鲜的,刚刚从半空中飘落的蝉鸣声。她问,“什么变化?”
他说,“想通了一些事情,也学会了讲市场规律。”
她笑着说,“如此说来,你现在干的不错——至少比以前应该有些起色。”
他说,“说不上混的好,但也饿不着。”
她说,“我老公现在也搞些当代艺术投资,他还惦记着你。”
他说,“上周他还给我发微信照片来着,好像是个装置艺术五城联展的活动吧?搞得挺不错,可惜这块我不熟。”
她说,“本来他准备跟我一块来,顺便看看你,可是临时有事耽搁了。”
他问,“下次我上北京找你俩去。”
她把眉毛一扬,说,“算了吧,回回都说下次来。上回你说了要来北京,他把公司里的董事会议都给推迟了,一大早出门亲自买菜,结果你又放我们鸽子。”
他有些不好意思,说,“这次是真的,我说话算话。下次到北京我做东给你们赔罪。”
她说,“这几年下来,我算是明白了,你们搞艺术的,压根就不会说实话。”
他说,“上次确实有点事给耽搁了,这回我可以立字为据。”
她说,“怎么搞得我跟逼债的黄世仁似的——你现在空口白话,我也记不住。”然后掏出手机来,给她老公发语音,“我跟你那艺术家哥们吃饭呢,他可说了下次来北京请咱俩吃饭,你记着点。”
他看着她现在蓄起一头乌黑的长发,干练地扎起一个马尾,倒显得年轻了一些,只是眼角多出了几丝细纹。窗下游过几条观光的乌篷船,有一个孩子兴奋地大叫着,他又发现她的脸廓圆了不少,虽然画着淡妆,但还是掩饰不住一丝疲倦。他的目光从她的头发移到因天气闷热而有些泛红的脸颊,然后又迅速扫过雪白脖颈上的一块翡翠胸坠,跳过青黑色连衣裙上装里的饱满胸脯,最后停在了她手指上的婚戒。这个曾经让他最苦恼的东西,现在倒让他感到有些放松——这些年来只有它没有变,而这个面前的女人,它曾经的、现在的主人,也在记忆和时空的接缝处对上了号。
还没有上菜,桌上只摆了几碟奉送的炒豌豆、花生米、瓜子等零食,他端起茶杯来又放下,他想抽烟,但是景区里好像已经完全禁烟了,他又觉得在这个小小的包座上有些别扭。她正在跟自己的丈夫、他的大学好友说着一些事——家里的事、工作上的事、还有一些他们共同的过去的事。他不愿去想另外那些不能在三个人面前公开的过去,只好扭头在窗户外盯着那些声音,包裹着湿润的水汽,满满上升,四处飘荡。突然他看见有个五六岁大的小男孩,举着一个冰激淋骑在父亲的肩头,那个年轻的母亲,正在一旁哼着歌逗弄他,“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他心里一紧,那个熟悉的旋律在飘过时候抓住了他,他轻轻地跟着哼唱起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到这里,他却如何也想不起歌词了,这首歌本来是很熟悉的,他听过无数次,每一个字都很熟悉,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换气,都很熟悉,他想起在泳池里溺水的那个晚上,在朦胧的水底,他都没有忘记这首歌,但现在他却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了。
卢边月和他结婚的时候,他当时正在四川,跟随一位艺术家去寻找多年前散失在凉山彝人村落的三十多箱石画版,并没有出席在婚宴上,也没有亲眼看到他们如何挽着手走过红毯,又如何交换了戒指。那几天因为长途奔波,加上山里的居住不大方便,时常风餐露宿,工作进展又不顺利,他无比怀念着阴雨绵绵的上海。那位艺术家——现在早已病逝——看出他的不快后,决定在暂住的寨子里多待几天,给他一段时间调整。结果有一天夜晚,他们从隔着一座山的另一个寨子返回的路上,天降大雨,当夜他就发起了高烧。寨子里原有一个赤脚医生,但是那几天因为嫁到城里的女儿生产,早早就离开了寨子。艺术家急的团团转,好在借宿的那家彝族老乡请来了他们的苏尼,忙活了一晚上,居然第二天就退了烧。回上海以后,他却发现,自己能看见一些在空中像雾气一样弥漫着的声音,比如城市里最常见的公交车报站声,形状齐整,排列有序,而那些大小不一,浓度各异的不同方言口音,则要杂乱的多。起初他以为是眼睛的毛病,自己的祖父、父亲,都不同程度有先天性的青光眼。但是上医院检查了几次,他就放弃了。一是因为并没有检查出什么眼疾,二是因为医院里那些痛苦的声音着实有些吓人。远远地,他就能看见那幢高大漂亮的就诊楼,像通往地狱的检票站那样耸立在一片现代文明的摩天大厦中间。
卢边月问他,“你哼哼什么呢?”
他的思绪被拉了回来,忙问,“你听见这首歌了么?”
卢边月问,“什么歌?”
他说,“《我和我的祖国》,你还记得吗?‘我歌唱每一条河’后面是什么词来着?”
卢边月也有些无聊,于是加入这场回忆歌词的游戏里来,她从头开始,低声哼起来,她的声音很轻,落在桌面上的时候像一片飘落的蒲公英,“......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一条河.....哎呀,我也忘了。”她有些沮丧,但又一直紧锁着眉头,努力去回忆着。
他看着她两条被仔细描画过的眉毛,它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原来的样子连他也不记得了。它们上一次在他面前锁在一起的时候,他和她正赤裸地在沙发上,紧紧贴在一起。
它到底是什么呢?曾经熟悉的,或者说曾经围绕在生命中——尽管它并不显眼——那些歌词其实也并不重要,但它确实存在着。这不属于他,但是他拥有过的。但现在它消失了,也许是暂时的——经常有类似的经历,比如正在琢磨的一件事,突然在脑海里凭空消失,但往往在此后的某个瞬间,在你不再注意的时候,它重新浮现出来。比如大凉山里淋过的雨,那个卢边月离开的下午,那个北方同学——后来成为了卢边月丈夫的男人背他去校医务室的夜晚。但是此刻,仅仅在遗忘发生的此刻,它的缺席给他带来了不安和波澜。窗下的河水荡开涟漪,他有些焦躁。
卢边月长呼一口气,摊开手无奈地说,“没辙,我想不起来了。算了我先百度一下。”
他条件反射一般地打断她,“不行,接着想!”
卢边月吓了一跳,有些奇怪也有些着恼,但随即就笑了,“你接着想,我接着查,我查到了也不告诉你。”
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还记得它。”
卢边月说,“我知道你们搞艺术的都有些神经质,没事,以前你没少干类似的蠢事。”
但他知道这和“神经质”毫无关系。他只是和它过不去,他甚至也和自己过不去,但除此以外,他没有其他的毛病,和普通人一样上班、下班、挤公交、吃饭。他的祖辈、父辈里都不缺这样的人,它更像是一种基因,一种命运的生物学表达。
两人突然陷入了一种没有方向的沉默。
他向窗外望去,看见了火焰,耀眼而炽烈的白光在空中摇晃,整个世界都在熊熊燃烧。他的视线飞出屋檐,他听见有人在遥远的地方喊着他的名字,但好像还有其他人的说话声。他们窃窃私语商量着什么,它们组织成一个不规则的方阵,匍匐在地面,蛇行穿越水网密布的平原。他想在人群里找到那个母亲,期待她能接着唱下去,帮他回忆起那段消失的歌词,但是人太多了,东北话、湖南话、四川话......无数的声音阻挡在他面前,他越来越急躁,至于深陷在沉默中难以抽身。空荡荡的旋律还在回响着。
卢边月发现他满头大汗、眼睛充血,忙问,“你怎么了?”
他端起茶杯将慢慢一杯热开水,一饮而下,喉结一动一动,然后瘫靠在柔软的沙发上,喘着气说,“天太热了。”
卢边月说,“我叫人把空调打开。”她站起来招呼了服务员,然后在他身边坐下,伸手往他额头上一摸,有一些微微发烫,“你发烧了?”
他说,“没有。”
卢边月说,“敢情是中暑了吧?”
他说,“应该也没有。”
卢边月说,“得了,饭先别吃了,我带你上医院。”
她的身体一点没变,他熟悉那每一寸光滑而柔软的皮肤。她从他汗涔涔的胸膛上爬起来,下床穿衣。他看着她坐在床边麻利地把头发绑在脑后,问,“什么时候走?”
她背对着他说,“五点的火车。”
他又问,“饿吗?”
她说,“刚才在医院里吃了点零食,现在不饿。你饿了?”
他说,“没有。”
她站起来开始收拾行李,边收拾边说,“我得走了,你可以再歇会,今天的房费已经续过了。”
他坐了起来,说,“不了,我跟你一块去车站吧。”
她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你不会是装病的吧?”
他一下站了起来,说“你看像吗?”
空调的凉气轻轻地吹在他光溜溜的身体上有点冷,激灵地打了个哆嗦,他又说,“帮我个忙行吗?”
她问,“干啥?”
他说,“让他有空给我唱一遍《我和我的祖国》,他肯定记得。”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