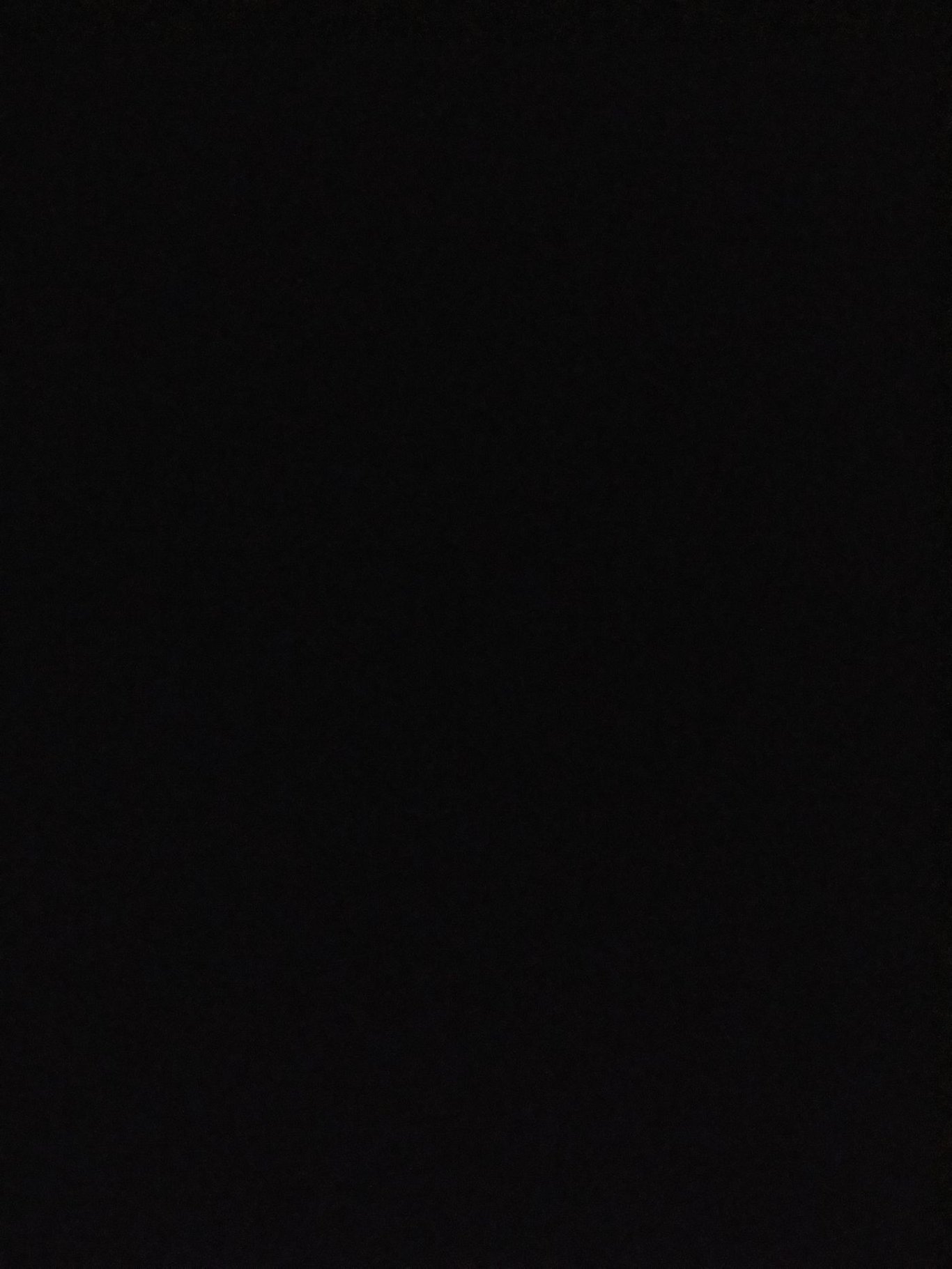
写点小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敢在晚上七点半到九点之间的益乐新村门口跟人吵架,是一件特别让人佩服的事情。
首先你得精通现代汉语中最精妙的各式俚语,对当下流行的网络段子如数家珍,还要从容应对各种口音不一,或高亮或低闷的方言字眼,更要有纳博科夫式的语言敏感和对结构的高度关注——因为经常会有半土半洋的杂交词汇,让你在分神琢磨它的含义时,疲于抵挡正面的进攻——实际上这些词汇往往并没有什么比字面意思更深刻的含义或者隐喻。
那一晚,我在人群的外围看到了这场吵局的尾巴梢,双方选手分别是一个白人和一个卖香辣鸭脖的小个子湖北男人,而他们争夺的赛点正是关于鸭脖的价格是否能跟麻辣程度成正比关系。但遗憾的是我来的太晚,还没弄明白赛况,这场对局就已经结束了。因为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也因为对手是一个外籍人士,害怕因此引来警察,所以鸭脖摊老板并没有坚持太久,很快就主动认了怂。
“我不跟你计较。”他涨红着脸瞥了对方一眼,熟练地打包起食盒丢在一边。
“你还有脸跟我计较?”那个白人也没好气地说,他的汉语说的并不标准,语速却不慢,听起来倒挺流利的。他一边拿出手机扫码付钱,一把抓过那个食盒,离开还不忘说一句,“要不是这里是外国,我早把你摊子砸了。”
鸭脖老板听了,突然没憋住笑,“我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还没脑子。这里他妈是中国。”又说,“你敢动一个试试?我让你走着来,爬着去。”
那个白人一愣,扭过脖子说,“废话!我他妈又不是中国人。”人群里也开始有人笑了。
这个湖北人其实我知道,他白天在两条街外的一家租房中介里当客户经理,每天的活无非就是骑着电动车带人去周边的各个小区里看房,晚上回来就跟几个老乡一起支个卖鸭脖、鸡爪的小摊——他的几个老乡,也是他的邻居,专做这个。
那个白人,其实我也认识。他就住我楼下,是个德国来的人类学博士,住在这里不知道有多久了,自称是在这里搞一个关于城中村的田野调查。有一次他敲开我的房门,用他别扭的中文告诉我他想借我的笔记本电脑一用。
我还是有些吃惊的,因为这个充满市井气息的社区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受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成为我的邻居。我选择住在这里,并不是只是因为房租便宜,更有一大部分是因为这里充满人间烟火的生活气息,窗外充盈着海浪般层叠交替又相互消融的市声。这让我在写作之余,能迅速从作品里抽身出来,感受到自己肉体的实在,和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共同生活状态。但是现在有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站在我的面前。配合着手势告诉我他是我的邻居。这他妈实在是有些荒唐,按说派出所怎么能让一个外籍人士独自一人居住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呢?但是作为国际化现代城市的杭州,作为杭州市西湖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样板小区,它自然应该值得有,也应该有这样足够的胸怀和自信,让外国人住在这里。
我虽然犹豫着,但还是把笔记本电脑借给了他。他摆摆手说只是想发几封邮件,不占工夫,鉴于是借用私人电脑,他想在我这里直接使用,也好让我放心。他在对话中非常熟练地使用着“您”、“贵”等敬词,我听了一会打断他说,“中文跟谁学的?”
“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学过中文入门课,上大学之后认识一个朋友是台湾人”他顿了顿,又跟我说,“中国的台湾。”
我把他让进房间,说,“倒听不出来你有台湾口音。”
他说,“实际上我练习口语的教材是央广电台的录音。”说着他一本正经地学起了韩乔生的播音腔。
我的房间是一间小小的隔间,只够塞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写字台:床既用来睡觉,也用来会客以及堆放衣物和几十本书。而写字台的用处更大了,既是餐桌,也是工作室,它的抽屉原有一把锁,坏了之后我重新买了一把,于是它又成了我的保险柜和药橱。一进屋,不需要转头就能一眼把我所有的家当都看穿,他很高兴而自觉地在床边坐下,顺手拿起一本书来翻着,说,“房东说您是个作家,鄙人很好奇。”他对着正在打开电脑的我说,“平时在小区里很少看到您,写作是您的专职工作吗?”
我说,“我前几天刚搬来。另外我也不是什么作家,只是写一些小说赚点零花钱。”
他说,“忘了自我介绍,鄙人来自德国,名字叫Lukas,中文名字叫卢楷兹。”他手里翻着一本书皮起翘,书脊上贴着厚厚一层补丁的《布恩雷蒂罗之夜》说,“这本书能借鄙人看看嘛?”
我把电脑交给他手里,然后打开窗户点上一支烟,接着说,“你是干什么的?”
卢楷兹说,“鄙人是搞社会学研究的,在这里做一个关于城市化区域发展中微观社区形态的调查项目。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城中村、棚户区的。”
我说,“你的中文说的挺好。听说不少专业的汉学学者,都不见得会说一句中文。”
卢楷兹一边操作电脑,一边说,“感谢您的谬赞。当然,还感谢您的电脑。”
我把烟灰弹到窗外,问,“你们搞这个调查就你一个人?”有一个提着菜篮子的妇女路过, 我就这么看着她慢慢走远,消失在另一栋楼的拐角。
“不是,这是联合国人居署的一项计划,在全球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展开。”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鄙人那位在波恩大学的博士导师邀请鄙人一起参与,最后鄙人选择到中国来。”
“有意思吗?”我问。
“挺有意思的。白天混在人堆里观察,记录,晚上又回来写一些总结,”他又抓起那本《布恩雷蒂罗之夜》轻轻念着扉页上的原版书名,“Las Noches Del Buen Retiro。”
他说,“社会生活不仅是文学写作的丰沛资源,同样也是我们了解自己的最佳途径不是吗?巴罗哈本人就说过自己喜欢在大街上搜罗故事。”
“实际上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巴罗哈,但也不是不喜欢——不那么喜欢,读他的书常常让我感到头疼。”我说,“在你眼里的人是一个群体,一个对象,一个样本,但在我看来我与他们别无二致。”
他已经忙完了他的事情,把电脑慢慢合上放还到桌子上。“您说到了一个让鄙人感兴趣的问题,您与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经验,在身份问题上产生这样的认同并不奇怪,但是它的产生是否以您的自觉意识为前提呢?”
我把头伸出窗外,左右四顾,这时街上没有一个人,更没有讨厌的物业清洁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无聊。”说着,我迅速地把手里的烟屁股弹了出去,它在空中飞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最后掉进了对面的绿化草坪。
卢楷兹起身告辞,临走时又提起借书的要求,我打开门,走廊里空无一人,说,“你借哪本都行,唯独这本不行。”
他问,“为什么?”
我说,“那是偷来的。”
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一个字,那些句子总是像约好似的,在我需要它们的时候躲得干干净净。如果是以往我也许并不那么着急,因为写作于我无非是一种用来消磨时间的方式,衰弱的神经已经取走了我大把的睡眠,于是我得找一种办法,填充那些无所事事的夜晚。久而久之也攒下一些马马虎虎的小说和诗歌,它们在一些地方报纸和民办刊物上转了一圈以后,又变成了烟灰缸里的灰烬和墙角一个个东歪西倒的空酒瓶。
但是现在我需要一笔钱收拾一颗烂了大半年的后槽牙,我每舔一舔那个空洞洞的位置就会感到一点害怕——在这世上,每个人都会慢慢被抽空,只是有的人从肉体里得脏器开始,有的人从精神里的脆弱部分开始,而我会从我的牙齿开始——也许开始是凿开一个虫眼大小的洞,然后慢慢敲下其他的部分。这颗烂牙现在已经所剩不多,我只能感受到它剩下的残垣断壁。我意识到必须要把它补一补,至少为了省去每次进食后清理食物渣滓的麻烦。
两个月前的时候,有一个编辑通过微信联系上我,找我去给一个民间方志编写团队去帮闲,说好等项目结束有一笔两万块的稿酬。我兴趣并不大,因为这种活往往投入与产出难成正比,帐面上的两万块也许需要付出数倍于此的劳动。
第二天是定期取药的日子,我比平时提早了两个小时去医院,为的是顺便看看牙齿。挂号排队,拍片检查,来来回回跑了几个科室。大夫看看X光片,又撬开我的嘴忙活半天,最后说,“补已经来不及了,要么植牙吧。”我问大概要多少费用。大夫说,“手术不大,一次拔牙一次种牙,临床费用大概两万吧,包括假牙的钱在内。”他见我愣着,又拿过X光片摆在桌子上,用一支棉签在上面画着圈,“看这里,看到了吧,牙冠已经烂光啦,只剩一点儿牙根还在牙床上,这个程度补牙已经无济于事了。”又说,“当然做不做这个手术主要看你个人意愿。我只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给出建议。”
我问,“不做有什么影响呢?”
大夫说,“首先影响咀嚼,吃东西不方便吧?其次会影响周围健康的牙齿,在槽骨上发生位移,松动。”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年纪还不大,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好牙口有多重要了。”
我问,“医保能走多少?”
大夫说,“其他诊疗环节都能报,拔牙,治疗牙周等等,最后一步植牙不行。”
我想了想,说。“做,不过要等我凑笔钱。”
大夫说,“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有什么问题方便沟通。”
我说,“不必了,我每周都要来的。比回家都跑的勤快。”我晃了晃装药的袋子,不确定他有没有看清楚。
回来的公交车上,我就在微信上联系了那位编辑。车厢摇摇晃晃,在滚烫的马路上行驶,像太阳底下晒透的一罐巨型可乐,拥挤的铁罐头仿佛随时会爆开,我在手机上写着,“老师您好,上次所谈之事请问现在还需要人手吗?”点击发送之后,聊天框里却多出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我按灭了手机,把头靠在车窗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快走几步赶上卢楷兹,他闷头走着显然心情不佳。我喊了一声,“卢!”
他回头来看见是我,尴尬一笑,说,“祁先生见笑了。”
我说,“没招来警察算你运气好,吃饭没有,一块找个地方吃饭去。”
他举起手里的塑料袋,里面有一些吃的,还有啤酒。说,“上鄙人那吃吧——煮火锅。”
我回到屋里简单收拾了一下,临出门时想了下,带上了那本书就下楼去了。
卢的房间跟我的一样大小,仅多了一个外伸的窗台,他的房里非常整洁,窗边有一个小小的书柜,但上面大多堆放的是一个个档案纸袋,我走近瞥了一眼,袋子上贴着标签纸,从上面那些字母拼写出的人名可以辨认,那是他长期以来采访小区居民的档案。
卢正在水池边清洗一个不锈钢小锅,他探头看我对他的工作成果好奇,说,“祁先生要是有兴趣,一会给您讲讲采访来的趣事,不过还请不要向外透露。”
我把书放在桌上,说:“还是免了,我怕我的嘴不严。”
他笑了,说,“鄙人觉得作家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窥探秘密的爱好。”
我说,“我哪算什么作家。”
他走出洗手间,然后在桌上摆好一台电磁炉、两幅碗筷,在等水烧热的时候,他看到了《布恩雷蒂罗之夜》,显得非常高兴,说,“实不相瞒,鄙人可以算是巴罗哈的铁杆书迷,这本书我读过好几个版本,西班牙语的原版书还读了三遍,中文版的却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点点头,“正好我最近不看,这本借你了。老实说中译本其实翻译得一般。”说着我掏出烟盒,里面只剩最后一根了。当时有些尴尬,他抽不抽烟?如果抽,我是不是也得递他一根?如果不抽,他一个外国人闻得惯中国烟的味儿吗?或者他不许我在他房里抽怎么办?去屋外头?算了,还是憋着吧。
卢从桌子下找出一个烟灰缸来,说,“请自便。”
我说,“不好意思,我就剩一根了。”
他说,“您试试。这里有几盒不同口味的。”
我以为他要请我抽洋烟,正好奇着,他却掏出几盒利群、云烟、芙蓉王在桌子上排开。我突然有点失望,他接着说,“鄙人爱抽这款。”说着举起一盒十块钱的硬云烟。
我问,“你屋里烟味也不重,存这么多干嘛用?”
他说,“鄙人自己抽的少,这大都是采访的时候给别人准备的。我本来抽Davidoff,但这里的人很少抽这种烟,还是用你们中国的本土烟比较方便。”
不一会儿,水已经煮开,卢熟练地加入超市买来的火锅底料,一边用一双筷子搅动,一边把准备好的肉片、鱼丸慢慢放入,顿时一种工业化食品特有的香气就窜了出来。我说,“别玩命搅,盖上盖子改小火焖一会。”
卢说,“鄙人六年前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住的酒店里有一家自助火锅餐厅,一个同事告诉我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饮食方式。把半加工的食材放在锅里现煮,浓汤重辣,所有的味道都混在一起,比如您挑出一颗鱼丸,”他说着捞出一颗樱桃大小的鱼丸子放到我的碗里,“倒不如说期待它是一颗鱼丸,因为在锅里它早就和五花肉、里脊肉、鸡爪、年糕等等其他同胞的味道混在一起了。您得咬开它,尝到内芯里的鱼肉味,才能知道外表上的麻辣鲜香,不过是一种点缀。这就像做田野调查,一般意义上的统计学调查,最容易犯混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错误,但鄙人要做的是要咬开它,用自己的舌头去分离出各种不同的味道,最后发现它的本质。”
“所以你喜欢吃火锅?”我一边问,一边把鱼丸倒回锅里。“但我猜你一定不常吃,或者一般都只是自己一个人吃。因为我不用吃就知道这个鱼丸还没熟,你有点着急了。”
他说,“原来如此,怪不得鄙人一直觉得吃火锅,鱼丸的味道最怪,想不到一直吃的都是生鱼丸。”
我说,“吃火锅就是这样,一样佐料百样吃法。你愿意怎么吃都行,就是要注意卫生。”
我掀开盖子,锅里已经翻滚开了,热水从底部不断涌上来,把辣油沫子推在四周的锅壁上,发亮的不锈钢锅映着两张扭曲的人脸,一个中国人,一个白人,我拿起勺子搅了一下,两张脸全都被油沫子给糊住了。
他说,“鄙人来到这里以后时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惯常熟悉的理论难以适用,但又不是完全不能进入,而是同时呈现着矛盾的两面性。用中国的一个词来说,就是……就是……哎呀,鄙人一时忘了。”
我问,“拧巴?”
他说,“对对对。”
我说,“你又不是中国人,这里离你太远。”
他说,“其实,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需要像一根探针一样进入研究对象,我希望祁先生能做我的探针。”
我说,“你们这么大的项目,也没个中国本土的学者参与?”
他说,“有的,有一个人民大学牵头组织的联合小组,成员来自几个不同的高校,只是他们不像鄙人长住这里,只是定期过来做些采访。”
我说,“我可干不了,我不懂。”
他说,“祁先生谦虚了,鄙人确实非常需要一个助手,能和鄙人一起展开调查研究,没有相关知识背景不是关键,您有您熟悉和擅长的领域。”
老实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擅长什么,大学四年挂科比合格的课目都多,整日在校园里东游西荡像一个野生动物。其实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个工程师,因为修自行车的邻居李师傅会玩无线电,自己能用零件装配收音机。有一次,他送我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我高兴了好几天。后来我把这事写进作文里,老师批改后加上评语:“希望你的工程师之梦早日实现!”我爸看了评语以后特别高兴,逢人就说这个孩子有志气。其实我只想学装收音机而已,但上了初中以后我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学校的两条街外开了全县第一家网吧。
我沉默不语,卢见气氛尴尬,忙说,“上次在您家,听说这本书是偷来的?”
我说,“对。”
他说,“封底上还贴着条形码呢,像是馆藏之物。我猜是您忘归还了吧?”
我说,“我压根没借,用不着还。你要是想学,特别简单。开架的书库一般都很好下手,挑好了书后多转转,找个摄像头照不到的窗户扔出去,再下楼去捡回来就行了。记得扔之前小心看看,楼底下有没有别人。”
他说,“听起来挺好玩,不过这样做毕竟不道德。”
我说,“那回头你看完了麻烦你给我还了。”
他说,“没借的东西怎么还?”
我说,“那我再教你一手,省图书馆那一楼的男厕有个气窗,你在楼外顺着气窗把东西扔进去,然后进去捡起来,这样就能绕开大门口的安检。有一回我找一本《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可是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它哪去了,当时我连着在网上检索了好几个图书馆,最后从一个社区阅览室里找到一本,于是我如法把它偷出来,又放到了省图书馆的书架上。”
他听呆了,好一会才问,“您这么干是为了什么呢?”
我端着碗,头也不抬地说,“为了舒坦。”话刚说完,一块没有熟透的藕片突然卡在了我的坏牙上,正好挤进了那个隐秘的黑洞,疼得我一咧嘴,把嘴里的东西差点全吐出来。
我见他愣着,问他,“给你干活,你付我多少钱?”
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算顺利,卢的工作风格让他的进展非常有限,实际上我建议过好几次去寻求区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但他对拆迁、村民自治等等事务没有兴趣,终日拿着录音笔和笔记本在杂货店、快递点、夜宵排挡和一小块贴满“房东直租”、“单间现房带卫生间”等招租小广告的布告栏那边,像布鲁姆一样毫无意义地转悠——本地村民和外来的寻租者往往在那里聚集。每天早出晚归,作息倒非常规律,十一点吃过夜宵回来后,就把我叫到屋里,一段一段地放录音,然后由我把他听不懂的词语解释一遍。
半个月下来,书橱上的档案袋又多了几只,但他依然很苦恼。我只是觉得很奇怪,这个洋博士似乎什么都非常好奇,他的调查毫无重点,只是不停地记录、分类。对于这个居住着两万多流动人口的社区来说,我们就像一对滑稽的怪人——像埃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那样,所有的工作、讨论、分析只能用来消遣。
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湘菜馆里吃晚饭的时候,喝了一点酒,我的牙时不时隐隐作痛,卢却突然唱起歌来,我匆匆结完账,把他半扶半扛地拉到了街边的小花园里。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他兴致高涨,继续唱着那首《月亮之上》,偶尔有几个路过散步的市民投来古怪的一瞥,还有个遛狗的大爷掏出手机来想拍,我急忙上前抬起手,说,“来中国太久,想家难受,喝多了您别介意。”那大爷听了点点头,放下手机问我,“他听得懂中文不?”我说,“听得懂一点。”他走过来拍拍卢的肩膀,说,“别难受,咱中国欢迎你们,把这当家吧。”我本想把这老头支走再把醉鬼弄回家去,谁知道卢突然开口跟这老头聊上了,“我不想家,我想变成中国人。”老头笑了,说,“那好呀,改天去派出所上户口去,现在便民中心的办事窗口办事方便得很。”卢问,“真的?”老头说,“看我这条狗没有?三年前办狗证跑东跑西忙活大半个月,前两天过期补办,小半天就给我弄妥了。”卢看了看狗,狗也看着他,他又看看我,突然问,“这是不是在骂我?”我说,“没人骂你。”老头也说,“我这是给你打比方。”卢又转头对我说,“我有了个主意。”
实际上他有过好多主意。不久前为了了解小区居民的教育背景,他找到物业公司的一个主管,希望允许他在小区里发一份调查表,主管见是个外国友人,开始挺热情,可是听了半天也闹不清他想干什么。碰了壁以后,他突然说一句,“我有主意了!”然后又上门到物业公司里交了点钱,申请了一个临时的街边摊位,当发健身馆、美容会所广告传单一样在街头开始他的调查,没过两个钟头警察就找上来了。派出所后来给打电话来我吓了一跳,赶到以后,片区民警刘警官,还有出入境管理局的一个处长以及一位市里派来的翻译员正在训他。刘警官看见我,问,“你是来领人的吧?你们什么关系?”
我说,“邻居。”
刘警官说,“不对吧,他说叫来一个同事。”
卢说,“祁先生是鄙人的工作伙伴。”
刘警官说,“你先别说话,我这问事呢。”又对我说,“你也来坐着。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我见这情况,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先掏出烟来给三位警官递上,说,“我住他楼上,他是个洋博士,住我们那正写论文呢。我有时候给他翻译点材料。”
一旁的翻译员说,“他这中国话原来都是你教的?人倒客气,就是不会好好说话。”
另一位处长说,“他的底细我们都清楚,找你来就是给你们俩一块教育教育,毕竟你是他的联系人。”
我说,“是,您说,我好好听着。”
刘警官接过话茬,问,“今天下午他在街上干什么你知道么?”
我说,“不知道。”
刘警官拿过一沓纸来说,“你看看,上街发传单呢。”
卢说,“这是鄙人们的一份调查表。”
处长说,“东西我们也看过了,发出去的单子我们也基本都收回来了,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内容。可是你想想一个外籍人士,在大街上搞这种调查,是什么意思?会造成什么社会影响?你们考虑过没有?”
我说,“这事跟我可没关系——不过他就是个书呆子,您看该怎么处理——他搞这个调查项目跟人民大学有合作,他们能证明。”
处长摆摆手,“人民大学那边已经确认过了,人和项目都没什么问题,”他话锋一转,“不然,我们就要到审讯室里谈了。”
他把烟点上,接着说,“可是你们也要考虑影响是不是,读书人嘛做事更要讲究个名正言顺对不对?不然都像你们这样胡来,出了问题谁负得起责任!”
我忙点头说,“对对对,确实是欠考虑了,今后一定注意。”
刘警官严肃地说,“不是今后注意的问题,你要保证没有今后!”
当场写了两份保证书后,我和卢离开派出所已经是晚上七点。
卢一脸沮丧,我瞪他一眼,“你知道问题在哪嘛?”
卢说,“鄙人不知道。”
我说,“不会说人话。”
刚走出不多远,刘警官打来了电话,叫我们再回去一趟,“不是都完了吗?”我问。他在电话里说,“有东西要给你们。”
我问,“什么东西?”
他说,“你回来就知道了,你不是刚出派出所大门吗?我在办公室都看见你们俩了。”
于是我们又掉头回到派出所,卢不愿意再去那个惩戒了他一下午的办公室,我只好一个人上楼,刚一进门,刘警官把一张精美的小卡片递给我说,“你让他以后把这带身上,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好联系。”
我取过一看,一张名片大小的塑料片,上面印着卢的照片,还有中英双语印着他的姓名、国籍,最后居然还有我的名字和电话。我翻转着卡片,发现它的上下两端都画着警蓝色的条纹,抬头上还写着“西湖区警民联系卡”,我一看,刘警官的办公桌上也放着一张他自己的卡片。
刘看在眼里,解释说,“我自己用多余的空白联系卡打印的。以后带着,在外也方便照应。”
我说,“您说的对,可是把我印上去干嘛?”
他说,“你们不是朋友吗?”
我说,“不是。”
他说,“不是朋友他一进来就说要找你?”
我说,“我们就是刚好住在一栋楼,其他没那么深交情。”
他说,“你这就没觉悟了,人家漂洋过海来中国,为什么单单就跟你住一栋楼呢?为什么单单就找你给他帮忙呢?”
我说,“那不一样,您说的这些都是巧合,这不能构成我照应他的义务啊。”
他说,“你别废话,我们问过人大那边了,这个卢博士,是姓卢是吧,他们的调研项目即将取消,他在中国也待不了多久,你这段时间学习一下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你不是失业嘛。”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的项目要黄了?”
他说,“人大那边负责相关工作的一个老师是我高中同学的朋友。我一问,他就知道是谁了,据说他们第一次合作搞个啥研究课题是在北京天通苑。就是前段日子的新闻里的那个连地下室里都住满人的地方,知道吧?”我不知道不过我还是象征性地点点头。
他接着说,“当时这个洋博士在地下室里住了半个多月,有一天遭了小偷,电脑、手机、现金搬的一干二净。他去报警,当地派出所的领导很重视,毕竟涉外案件嘛。第二天晚上就把人抓住了,还把销赃掉的电脑手机都找了回来,但是收赃的人动作太快,已经把他的电脑都拆过了,里面的资料也全被删掉了。”我想起卢的房间里那一架子的档案纸袋。
他说,“大概就是如此,可能是因此受了刺激,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事情受了刺激,总之此后人就不大对劲。”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精神病了?”
他说,“病倒是没毛病,但是精神状态有些影响。”
他接着说,“你不用管那么多了,你什么情况我们也了解过。在过去,你这种无收入来源的流动人口都是我们关注对象。你只当做件好事,反正人家现在也信的过你。”
我说,“你们都不管?”
他说,“他又没犯事,我们管什么?”
我说,“那这样,人大那边还跟他搞什么合作,这人迟早要出事。”
他说,“架不住人家关系硬啊,他的老师是德国啥大学一个啥教授,是他们这个专业里全球顶尖的几个学者之一。又是联合国人居署在其中牵头,人大除了欢迎,还能说什么?”
我说,“倒是听他说起过——那就在北京待着呗,大老远把这一个人扔杭州来干什么?”
他说,“他自己要来的。人大那边负责的老师也不想惹麻烦,一直不让他单独行动,他大概觉着北京没意思,突然有一天就给人发了封邮件,然后自己一个人溜到杭州了。”
我说,“学校那边不管了?”
他说,“他们已经联系了德国那边,说明了情况,那边申请项目暂停再把人送回去。”
我说,“那他们为什么不来人看着?”
他说,“有人。”
出门来,我把小卡片塞到卢手里,说,“这里有一个联系卡,你拿着。”
卢举起来仔细辨认,轻轻念着:“……联系卡……卢卡……祁……上面还有您呢。”接着摇摇头说,“他们把我的中文名弄错了。”
我说,“废话,你那名字自己取的,人家电脑里注册的名字只有外文,人家是为了方便直接用的音译。”
他说,“他们没有事先问过我。”
我说,“收起来吧,这也不是给你看的,是给别人看的。”
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没什么意思,你不是希望探针式进入吗?怕你一个人遇到麻烦没人照应,上面有我电话。”
接下来几周,卢一直在房间里整理材料,我依然每晚去他那里给他翻译,偶尔也什么都不做,我们抽烟,一遍遍听他采集来的访谈录音。有一天,我如期来到他房间,里面还有另一个男人,穿着简单。卢给了我两万现金,说,“这些时间多亏您的帮助,这笔钱您拿着。”我问,“你哪来那么多人民币?”他说,“这是我自己的钱。”又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的另一个小组成员,人民大学的李老师。”李老师伸出手来,笑着说,“祁老师您好,早听说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特别大,今天特来感谢。”
我和他握了握手,只觉得特别温暖,说,“别客气。也别叫我老师,您要是愿意叫我老祁就行。”接过钱来,我又问,“看这意思,项目完成了?”
李老师看看我,接过话头,“是的。”然后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了。他也许就是人大找来暗中照顾卢的人。
卢很高兴,说,“多亏祁先生的帮助,等成果出版后,我会在书里再正式感谢您。”
我点点了钱,说,“顺利就好。祝你早日完成论文。”
卢说,“接下来的写作工作我得回学校去完成。”
我问,“什么时候走?”
卢说,“一会就走了。祁先生您看这里有什么用的上,可以取走。书柜?”
我想了下说,“不用,我的书堆床上比放架子上更方便。”
第二天正好是取药的日子,我赶紧去医院交了钱,预约上拔牙的时间。这一次快多了,没多一会就办完了手续。回到住处,突然想起那本《布恩雷蒂罗之夜》还未取回,上楼时顺便去敲卢的门,才想起来此处已经人去楼空。
正可惜着那本市面上现在不大好找的旧书,突然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三个警察,带头的正是刘警官。
我正要开口,刘却像不认识我似的,亮出了一张拘留证,说,“祁子虚,我们有事要问你。”接着不由分说,另外两个警察上来把我架住,刘也接过我手里装药的袋子。就这样把我押上了警车。车子呼啸着驶出围观的人群,驶出了小区,又一路驶出了市区。
来到拘留所里,直接带到了审讯室。我像只鹌鹑一样被人安放在特制的椅子里。对面坐着的是另外没见过的两个警察。
我有点懵,问,“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警察说,“别废话,一会问你你老老实实回答。”
我说,“你总得告诉我,我犯了什么事吧?”
另一个警察正在整理着要做笔录的录音设备和电脑,说,“别装蒜,问你什么答什么,自己干过什么你自己清楚。”
两人准备停当就开始审讯,其中一个年轻些的警察说,“你的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套话就不说了,我是省公安厅禁毒大队的,这一位是市刑侦支队的李副队长,你涉嫌参与一起跨国毒品走私案,经由市公安局批准被依法拘留,现在我们要问你一些问题。”
李副队长年长一些,他接过话来说,“祁子虚,你年纪不大,过去也很本分,也许只是一时糊涂,希望你能及时认识错误,积极配合我们调查。”
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忙问,“两位警官,你们到底要问什么?”
他们对视了一眼,李副队长接着说,“你三个月前是不是接触过一个叫卢卡斯的德国人?”
我说,“是。”
李副队长说,“你们这段时间里都干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卢虽然一直强调自己在做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调查,但是在我看来他的工作既没意义也么有什么实质内容。询问室唯一的窗户正在我的对面墙上,夕阳斜照进来在另一边墙上缓缓向上移动,玻璃窗上有几道裂缝,但还是被擦得很明亮。我想起那天卢在公园里说起他的“主意”,又想起他的研究课题,想起他搜集来的小区居民访谈样本,其中最好玩的,是一个在银泰商场里卖女装的四川姑娘,她最大的愿望是学画画,还上过美院学生课外兼职的私教。抱歉,这里“上过”仅仅如它的字面含义,我之所以觉得她有趣,只是因为她那浓重的四川口音的脏话里存放了一群人的热烈和柔软。在无数个深夜,有无数的醉鬼、失业者、失恋者、因为超载被罚款的大车司机、丢了包裹被投诉的快递员、耽误了送餐而被责骂的外卖小哥.....在我们的楼下,吵骂或者痛哭,我和卡也无数次支起耳朵,从他们穿插着无数俚语脏话、难成整句的线索里,掌握那些不幸。
可是我们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呢?谁能知道。谁能知道一个飘洋过海而来的洋博士和一个失业独居的文学爱好者,正在窥视着那一扇扇整齐划一的窗户的背后。这有时候让我很内疚,很有负罪感,在早晨刷牙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在如厕的时候,它总是在我的面前凝视着我。有一次我跟卢谈起这个问题,他很坦诚地认为这是一种知识精英的心理包袱,它是“圣母病”的反面——从身份认同的问题上他就认为我天然地持有这种精英意识。
它也总是像警察一样问我,“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