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專注演戲和創作的躁鬱病人 在Matters神出鬼沒 IG:@ettachanchan YT: 努力生活的大嬸演員
(六) 冷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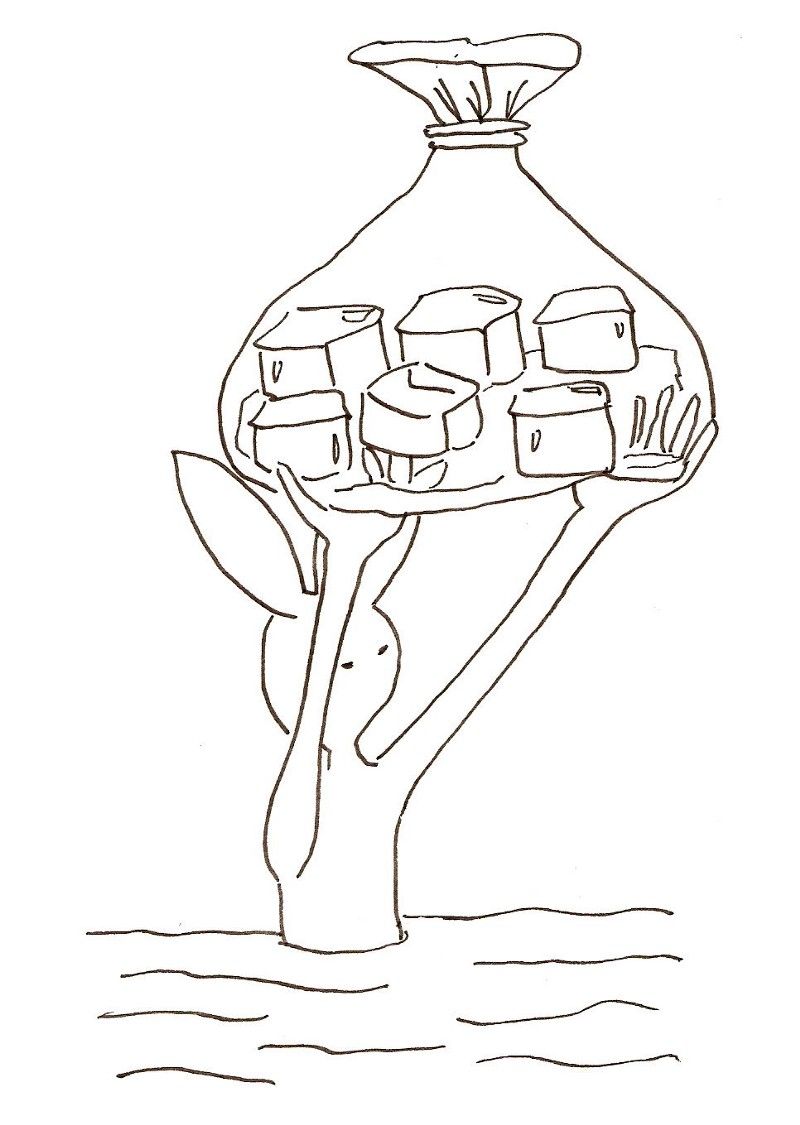
S到埗後的第二天是星期日,B約了她的同事和我們午餐。我哪有好心情和不論是內容或是口音聽不明聽不清的他們吃飯。雖然是Sophia坐在我旁邊,仍然是沒有心情,沒有像第一次見她時那樣和她閒聊。我就是專心吃東西,有時又作狀望望正在說話的人。S則顯得很雀躍的在說B如何好人,是她好朋友,又倚在B肩來個小鳥依人。她的如小女孩般的態度令人難受,又不是十來歲,撒這樣的嬌使我汗毛直豎。好不易吃完飯以為可以回去自己安靜的看看書或聽歌抒緩一下緊張的神經,回去是回去,但是是大夥兒的回去,我依然是像陌路人的跟著他們。B家不大,我又沒有自己私人的空間,只好呆坐一旁「看」他們聊天。
我呆到他們終於走了,但還是在呆著,B和S沒有主動的和我說什麼,我也不想和她們說什麼。上了一會兒網,心情越來越差,很掛念爸爸,他一定沒有想過我會在一個他也認識而且以為是可靠的朋友的家中正在受著委屈。因為實在太辛苦,我拿了日記簿,打開陽台的門,坐在地上,寫出混亂的思緒,不停寫著,眼淚也不停的流,但S和B好像聽不見我哭,但屋子小,根本沒有這個可能。她們依然邊說笑邊在煮甜品心太軟,但她們「心太硬」。寫了許多頁以後,那股委屈還在,而且越來越烈。我走到陽台外,自言自語,才到了英國兩三天,還未上課就這樣,我真不知除了哭還可以做什麼。S和B的談笑聲不絶,真的受不了,我又已哭得非常累,乾脆的躺在陽台的地板上。我是不是不該來英國寄人籬下?自己有情緒病,根本就不可以離開香港太久嗎?我要想方法冷靜下來,我不相信自己不能處理情緒。於是去倒了幾杯冷水,一口氣喝完。之後拿乾淨衣服準備洗澡,聽見B在她房間神神秘秘傾電話,我沒有理會,也不到我理會,趕快去洗澡。這一次花灑的水居然是暖的,如果這時水是冷的會更合適些。
洗完澡,抹著濕濕的頭髮,便邊唱著歌邊開啓電腦準備上網。這時我發現B不在家,S神色古怪,我心感不妙。問S︰「B是不是去了報警?」S回應說︰「沒有。」我沒有再追問B去了哪裡,管她的,繼續上網寫網誌。正當我聚精會神在電腦屏幕上,眼角見在人來了還說了聲 「Hi」﹐我沒意識很快的回應了一句「Hi.」。那人走近我前面,我才去留意他。第一個反應是以為是B的朋友,但認真的一點看他,是一個南歐裔身穿綠色救援人員般的制服,肩上背著一個很大的袋,那袋似是盛滿了醫療用品,因為我見有類似氧氣喉之類的東西在袋的外頭。在他身後有一個女警,雖然我從未見過英國女警是何許樣子,但是她的表情和穿著上一件未見過的制服令我知道她就是女警。
不消五秒,我被屋內全部的四個人包圍著。那兩個人已知道我的名字,女警好像很親切的說︰「Rain,你好,我們來幫你的……」我咬牙切齒的望著B,連名帶姓直呼她最不喜歡別人叫她的中文名,加後加一句「…我會好憎你!」之後我和那女警說︰「我沒有事你可以幫忙。」女警還想繼續說些什麼,我就乾脆跟她說我英文不好是聽不明白她說什麼,她重覆的說不相信我英文不好聽不明白她說什麼,不停的說︰「請聽我講…。」我立即戴上耳機將音樂聲量調高,不想聽任何一個字。可是這是沒用,女警蹲在我前面繼續游說我聽她說。而在較遠方的那個綠色制服人和B的對話,我更聲聲入耳,字字清楚。「可否給我看Rain的藥?」B拿了我放在枱上的藥盒給他看。「沒有藥名,我不能確定是哪一種藥的。你有寫上藥名的藥袋嗎?」「我不知她的 “Drug”放在哪裡?」「不是,是 “Medicine”。」 我突然對綠色制服人的細心非常感激。但是這感激是不足以令我對他們來「幫我」這事上態度軟化。所以我繼續不理他們,僵持的局面他們是沒有方法打破。我心中暗叫自已必須要沉著氣,不哭、不大吵、不大鬧、不做他們覺得異常的事,表現安靜,雖心不靜的邊聽著隨身聽,邊打我網誌。我把此刻的情緒一字一淚的打進網誌中。擾攘了好一會,他們是拿我沒法子的。女警鄭重的問了我一句︰「你是不是不需要我們的幫助?」我除下耳機,同樣鄭重的回應她︰「是。」於是他們走了。
在他們關門離去的一刻,我加多兩分力度,叫自已冷靜,一分也不能鬆下來,要繼續沉著,不理B和S會在細語討論我些什麼,要冷靜到令她們害怕。隨後我發了個簡單電郵給一個我信賴同時認識我和B的朋友,沒頭沒尾重點式說了剛才的事,因為已經沒有多餘氣力去組織文字讓他清楚明白事件始末。其實好想打電話給他,可是絶對不行,聽到他聲音,我一定山洪缺堤。發完電郵,關上電腦,舖好床被,關燈去睡。在被窩中繼續「冷靜」的睡,沒想過可以哭,因此不消多久便睡著了。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