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nect the dots.
幻影公众(Phantom Public)
副标题: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激励早期互联网的深刻的民主愿景?
1964年,加拿大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宣称“媒介就是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同时,他称媒体(media)为“人的延伸”(extensions of man)。五十年前,这些论断的挑衅性足以让麦克卢汉成为反主流文化的名人。如今,这一切似乎都有些平淡无奇:无论好坏,谁不觉得他们的智能手机是他们的一部分?媒体扩展了我们——使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善于交际,更有见地,更有权力——这一观点不仅仅是普遍存在的;这对于促进数字经济或理论家乔迪·迪恩(Jodi Dean)所称的“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至关重要。
尽管麦克卢汉的作品已经过时了几十年,但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人们对他的理论重新产生了兴趣,有人说,麦克卢汉从不害怕做出全面的声明或预测。麦克卢汉想象一个巨大的电子网络环绕地球,通过电影、电视、广播、电话和印刷机,人们可以在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中相互交流。麦克卢汉在其1964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理解媒体》中特别乐观地写道:“今天,计算机展示了瞬息之间将一种代码和语言翻译成任何其他代码或语言的前景。简言之,计算机以技术给人展示了世界大识大同的圣灵降临的希望。”这将导致“普遍的寰宇意识”的展开。
今天,即使你不是一个有证可依的麦克卢汉主义者,你也会相信媒体的形式有其固有的政治性。许多学者和权威人士认为,互联网的兴起导致了传播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尽管当代的一些批评家对这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提出了质疑,但认为新媒体与理解政治无关的观点同样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对数字网络和电子媒体时代的权力运作方式进行更具历史性的分析,并对当权者故意掩盖他们通过这些渠道的影响力的方式提出更尖锐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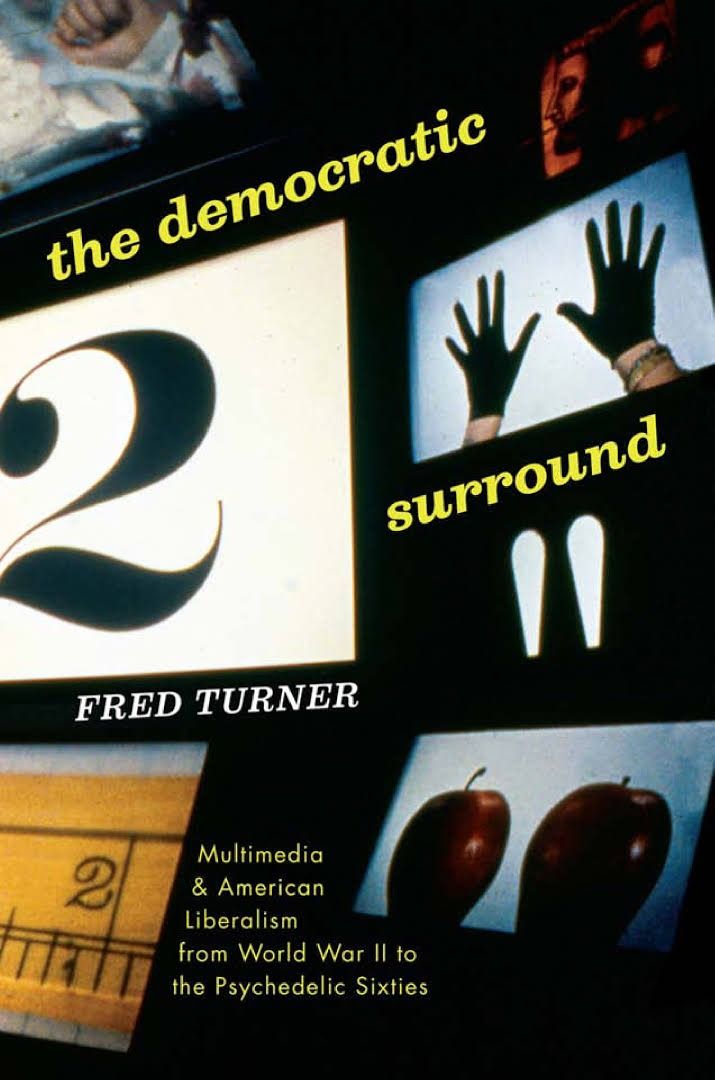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著作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正如他在2013年的著作《民主环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迷幻的六十年代的多媒体和美国自由主义》(The Democratic Surround: Multimedia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sychedelic Sixties)中所解释的那样,麦克卢汉在媒体方面的先驱性思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早期的反法西斯运动者和善意的冷战者。他们是第一批阐述媒体驱动的民主愿景的人,尽管从未得到完美实施,但这一愿景已经充斥了今天关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大部分流行思维。
这些先驱者对他们时代的主流观点做出了反应。20世纪30年代,随着另一场世界大战的临近,媒体成为广泛而强烈怀疑的对象,这种倾向集中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成员身上。那些试图理解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人抓住了一个从当时新颖的精神分析概念衍生出来的理论:纳粹主义的吸引力只能被解释为媒体操纵的结果。人们猜测,阿道夫·希特勒一定是通过广播和电影催眠了他的观众。广播系统的专业部署刺激和影响了手无寸铁的市民的无意识欲望;换言之,独裁政权的运行依赖于宣传。这一假设使那些希望团结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政府官员陷入尴尬的境地。如果大众媒体助长了专制的大众心理,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动员美国人,而又不会在不经意间把他们也变成法西斯主义者呢?
自由主义精英们寻求一种新的自下而上的传播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化解和改变极权主义潮流,让普通公民免受其害。他们的目标是设计出一套实践,培养出的不是可怕的“威权主义人格”,而是个人主义和民主人格。一群社会科学家和学者试图通过“国民士气委员会”(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来确立这些观点,该委员会由一位名叫阿瑟·乌法姆·波普(Arthur Upham Pope)的曼哈顿艺术策展人于1940年成立。如果纳粹的士气是顺从而脆弱的,那么美国版本的士气将是灵活而强大的,包含“完整的”自我,这一想法与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等精神分析学家最近的干预相吻合。如果纳粹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种族主义伪科学的基础上,那么美国的替代方案则会像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中所做的那样,强调培养而非先天。
虽然“国民士气委员会”已被遗忘,但特纳认为,该组织播下了新的传播范式和民主自我的新概念的种子。他们帮助创新了现在无处不在的沉浸式互动媒体环境——特纳书名中的“民主环境”。这种思维对美国在冷战期间在美国境内和全球范围内建立民主品格和促进交流的努力至关重要。但是,正如特纳在他对国际贸易展览会和世界博览会的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些博览会上,美国试图将自己与其共产主义对手区分开来,民主人格正在成为消费心理的代名词。民主等同于商业富足和选择。
到了60年代后期,这种受消费者影响的民主氛围,与反主流文化的平等主义和富于表现力的个人主义完全交织在一起,这种反主流文化并不像其信徒们认为的那样与过去发生戏剧性的决裂。1967年,当数万名嬉皮士涌入金门公园参加“部落集会”(Gathering of the Tribes)时,或者当摇滚乐队伴随着迷幻投影表演时,这些有抱负的反叛者实际上是在实现他们父辈的民主抱负,而不是推翻或颠覆他们。因此,今天我们这些沉迷于无所不包的数字媒体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的日常行为可以追溯到一条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将反主流文化的叛逆者引向美国冷战的宣传者。
“民主环境不仅是一种组织图像和声音的方式;这是一种组织社会的思维方式,”特纳写道。换句话说,多媒体环境和多渠道的传播方式最初被认为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我们瞥见了当前对官僚等级之上的水平网络(horizontal networks)的迷恋的起源。特纳写道:“如果法西斯社会是静态的,由上而下统治,那么民主社会将是不断变化的,通过理智(senses)的相互作用来管理。”但是,谁来管理呢?他们的权威从何而来? 他们对谁负责? 这种安排是否比之前的安排更民主?无论其发起者的初衷有多好,民主环境模式中蕴含的社会愿景提出了深刻的问题。
幸运的是,特纳写了另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2006年出版的《数字乌托邦 : 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是一本令人大开眼界的书,对所谓的“控制管理模式”(managerial mode of control)的兴起进行了必要的阐述。在书中,特纳探讨了一群紧密联系的反主流文化者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长起来,以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为代表的一个人物,采纳了“控制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为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推动的“新经济”的核心。总之,特纳的研究为当代关于媒体、技术、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思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启示。
1948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创造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舵手”(steersman)一词。正如特纳所写,控制论的吸引力在于它“把人和机器看作是一个单一的、高度流动的社会技术系统中的动态的、协作的元素”,在这个系统中,“控制不是来自指挥官的头脑,而是来自人、机器和周围事件的复杂的、概率性的相互作用。”虽然这个词有点过时了,但其概念仍然存在。它们已经扩散到生命科学、工程、数学、商业管理、艺术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等多种领域。(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杜达[John Duda]指出的那样,“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这个词——现在被认为是激进圈子里的核心原则——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控制论最流行的时候,才开始出现在无政府主义经典文本的翻译中。)
维纳的贡献很快被其他学者所掩盖,这些学者开始采用、改编和扩展他的方法,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他是控制论巨著《走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的作者,这对布兰德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寻求贝特森作为导师。控制论的框架使得将反主流文化和前沿(cutting edge)联系起来成为可能,这是前所未有的。控制论渗透到USCO迷幻艺术先驱的作品中,斯图尔特·布兰德于1963年加入USCO。USCO声称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完全做自己”和“融入人类世界”的机会。1968年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一场展览的宣传手册中,USCO被描述为“将神秘主义和技术的狂热结合起来,作为反思和交流的基础”。特纳认为布兰德和他的同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这种统一:由于他们的努力,计算机和技术不再被看作是政府官僚机构的呆板工具,而是成为个人表达和解放的工具。
布兰德是典型的湾区企业家,他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除了与USCO一起工作、与肯·凯西和他的“快乐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一起旅行、策划和推广1966年广受欢迎的“旅行音乐节”(Trips Festival)之外,布兰德还创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这是一本集工具、评论和反思于一体的大型汇编。该目录后来成为《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然后演变成“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简称WELL),这是一个在线会议留言板系统,被公认为今天的社交媒体的先驱。
在布兰德和他的同伴们的手中,控制论的修辞被用来促进网络和创业,使这种联系和活动像生物系统一样不可避免。按照这一逻辑,布兰德集结了他所有的社会资本,于1987年发起了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简称GBD)。与此同时,布兰德的长期同伴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明确的经济控制论观点。凯利认为,互联网成为了后福特主义市场的象征,它深深地遵循着自然原则,被一只无形的手所支配。正如特纳在《数字乌托邦 : 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中所描述的那样,《全球概览》的“以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变革态度、系统导向、对信息的专注,甚至是它所聚集的网络集群”,将通过布兰德和凯利后来的工作,成为“20世纪90年代关于网络计算和‘新经济’的争论的核心特征”。他们的理论为“寻求外包劳动力、工业进步自动化和降低工人就业稳定性的高管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布兰德和他的合伙人在2001年卖掉了GBN,但他还没有退休。长期以来对生态系统感兴趣,2009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地球的法则:21世纪地球宣言》的书,该书挑战了布兰德所认为的环保运动中日益严重的狭隘主义。布兰德坚信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但他在这本书里的目标是挑战左翼的陈词滥调。这本书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在对技术奇迹持怀疑态度的环保主义者身上。虽然所谓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ists)在捍卫“自然”时肯定会走向荒谬的极端,但布兰德更倾向于斥责那些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而不是对那些以牺牲人类集体利益为代价从化石燃料中获利的高管和股东发表不友善的言论。这种强调并不奇怪:在许多方面,GBN是炼油巨头皇家荷兰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一个规划团队的产物,最终将德士古(Texaco)和其他跨国公司列为客户。
布兰德的最新作品是2011年的《SALT Summaries, Condensed Ideas About Long-term Thinking》,它呼应了《地球的法则》的许多主题。从2003年开始,布兰德在Long Now基金会的赞助下,每月一次在加州旧金山召集专家和意见领袖们,正如网站所说,“帮助推动文明向新的方向前进”。SALT代表“关于长期思考的研讨会”:会议的目标是改变对当代社会问题思考的速度和规模。SALT Summaries由每一次SALT会议的简短摘要组成,音乐家布赖恩·伊诺(Brian Eno)在他的简介中称之为“精神的力量”(Power Bars for the mind)。但提供的花絮甚至比那些代餐品更不令人满意。尽管讨论了一系列有趣的话题——如何抵挡一颗小行星向地球飞来,寻找外星生命,城市规划和贫民窟,复活节岛的消亡,人类生命的延续,奇点,气候变化——但许多总结几乎站不住脚,有些只是演讲者的传记。
尽管如此,当通过《民主环境》和《数字乌托邦 : 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的视角来阅读时,SALT Summaries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事实上,该系列展现了一个成功的技术官僚阶层的有趣形象,他们自认为是后意识形态,但却希望通过社交网络传播自己的思想来改变世界。该项目的参与者自称是实用主义者或技术人员,而不是政治家或教条主义者。正如布兰德在《地球的法则》中引用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著名区分所言,他们是“狐狸”,他们汲取了各种经验和思想,而不是“刺猬”,用他们知道的一件事或思想去理解其他一切。
可以肯定的是,SALT演讲者都很聪明,但是他们更像刺猬,这是他们不愿承认的。SALT Summaries提出了一种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技术永远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的原因。问题不可能那么容易解决,或者说理想的解决方案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也不一定能达成共识,这种可能性被推到了一边。受邀演讲的名人——包括史蒂芬·平克、弗朗西斯·福山、克里斯·安德森、尼亚尔·费格森(Niall Ferguson)、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和克莱·舍基(Clay Shirky)——通常回避政治或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如果SALT是我们的向导,那么未来很少有女性(只有15%的演讲者是女性),而且几乎没有有色人种。特纳在他对布兰德“全球网络”的研究中强调了这种精英主义:如果它的人口统计数据能为未来社会提供任何指导,“它将是男性化的、有企业家精神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的。它将崇尚系统理论和技术促进社会变革的力量。它将摆脱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而转向个人和小团体赋权的修辞。”
换句话说,SALT Summaries是控制管理模式的写照;它提供了一个窗口,可以看到控制论思维的某个分支在起作用。技术官僚精英布兰德召开会议,想行使权力,但同时又否认自己的权威。他们认为自己走在了潮流的前面,采用的概念和工具会通过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渗透到其他人身上。
另一个世界可能吗?很明显,特纳写《民主环境》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醒我们已经被抛弃的好主意和没有选择的替代道路。正如他在书的引言中所写的,“已经消失的是那种深入人心的民主愿景,正是这种愿景促使人们首先转向媒介环境的转变,并在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60年代。”特纳希望通过他的研究来恢复这种“极端自由、多样化和平等主义”的愿景;他希望“经过新一代的努力,它可能会再次存在”。这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然而,为了让这样的理想复活,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缺失对我们的负面影响,而特纳从未清楚地阐述过这一点。
对特纳来说,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裂痕,当时政治导向的新左派和自由精神的反主流文化分道扬镳。在追溯“Be-Ins”和“Happenings”的根源到前几十年的民主环境时,特纳强调了前者的缺点,指出一些关键的民主潜力已经丧失。在特纳看来,这一时期乃至更广泛的反主流文化的多媒体实验,将个人心理提升为社会变革的正确领域,集体责任、有效组织和直接行动受到了影响。毫无疑问,特纳是对的,我们的政治野心已经变得紧缩和私有化,但是当你考虑到涉及的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时,将如此多的责任归咎于反主流文化,似乎既夸大又过于简单化。特纳哀叹道,反主流文化心态更多的是新自由主义崛起的症状,而不是其原因。
当然,反主流文化并不是乌托邦视野缩小的唯一领域。在1946年和1949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写了两封关于技术政治的令人痛苦的信。第一篇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标题是“一个科学家反叛者”(A Scientist Rebels),这是对波音飞机公司一名员工的回应,该员工要求一份绝版文章的复印件。尽管维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过军事研究,但他拒绝分享他的论文,对他的科学思想可能促成的“军事头脑的悲剧性傲慢”和“对手无寸铁的人的轰炸或毒害”表示遗憾。第二个是主动向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提出的有关自动化进步的警告,宣称他“无条件拒绝”为公司咨询的邀请。“我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向下游出售劳动力,”他写道。
维纳为科学在一个被权力失衡,尤其是经济失衡扭曲的世界中的作用而苦恼。他选择了一边。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必要让更多的人采取类似的立场。特纳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这么做——如果他们团结起来,通过建立协会和机构来宣传自己的信仰——他们可能会产生比一开始想象的更大的长期影响。但这也带来了一个警告:他们的努力可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他们既无法预料也无法理解的境地。“如果我们梦想的世界实现了,那么这个新世界的成员将与我们自己截然不同,他们将不再像我们现在渴望的那样珍视它,”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民主环境》开头的题词中说道。“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将不再感到自在。”我们这些生活在周围环境中,处于管理控制模式下,并希望改变这种模式的人,只能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狼狈不堪,被逐出我们称之为家的世界。
编译自:Phantom Public,作者是Astra Taylor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