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编辑。
波拉尼奥《佩恩先生》导读:大象如何消失在迷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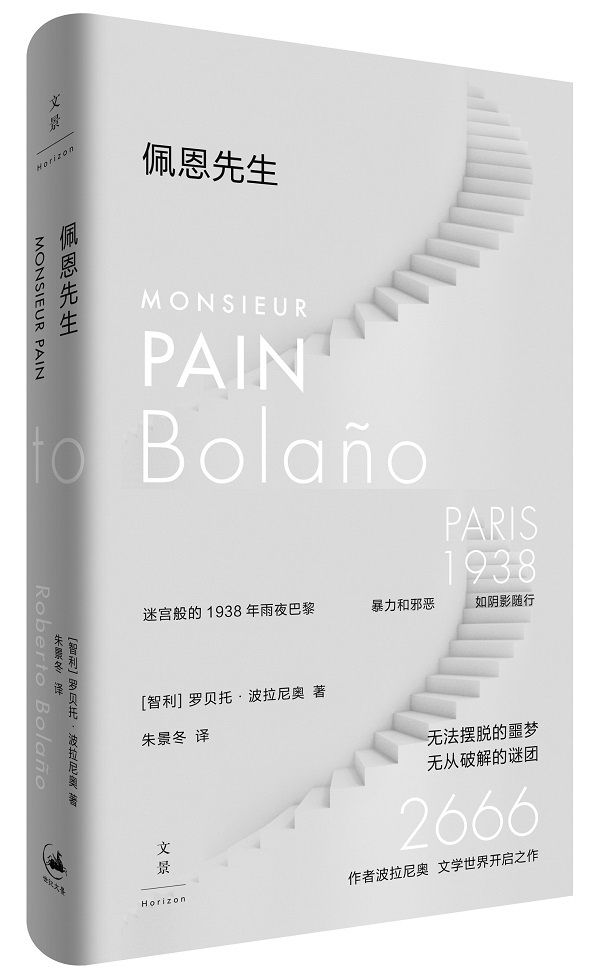
1977年,波拉尼奥离开墨西哥,移居欧洲,4年后定居波拉瓦海岸,“从此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
1992年,他被诊断出有肝癌,此后10年开始没日没夜写小说,“他天生是个诗人,可他只能开始写小说以供养家人”。
在这期间,他当过洗碗工、门卫、服务员和拾荒者,并且有过创作小说的尝试——如这本《佩恩先生》,写于1981年到1982年期间。在短篇小说《圣西尼》中,波拉尼奥就已透露过创作这篇小说的个人状态:
那时,我刚刚丢了巴塞罗那一处营地守夜人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养成了夜间不睡觉的毛病。差不多没朋友。惟一的活计就是写作和下午七点睡醒后开始的遛弯。下午七点是我身体产生类似时差反应的感觉,一种存在于不在、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莫名脆弱的感觉。我拿夏天积蓄的钱维持生活。虽说不大花钱,可一过秋天积蓄越来越少了。也许这就是驱动我参加阿尔科伊举办的全国文学征文比赛的原因吧。
尽管人们谈论波拉尼奥时,更多的是在谈论他生命最后10年(1992—2003)的作品,但如同预示到自己的死亡,他早在那之前就找到了路径——梦和现实,虚构和历史,文学和罪恶——直至抵达《荒野侦探》和《2666》的庞大世界。
借由人物之口,《佩恩先生》的隐秘主题在阴暗的电影院中浮现,这段对话发生在全书的三分之二处,如同电影剧本中的临界点:
“特泽夫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出现在一部糟糕的情节剧里是异乎寻常的。”
“你不能否认这是一部精彩的纪录片。”
“这要看对谁说了。”
情节剧还是纪录片?或者这样来问:幻觉还是现实?
对于熟悉波拉尼奥的读者们来说,这个问题早已不成问题,甚至在每本书都成为其乐无穷的解谜游戏:绑架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行动是否为真?(《荒野侦探》)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和恩里克·马丁有几分相似?(《恩克里·马丁》)散落于南美的纳粹文人又有多少出于虚构,多少具有原型?(《美洲纳粹文学》)
相比虚实不分的后期作品,波拉尼奥在开篇就布下了真实的锚点,或者说,每一个迷宫中唯一真实的事物——起点。

巴列霍的呃逆
巴列霍先生确有其人,全名为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秘鲁诗人,“很多西班牙语读者甚至认为他比聂鲁达还伟大”(黄灿然语)。他在秘鲁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囚112天,后移居欧洲;1928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员,与苏联交往甚密。1930年,他因参与左翼运动而被驱逐出法国,移居西班牙。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列霍坚定地站在人民阵线一边,反对弗朗哥政权,以此创作出名篇《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如果母亲/西班牙掉下来——我是说,这是假设——那么出去吧,世界的孩子们,去找她!”——死前未被印刷及出版。
1938年4月15日,一个雨天,巴列霍因病逝世于巴黎,病因仍未确认。在创作于1918年的诗作《黑石叠在白石上》中,他在开头便写到:“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一个我已经记得的日子。”
扎死居里的那辆马车/居里和催眠术
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巧的是佩恩先生也叫Pierre),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与夫人玛丽·居里共同发现镭。在科学研究外,皮埃尔热衷于神秘主义(当然,他相信这可以解释物体悬浮或异常运动的物理现象),阅读大量通灵术和催眠相关的书籍,参与了多次通灵实验。1905年到1906年期间,皮埃尔至少参与了8次IGP组织(The Institut Général Psychologique,研究催眠和心理学的科学组织)的会议,与会者包括玛丽·居里、亨利·伯格森和德·阿松瓦(“……居里遭遇离奇事故死亡后,德·阿松瓦尔就消失了。”P144)。
1906年4月19日,另一个雨天,皮埃尔在一次会议后死于马车的车轮下。就在9天前他最后一次参加了IGP组织的会议,为实验提供了一个制作复杂的羊毛袖子,将其套在人的脚上,以尝试是否能产生超自然的力量。
听闻皮埃尔的死讯,他的父亲说道:“这次,他在梦着什么呢?(What was he dreaming of this time?)”
大象之路
在本书的尾声,波拉尼奥煞有其事地写下每个人物的小传,出生地、逝世地和生卒年月的细节都似乎指向真实人物——他们的确在历史上出生和死去,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以不同的方式消失。
“大象之路”,在英文版中被译为两种说法:“The Elephant Path”(即P1提及的此书的原本书名)及“The Elephant Track”(即P163的章节副标题)。
“The Elephant Path”,根据某种说法为“捷径”之意。人类总爱寻找最短的路——例如,当两点之间隔着一片草地,而道路却离得太远时,人们会倾向于踏过草地,寻找最短的路。捷径不仅存在于空间,也可以发生在时间和认知中,我们很多时候了解历史也是通过不同的捷径,比如通往皮埃尔·居里的大象之路一般为:居里夫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丈夫。
和大象之路相对的,是不确定、不可靠的叙事,即佩恩先生所经历的迷宫:那对神秘的外国人、如蝰蛇般的勒迪克兄弟、介于剧情片和纪录片之间的电影、关于皮埃尔·居里被谋杀的阴谋论、使其无法接近巴列霍的医院走廊……这种虚实之间的对立,后来一再被使用,并演变成建立在现实之上的虚构,与现实交融的虚构,乃至“顷刻间从某种现实中游离出来”的虚构。
更有意思的是“The Elephant Track”这个说法,“Path”是即成的,但“Track”是更难以辨认的,可能被覆盖或掩盖。佩恩先生,一战老兵,残疾人年金被取消,“好像一个月或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吃一口面包似的”,开始寻找消失的大象。 *
用一个“kafkaesque”(尤其是在医院和护士的对话是典型的卡夫卡式对话)可以概括这个寻找的过程,不同的是,K面对的是可延伸出无限意义的城堡,而波拉尼奥为佩恩划下了具体的迷宫,他面对的敌人也是具体的:普勒默尔-博杜,法西斯及其阴谋活动,被时间所掩盖的神秘事件,以及佩恩自己对谜(从巴列霍到历史未解案件到神秘主义实验)的迷恋——“迷宫,对迷宫的喜爱,支配着我”。
于是,佩恩则被困于自己或他人布下的催眠术中,或者说“被困在时间中”(P90)。而大象彻底消失,梦境的忧伤无意义,唯有无迹(track)可寻的历史捷径(path),像雷诺夫人的回忆那般:
第一位丈夫的面孔,落雨,太阳,拉丁区的咖啡馆,皮埃尔·佩恩,一位她从没有读过其一行诗的诗人,过去的女性朋友们的柔情,任意故事里的小湖,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小的小湖,小湖越来越少,荒漠却越来越多。
* 这让我想起一个叫“大象消失术”(The Vanishing Elephant)的魔术:在1918年的伦敦,魔术师胡迪尼让一头重达5吨的大象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大象去哪了?巧合的是,胡迪尼本人亦不是单纯的魔术师,他疑似当过间谍,还揭穿过灵媒,甚至被怀疑因得罪灵媒界而被下毒致死。更诡异的是,波拉尼奥对胡迪尼本人推崇有加。在一次采访中,采访者问他觉得自己像哪个历史人物,波拉尼奥的回答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尼莫船长。于连·索雷尔,我们的父亲。梅诗金公爵,我们的叔父。爱丽丝,我们的教授。还有胡迪尼,他是爱丽丝、索雷尔和梅诗金的混合体。”
参考:
《巴列霍诗选》,塞萨尔·巴列霍,黄灿然 译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罗贝托·波拉尼奥,赵德明 译
《 Roberto Bolaño: The Last Interview & Other Conversations》
https://history.aip.org/history/exhibits/curie/trag1.htm
https://psi-encyclopedia.spr.ac.uk/articles/pierre-curie
http://www.rochester.edu/College/translation/threepercent/2010/01/21/monsieur-pain/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