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册
近日得闲看了部讲红军旅(RAF, 70年代活跃于德国的极左翼恐怖组织)的六集纪录片,看了一会就突然想起施隆多夫的《丧失了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初看该片是高一,警察粗暴恐吓女主角的场面启蒙了我对state power本质的认识(因为一下子唤醒了现实中老师,家长给我带来的一些不愉快记忆)。我一度对这类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停止空谈,选择行动的militia很向往,直到读了帕索里尼对68年学生运动的那番著名批判(闹事学生都是吃饱了没事干,精神空虚的布尔乔亚分子,警察才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学生喊着左翼口号挑衅警察属于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帕索里尼是我青年时代的绝对导师,他宁可粉丝清零也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实在太badass了,正是这番话埋下了我对白左苗头根深蒂固的拒斥,当然,那个时候还没“白左”这个词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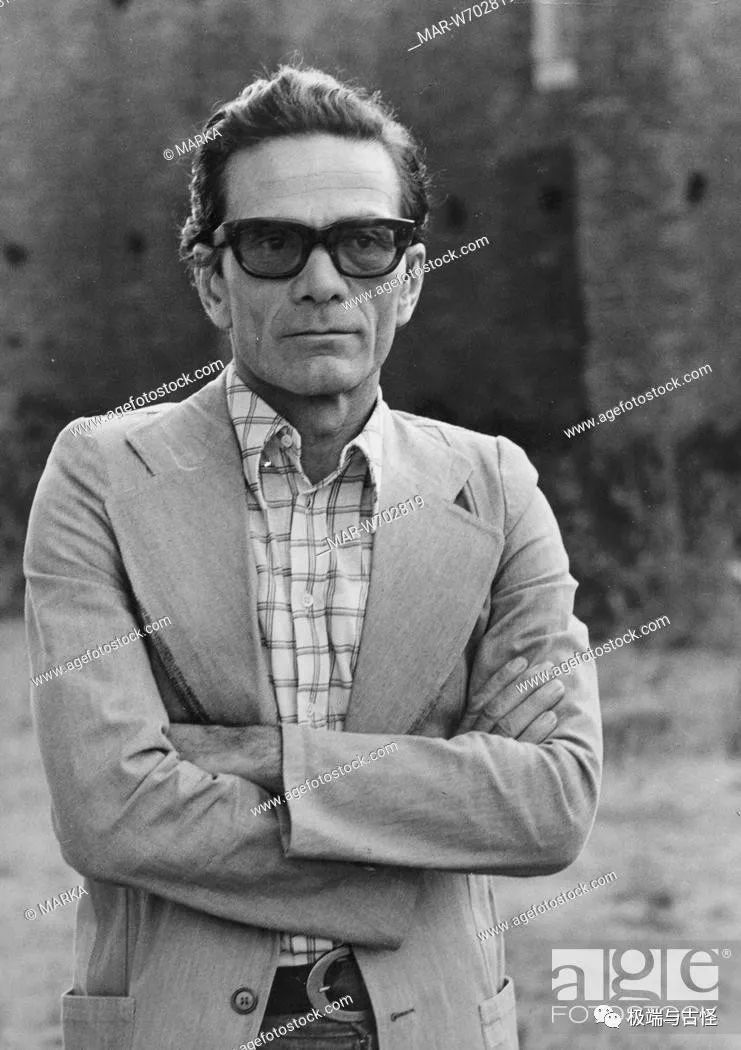
如今回看,我仍然坚持对RAF之流的批判态度,但这已经不再是出于对谁谁的迷弟情结或者对小资产阶级群体情感上的厌恶,因为此处牵涉到一个无解的哲学问题:有没有人/物可以代表另一个人/物?这个问题放到革命语境里面,那就是组织的利益就能代表每个成员的利益?而到了文学层面则是,一个语素就一定对应一个含义吗?本文不试图回答这个异常宏大复杂的问题。回到为什么要拒斥团体,这里的悖论是显而易见又难以回避的:渺小的个体要反抗多数人对个体的暴政,必须形成组织,二十世纪的教训是:任何组织一旦建制化了必然等级森严,这个组织再minority,对于个体来说也是个majority,也就是说,个体最终不管如何都是要被吞噬,以捍卫伸张个体权力而成立的组织首先剿灭的就是建立它的这些个体的权力。当然,对于鼓吹组织的理论家们,这个不叫剿灭,而叫权力的集中,权力最后只能集中在唯一一个个体,那个个体就变成了加缪嘲讽的:“只有他一个人是自由的,因为他要教会所有人自由。”
革命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暴力必定战胜理性,群体终将征服个体。我想,我和我的朋友们对于革命和任何群众运动本能式的厌恶和我们成长的原子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我看到反抗不需要中心化,建制化,甚至不需要行动,因为思想本身就是最内在,最永恒的反抗。上世纪末掀起的黑客无政府主义运动虽然伴随着维基解密神话的破产已经不是那么流行,但是这种匿名的,去中心的,游牧的,双向的,从不自称革命的赛博斗争仍然是我所知道的对反抗者而言最友好的反抗。同样,这样的抗争收效同样是微观的,碎片的,甚至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维基解密公开一份CIA档案不可能激发你我身边那些被压迫,荼毒最深的人的一丁点兴趣。但今天谁还必须相信启蒙?受到的压迫最重,难道就在道义上最应该统治他人?这个问题再想下去,就触碰到了左派文化最敏感的软肋:社会是如此不公正,以至于意识到社会不公正的往往是这种不公正的受益者,让他们去“指导”对不公正的抗争,这件事情不光在伦理还是在实操上都是彻头彻尾的笑话。要改变社会没有捷径,只有等到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作为个体的智识和能力都改变了才可能,鬼知道这要等多久!只有遍地freedom才可能垒出liberty, 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就走得远了。
写到这里我就想到了《马丁伊登》,这本书简直是为今天的我们写的,主人公问他的导师Russ Brissden:“你既然相信communism,为什么不入党?”后者给出了一个先知般的回答:“我相信communism,不是因为我喜欢它,而是因为我知道它必然到来”。你们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认为过去那个世纪留给我们的最大幽灵就是:以个体解放为名的集体主义,以升华思想为借口的盲动反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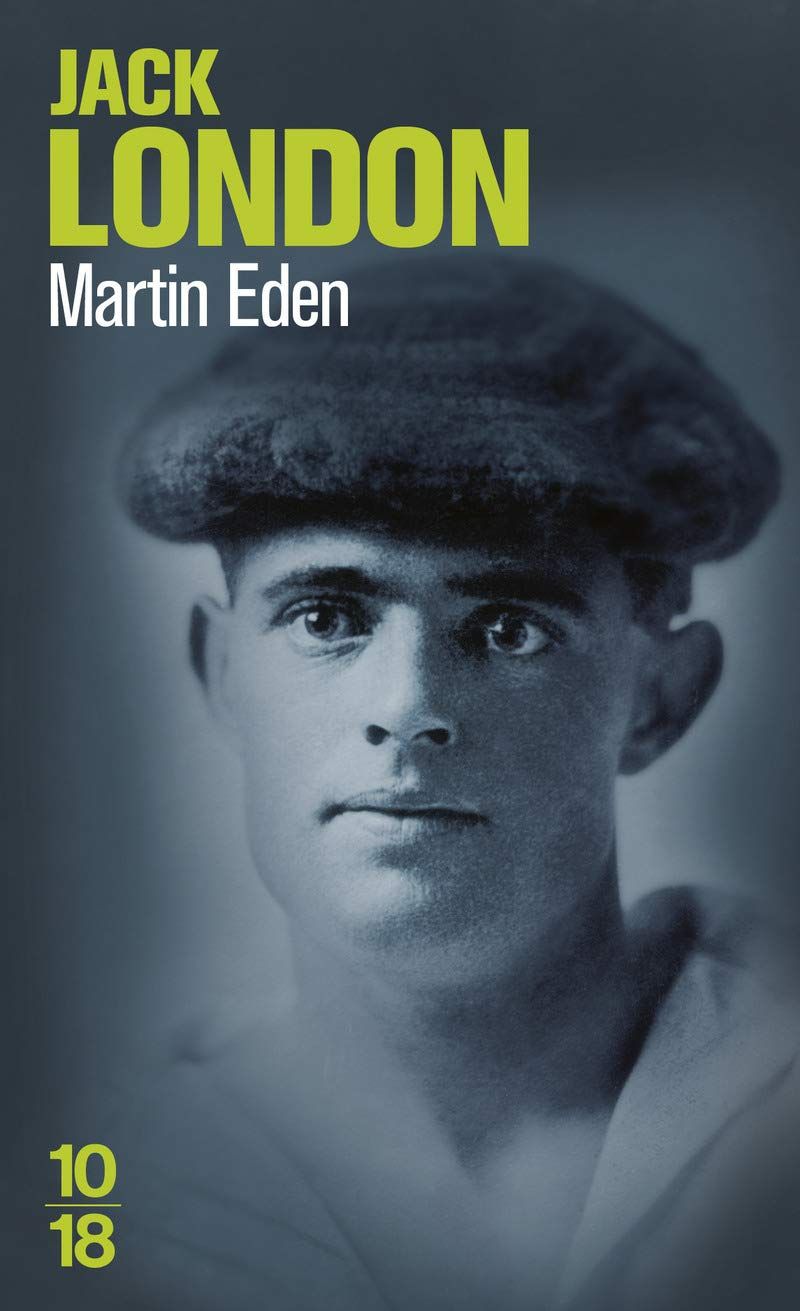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