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病毒會否殺死英國劇場?
1599年的倫敦,莎士比亞的環球劇場(Globe Theatre)落成於泰晤士河畔。在此前後的十多年間,英國一直受到黑死病纏擾。四百二十年後,因為新冠肺炎疫症蔓延全球,莎士比亞環球劇場(Shakespeare's Globe)面臨結業危機,自2020年3月起關閉,造成重大財務負擔。這個劇院是在1997年開業的,參照當年莎翁本身劇院原樣重建。第一代環球劇場在1613年在火災中被燒毁;翌年重建,直至1642年被禁——這次是出於政治原因:英國內戰開始,清教徒控制的國會下令肅清劇場,倫敦劇院無一倖免。幾代環球劇場的命運,象徵了劇場藝術在歷史上一直面對的存亡危機。我從香港來到倫敦,在倫敦回望香港,感受到雙重的危機感;這篇文章是在這種跨界視域之下的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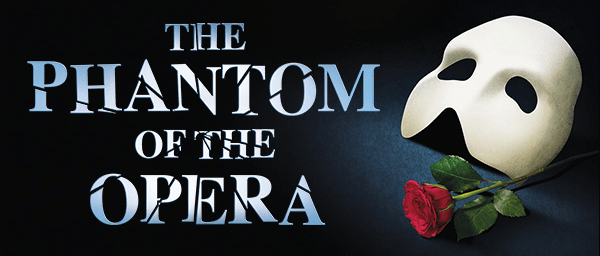
甚麼是劇場?
今年春天,為了防止群眾聚集傳播病毒,各地劇場等表演場所須關閉,公開演出暫停。瘟疫歷來是劇場的天敵,因為劇場是人們聚集交流之處,防疫卻須分隔人群。廿一世紀的資訊科技似乎可以突破這種限制,各地劇場工作者立即變陣,推出各種節目以饗觀眾。例如莎士比亞環球劇場及英國國家劇院都把現場演出的視像版本放上YouTube,全球免費收看。同樣轉移到網上播放演出的藝團及節目規模有大有小、種類繁多,從戲劇節到小劇場,從舞蹈到管弦樂,相信各位讀者這幾個月來都看過不少。因為網絡無國界,除非受到版權或部分國家的審查限制,觀眾看到各國演出的機會及數量不減反增,不單是節目看不完,就是連很多整理這些網上演出資源的文章資訊量也令人有點吃不消。例如這兩個:
一)Where To Get Your Theater Fix Online, Old Favorites and New Experiments
二)Hottest Front-room Seats: The Best Theatre And Dance to Watch Online
然而這些網上轉播的節目質素參差,主因卻跟演出本身的質素無關,而在於影音設備及錄製人手的專業性和資源上的差異。像英國國家劇院所播放的NT Live節目,自2009年開始,本來就是為了在電影院播放的高清製作,常常邀請電影明星主演經典劇目,加上預先設計好的取鏡及剪接,固然最受注目。相較起來,很多小型藝團放上網的作品,同樣是舊作預錄,但多是本來用以紀錄而非觀賞用途。因為資源所限及原意有別,影響了可觀性,例如現場收音不夠清晰、攝影機的位置無法顯示導演的調度、觀眾亦更難看清楚演員的演技。
已有不少人提出過,像NT Live這類製作精良的節目真的算是劇場演出嗎?上述提及的優點,其實都是電影的特點,例如現場觀眾無法看到的鏡頭角度、演員的特寫鏡頭等等——最重要的是剪接,是電影及劇場兩種媒介的主要區分。所以在社區隔離期間,觀眾在屏幕上看到的演出,不論製作水平或規模,本質上都是影視作品,屬於「劇場電影」或「劇像錄像紀錄」,而不是劇場。若以劇場視之,上述的「優點」甚至可反過來說是「缺點」:例如觀眾在劇場看演出,可以自己決定把注意力放在舞台任何一個角落或演員身上,即使那是在背景中的配角,只要在台上便是在演出;但像NT Live這種製作方式,每一個鏡頭都是導演代替觀眾作出了注意力的選擇,把其認為不重要的隔於鏡框之外。而節目一旦涉及剪接,則在演出之上增加了一層節奏感,對於舞蹈來說,甚至可說是一種干擾。例如我在網上看艾甘.漢(Akram Khan)的《異地人》(XENOS),在舞者本身的節奏以外,還增添了鏡頭剪接的節奏,因此我再分不清,觀賞時所感受到的,還有多少是艾甘.漢創作的效果,而有多少屬於錄影轉播一方的「貢獻」。換言之,劇評人亦難以透過影視再現形式的演出作出「劇評」,只能當作影評。
影音媒體和劇場真是涇渭分明嗎?網絡視像版本的演出,只能被視為一個暫時的替代品,抑或可以是幫助劇場發展的助力?因疫情而大規模轉移到網絡活動的劇界能否藉此機會探索新的劇場美學,以及與觀眾交流的方式?除了舊作轉播,這三個多月來,藝術家們並無停止創作,反而利用各種媒體技術突破在家隔離的限制。有的利用網上會議軟件的界面來作即時演出;有的編劇撰寫微型劇本,讓演員在家演出,在Instagram上播放。各種社交媒體讓藝術家和觀眾作出即時透過留言或視像交流,保留了劇場的互動性。即時交流是劇場藝術的特性,所以有創作者在這時期探索遊戲化的作品,讓觀眾在網上參與演出。例如取材自封城時期人們在家工作的《WORK_FROM_HOME》,便讓觀眾以網絡會議軟件參與,成為其中的角色,探索「數碼劇場」的可能性。也可以說,當人們被迫隔離在家的時候,反而透過網絡演出而開拓了更多接觸面,突破劇院在地理上的具體限制,觀眾有更多機會看到世界各地不同作品,藝術家也能向外地觀眾推廣了自己的作品。例如我很慶幸身在英倫,也能看到香港的《5月35日(庚子版)》之網上直播。在隔離時期,劇場藝術家可利用資訊科技,突破地理隔閡,把人們凝聚為一個新的虛擬社群。

電子遊戲化的趨勢亦可見於藝團Punchdrunk及科技公司Niantic之合作;前者專營沉浸式劇場,後者則曾推出大受歡迎的擴增實境遊戲《Pokémon Go》,在6月宣佈「組隊」研發創新的互動戲劇形式,但細節仍未出爐,沒人知道這新計劃如何兼顧安全的社交距離之餘,亦帶來沉浸於現場環境中的戲劇體驗。其實表演藝術界一直緊貼著創新媒體科技,例如英國國家芭蕾舞團曾配合VR技術製作360°全景版《吉賽爾》;皇家莎士比亞劇團亦運用過動態捕捉及全息投影技術去演繹《暴風雨》的精靈Ariel;香港的「風車草劇團」在《新聞小花的告白》中也試過利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把一段劇情傳到觀眾的智能電話中,共同感受戲中人收到「突發猛料」時的震憾。
換言之,若我們區分劇場和電影(或其他電子影音媒介)之時,強調前者是現場、即時和實在的藝術,而後者則是經過資訊科技干預的虛擬影像,或會忽略了現在的劇場早已是經過媒介(mediated)的藝術形式。曾在5月於網上公開的演出《The Encounter》是錄影預製的版本,但創作兼主演者Simon McBurney特別為這網絡版本製作了一段充滿自反性幽默的片頭:我們一開始時看到的是在劇院後方的廣角鏡頭,舞台和觀眾席皆在畫面之中,看觀眾入場就坐。突然一位劇場觀眾轉過身來向我們(網上節目的觀眾)說話,正是McBurney本人,然後這個「觀眾入場就坐」的畫面裂開——原來之前看到的場面是藝術家利用藍幕合成技術構成的,而他在家中隔離自拍,再正式向我們介紹這個節目。McBurney藉此提醒我們,眼看未為真,耳聽未為實,這正是《The Encounter》的要旨之一。這個作品本身是有關「現實經過媒介」的問題,現場觀眾須佩戴耳機收聽劇中以Binaural Audio聲音技術來錄製的「入腦式」音效,而在網絡收看的觀眾亦一樣。McBurney的聲音設計令觀眾難以分辨哪些聲音來自現場演出,哪些是預錄內容,聽他訴說一個虛實難分的故事。
說了這麼多,我仍有未解決的問題:這些真是劇場嗎?劇場是甚麼?當劇場演出變成影視作品、互動遊戲和網上會議時,更多是變成了另一種已經存在的媒介,多於創新的劇場形式。世界上早已有電影、電視、網上串流平台、網絡遊戲和手機遊戲等等,而當劇場界倚靠既有的科技來轉換形式,只是成為了這些媒介的一部分,但在製作水平及規模上難以跟既有的媒體工業競爭。劇場與電子影音媒介的核心分別在於這個「場」字,在於觀眾及演出者的身體與劇場空間的實在性;我認為:容納觀眾及演出者同在現場的即時演出才是劇場表演。
這樣問題便大了。
劇場之死?
因防疫而關閉演出場地,再加上有關社交距離的措施,的確對劇場構成重大威脅。英國劇場界正面臨沒頂之災,因為停演便沒有收入,即使有政府的臨時救助,很多劇院預計在9月至12月期間便會「乾塘」。即使像英國國家劇院這樣受歡迎、籌款能力又高,也宣佈了須在9月裁減約三成的前台及後台員工。創意產業工會(Broadcasting, Entertainment, Communications and Theatre Union, BECTU)預計疫情之下,劇場界會有三千名常設職務被裁減;重點是,這只佔劇場職工比例約三成,而大部分戲劇工作者都是自由身,手停口停。有的劇場演員轉向影視界尋求工作機會,更多人則可能要轉行。雖然政府有推出為自由身工作者而設的特殊津貼,但仍有不少人因為不符合稅務標準而無法受惠。我向香港劇界的朋友打聽,首當其衝的亦是小型藝團,因所受資助不多,平常多與自由身的劇場工作者合作,在劇場暫封期間都失去收入,為生計須暫時轉行(例如當清潔工);而得到大筆資助的大型劇團及其受薪員工,所受影響則較小。
英國劇場產業的存亡危機有結構性的原因,在新冠肺炎爆發前早已存在。最近十年,保守黨政府大幅削減各類公共開支,藝術和文化項目得到的資助大減,劇院須更加商業化,在收入比例上更倚賴票房及場地餐飲等維持收支平衡。根據一篇2019年的報導,從2010年開始,文化領域(包括圖書館和博物館)從地區政府收到的預算減少了四億英鎊,來自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的預算則削減了三成。就算是受到公帑支持的劇院,同樣受到業績壓力,須滿足資助者的要求。所以當封城令一下來,劇院關門便難以自負盈虧,從本身最「旺」的倫敦西區,到各城服務本地社區的劇院,皆面臨結業危機。即使疫情將會高度受控,劇場界遭受的影響亦不是暫時的,而是不可逆轉的大規模衰退。劇界向政府呼籲「包底」(bailout)救亡,不單為了很多人的生計,亦是文化保育;按名演員茱迪丹茱(Judi Dench)的說法,英國劇場不只是產業,而是藝術遺產。
英國歷史上,劇場曾多次遭受類似的存亡危機。十七世紀內戰時期的劇場禁制令持續了約十八年,到1660年君主復辟後,戲劇界才復甦。而十六、十七世紀之交,英國也因鼠疫而多次關閉劇院,而這也是莎士比亞最活躍的二十年,四大喜劇和四大悲劇都在此期間寫成。業務之危能否轉化為創作之機?評論人William Cook提出,疫症可促使劇場界探索新的演出空間及形式;如果閉密空間會傳播病毒,便搬到戶外的公共空間演出;若疫情引來經濟衰退,便有機會以更廉價的租金使用舞台,或利用廢棄空間來演出。
Cook的提議呼應了有關自由與劇場的悖論:英國劇場本身已面對多年的結構性危機,源自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路線,自戴卓爾夫人時代起便一直被削減公帑資助。雖然有創作自由,卻在財政壓力之下,缺乏資源去嘗試更多的營運及創作模式。香港的藝團雖然有公帑資助,但集中分配在少數大型藝團之中,中小型藝團也是吃力地維持;今年因應疫情而推出的防疫基金,亦有藝團之間「貧富懸殊」的狀況。另一大憂慮是「國安法」生效,正如港澳辦所言,是頭上懸劍;戲劇工作者在這把利劍之下,自由創作的空間會被削去多少?Cook對使用廢棄空間的建議,正回應著如何擺脫政治及商業兩大壓力的問題,尋求一種更質樸的、貼近民間的創作自由,是anarchist式想像。誠然,這種非商業模式是無法解決刻下戲劇產業及從業員面臨的生計危機,只能當是衰落之後春風吹又生的想望。更悲觀地說,當新自由主義的巨輪繼續開動,那些廢棄空間早晚會在仕紳化或再發展的過程中被壓碎;另一方面,若政權要扼殺民間的自主聲音,把人們自發性的聚集交流視為威脅,這些創意空間同樣會被履帶輾平。
電影《V煞》(V for Vendetta)有一句對白說:「意念是防彈的。」劇場的最核心不是產業,而是創意。所以藝術家們在封城期間百寶盡出的作品,不論算不算真的劇場,都對劇場藝術帶來重大貢獻。創作的信念不會被困在高牆之內,也不會被子彈或病毒殺死。劇場用不懼怕各種形式的「瘟疫」,因為劇場就是瘟疫:
“The action of theater, like that of plague, is beneficial, for, impelling men to see themselves as they are, it causes the mask to fall, reveals the lie, the slackness, baseness, and hypocrisy of our world.”
“The theater, like the plague, is in the image of this carnage and this essential separation. It releases conflicts, disengages powers, liberates possibilities, and if these possibilities and these powers are dark, it is the fault not of the plague nor of the theater, but of life.”
——“The Theater and the Plague”, Antonin Artaud (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
(原載於2020年7月,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網頁專欄「藝評筆陣」,連結:http://www.iatc.com.hk/doc/106380)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