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在跟自在都在臺灣土生土長,喜歡說廢話、筆戰、看閒書。 不喜歡的話一定要直接留言批評,留下具有建設性而且跟文章有關的留言。這是我唯一的願望你們這些觀眾最好是要做到,因為自由社區內有自由社區獨有的理性,請不要讓自己的中心思想失望了。
【解構練習】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ep.2
第二節|縈繞不去的重擔
媚俗是一座屏風,遮掩著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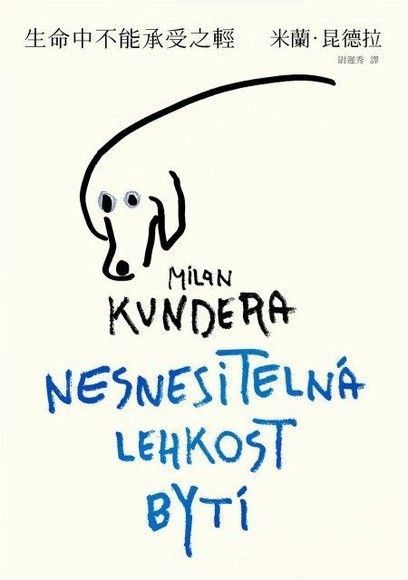
我們很榮幸的有弗蘭茨成為我們的冒險者,他展現的特質最後讓我們看見(不那麼好的)結果 — 劫難的輪迴,或者說,無法逃避的重擔。
弗蘭茨的人格特質使他導向悲劇的重大缺陷:他崇尚偉大的進軍且(我會稱之為)懦弱。偉大的進軍基本上可以與媚俗站在同一邊(但並非同義詞)。然而,我們並不需要因此把弗蘭茨與媚俗畫上等號,弗蘭茨並不是一個媚俗的人,因為偉大的進軍對他來說只是同理想般的存在(就如同薩賓娜對於美好家庭有所懷念,但她不可能放棄背叛之旅),就如第一集結尾所提: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超人,也沒有人可以完全逃脫媚俗。不論我們如何輕蔑媚俗,媚俗終究是人類境況的一部分(頁295)。
我們無從退路無處可去,因而我們要時時提醒自己,視媚俗為謊言。弗蘭茨的生命歷程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這些理想式的詞彙,這種理想的行為我們可以將他進一步解釋成使它存在不致失重的維繫之物,進而我認為維繫之物在小說或者人物的生命歷程中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關於如何向重告別並前往輕的生命議題上,顯然必須有一個調和來使這個過程不致失速,我們亦可說這是維持小說節奏的良方。在文本中,一方面,我們探討的是如何離開重到輕;另一方面我們也因為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輕,必須找到著力點,在離開和保留之間達到平衡。這是最重要的一塊,我想也是普羅大眾能夠去思考的課題。
生活在真實裡。
這句出自卡夫卡的語句吸引著弗蘭茨,他企圖這麼做,因為他渴望背離,他原有的重使他喘不過氣來,使他必須不斷活在謊言中,活在胡言亂語中,這當然是正在增加負擔。這使他想要騎著薩賓娜背叛他的妻子,或者說背叛那個妻子體內的女人,這個隱藏女人代表著代表著他的母親,弗蘭茨對母親的崇拜自母親死之後愈發堅決,弗蘭茨信以為真她就是他偉大進軍的其中之一。(這點和特麗莎的情形正好相反)
然而與薩賓娜背叛的堅決不同,弗蘭茨更為有所顧忌。這是他不敢生活於背叛所帶來的輕裡頭。一切都使他害怕,而這個害怕使他被命運遣返了他所逃離之處。弗蘭茨自己也明白,他畢生所追尋的偉大進軍不過是一種媚俗的行徑,他必須開始進行背叛,渴望背叛所帶來的輕如同薩賓娜交給他的那樣,但他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嗎?
可惜的是,他的懦弱或者說她的猶疑不定致使他最後依然無法,自從與妻子分居,和女學生同住之後,這看似所謂的背叛的確讓他感受到暫時的輕盈,他不再被那個妻子體內的女人給束縛住,他擁有了自己,特麗莎甩掉母親找回自己,而弗蘭茨甩掉妻子找回自己。
我想我必須另外言明,女學生是在特麗莎離開之後才出現在弗蘭茨的生命旅程中,戴著一個圓框眼鏡出現。弗蘭茨把她看做薩賓娜派來替代薩賓娜的,是薩賓娜送給他的一份禮物,這個替代弗蘭茨極為重要,弗蘭茨將這些替代都看做偉大的進軍的一部分。但終究他還是無法逃離重的境地,因為他的維繫之物不斷的變動,每進行一次背叛就想要找出新的維繫之物,這個習慣讓他依舊無法安心於旅程中,他是渴望被隱形的眼神看見的人,這又是另一個肇因,這強烈的昭示呼喚他回到重的一端,然後他聽從了,一切進入到第六部《偉大的進軍》。
我們的朋友,弗蘭茨,這個不斷尋照維繫之物的冒險者,最後秉持著他需要為了他所謂隱形的眼神(可以說是薩賓娜)而這麼做(他認為那眼神會希望他這麼做),出現在柬埔寨。
這起在亞洲的政治事件是米蘭.昆德拉在《巴黎評論》中提出之複調概念中的一部分,第六部分不斷重複討論「媚俗是什麼?」。而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言:
這個複調的段落是支撐整個小說的支柱,是解開小說之秘密的關鍵。
第六部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作為辯證本書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 — 「媚俗是什麼?」,在帶有嘲諷意味的文體中,我們會知道這種媚俗是多麼可笑,對存在的全盤認同,沒錯,正因為這種無用的行為,弗蘭茨認為薩賓娜希望他去柬埔寨、他認為薩賓娜正看著他,將目光投射在他身上,他以為是他自己做了選擇,他反擊在柬埔寨試圖搶劫他的人,偉大進軍的光芒正照拂著他!
偉大進軍的榮光變成只是一些遊行者可笑的虛榮,他再也無法接受...
弗蘭茨冒險的一生,最後終結在無可承受的重擔中,就連帶著圓框眼鏡的女學生也一起承受了,最後的贏家是弗蘭茨法律上的妻子瑪麗 — 克洛德。 迷途漫漫,終將回歸。這是弗蘭茨的墓誌銘,一切是命運作祟嗎?
我想說的精確一點,媚俗使他因重擔而死亡,死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中。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