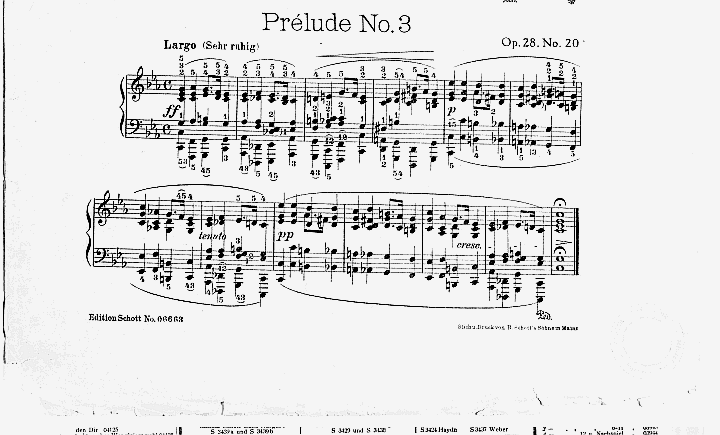
意识到也许永远不能被发表,但又不愿意只做一个抽屉里的作者……
故事五:毁灭城市的城市
第一类的伪公理是:无论什么,都在某处和某时
——伊曼纽尔·康德
《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1770)
如果我们认为事件是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固定某处;如果现实是由时间和空间上完全独立存在的物质构成,那事件只不过是这些冰冷核心产生的各种关系变化。就像幻想这些荒漠中的岩石和矿物居然有一天风云突变,结合成壮丽的宫殿和伟大的城市,我们更关注的居然是被改变联系的物体,而不是创造这一运动的自由魔法本身,这是一种可悲的错误。
某一位万王之王伫立在荒野中时如此想到,如果当时他愿意表达,他会赞同将现实视为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事件,即事件和过程才是本质,所谓不变的物质只是从事件中抽象出来的。不过此刻这位伟大帝王的思绪被更重大的事情所占据:如何修建自己的陵墓。
按照波斯帝国的传统,帝王会用一生的时间准备自己的陵墓。他知道伟大的征服者在埃克巴坦那、苏萨和波斯波利斯都兴建了古典艺术的范本。他知道那个从印度到希腊的光荣时代已经逝去,万国门的猛兽护卫着希腊的女性雕像;亚美尼亚崖葬的设计用在居鲁士的陵寝中;大流士宫殿使用埃及神庙风格的大门;挥金如土的阿帕达纳宫似乎被各种神话动物浮雕淹没。怀着疲惫的尊敬,万王之王修缮了大流士在苏萨古老的宫殿——两河的湿热让那位改革者匆匆离开舞台;然后是阿达帕纳的圆柱和莲花——在阿尔塔薛西斯一世之后再也没有君主能有闲暇享受帝都的隐居生活。
历史的逻辑自有其不可侵犯的凛然,只需要几代人的重复,就可以产生永生永世的倦怠和无力。集天下之精华建起的宫殿往往无人居住,清凉和慌乱的营地才是君王消磨半生的处所。征服埃及的冈比西斯再也没能回到故乡的王座;大流士在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的野心到继任者薛西斯才完成;后者没能看到百柱大厅和万国门的落成,就被暗杀在奢侈的卧室之中。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击杀了哥哥和弟弟,他的长子在酒醉中被暗杀,继任者大流士二世大多数时光用在平定叛乱中,无力阻止儿子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和小居鲁士的漫长冲突。随后是厌倦等待的儿子攻击父亲、兄弟阋墙,欺骗、毒药和对王族的屠杀。历史——我们渴望遗忘的噩梦,如果继续将自己的宫殿建在平原上、墓葬挨着先祖的悬崖,就等于向这种恐惧投降:没有一代代君主,只有父与子、成功者和失败者、死者和继任者,只有周而复始的同一个血腥故事,除此之外的人和物都是抽象的形象。波斯人对这种逻辑非常亲切,著名的长生军有一万携情人和豪华武器的重装战士,每个人退出战斗后都要立刻更替,所以他们是不死的。
——就如同这平原上璀璨夺目的星辰都是虚幻,只有苍凉的宫殿和圆柱矗立。在那些超脱时空的事件面前,物质只不过是一个演员。他熟悉若干人类的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承继的,旧王已死,新王万岁,关于意外、阴谋、衰落与崛起。击中皮洛士的那个石块、毒酒、女子和宦官的暗杀在其中扮演同一个角色;腓力的远征、阿吞神、马尔都克在哈兰的神庙,都是作为注脚的小小牺牲,甚至可能包括他本人在内。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漫游的,征服、流浪者自愿或被迫忘记故乡,在陌生和疏离的世界中重建自己的羁绊。尤利西斯、冈比西斯、更古老的狄多女王和印南娜女神先后成为这个漫游者的象征,而未来的亚历山大里亚、色雷斯的那座渴望之城、圣墓教堂和乌尔菲拉斯的抄本,都是这种关系中胜利的纪念碑。他不需要预知那个马其顿的少年将成为击败所有守护者的守护者;甚至他自己也会成为阿契美尼德帝国一系列暗杀的下一个死者,单是这种虚幻感就足够悲怆了。——于是那些时空永远地离他而去:德谟克利特的无限宇宙;普罗提诺的上帝溅射出的中心世界;伊西斯和阿纳希塔孕育的时光之水;平直的无限空间和耶和华创世的时间;发生在我们身体中的暴涨宇宙和反德西特空间……
万王之王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长久沉迷于古都荒废的宫殿,但又不想让自己加入拥挤的平原,便下令将自己的宫殿建在能够俯瞰整个建筑群的后山上。《微暗的火》中那个活在未来逻辑中的君主或许会喜欢这种谜题,但正如本文的作者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却毫不掩饰他对于纳博科夫才华的钦佩以及作品的厌恶一样,万王之王奥科斯决定用阿契美尼德帝国最低调的名字掩盖他的身份,他自称为阿尔塔薛西斯三世。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