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爱好者
第一章 词语 独裁者如何劫持我们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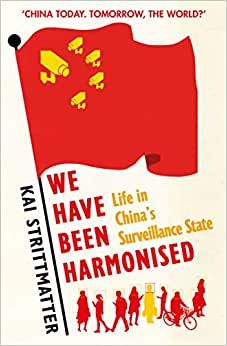
《开明的中国式民主让西方蒙羞》 新华网2017年10月17日文章
我住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我住在中国。是的,我所在城市的街道两旁成排的宣传栏和宣传板上就是这么写的:自由!民主!法治!在北京的每一个街角,我每天都能看到它们。这是党已经宣传了数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美国总统每天都要冲着群众高喊十几次“要相信我!”每次川普在作出黑白颠倒的陈述时,都会加上这句“要相信我!”在他总统任期的第一年,滑稽可笑仍被看成滑稽可笑,困惑的仍旧困惑,麻木感尚未生效。不幸的是,从那时起,人们对于这些极致的谎言和欺骗造就的陈旧记忆已逐渐模糊。我们忘记了,在人类历史上,川普和他的谎言并没什么出众。这些谎言对于各地的独裁者和准独裁者而言,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是他们的通用货币,远非一个政治小丑的特殊病理特征。任何一个曾生活在新兴专制国家的人--比如在土耳其、俄罗斯或中国--都对川普这一套故意的、系统化的和无耻的扭曲事实的行为似曾相识。它来自于独裁者的教科书,书中第一条也是最要紧的一条权力工具就是谎言。虚假新闻?被选择的事实?对于地球上的亿万民众,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经验。过去二十年我都在中国和土耳其:在这两个国家,左可以被说成右,上可以变成下。我只是一个外人,一个观察者,一直享有拉开距离并对每次新的暴行表示惊讶的特权。如果你生在这个国家,并还想不受干扰的过你自己的日子,那这样的特权你可消受不起。
中国人对于统治者重新诠释这个世界见得太多了。在二千多年以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首次统一了帝国。从公元前209到207年,他儿子继续当皇帝,身边有一个令人恐惧的权臣叫赵高。一天,当着皇帝的面,权臣带着一头鹿到朝上。“陛下”,他指着这个动物说到:“这是献给您的一匹马!”
皇帝和其他官员们一样,都吓了一跳,请权臣解释,这只鹿怎么可能是马。“如果陛下不相信我说的,”赵高答到,指着他周围的官员们:“那么请询问你的臣子吧。”一部分乖巧或胆小的官员都来证明:“这的确是一匹马,陛下。”当然,也有许多固执的官员坚持认为站在那里的动物是一头鹿。不久之后,这些官员都被逮捕和处决。但赵高并没有止步于此:那些因为吃惊或害怕而沉默不语的官员也都遭到毒手。打那以后,鹿就成了马。所有人都学乖了。指鹿为马这个成语一直在中国流传至今。
西方社会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舒舒服服地成长在一种确定性的环境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于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极权体制的经历也都快忘光了。所以,一个带着不择手段的天性和极度渴望权力的自我激励的独裁者,面对着今天这些天真的未经世事的民主人士,永远是领先一筹。在美国,川普宣誓就职后不久就证明了这个论断。因为大家开始争论,如果一个谎言出自总统之口,你还能称其为谎言么?就好像权力被赋予了重新命名世界的权利。最终,纽约时报是头一家指出他在撒谎的报纸。很多人在查了字典之后,也为这些媒体鼓掌。他们确信,如果"有意隐瞒“是一个事实,那么,报纸的确可以这么说,那句话的确是谎言。
对于独裁主义的个人和体系来说,最首要的意图并非欺瞒,而是恫吓。所以独裁者的谎言通常更加无耻和乖张。在川普的就职典礼上,全世界都亲眼看到来华盛顿观礼的人群是多么稀疏。当时的视频在互联网上触手可及。但总统先生一点不在乎,他照样夸口”史上最拥挤的一次典礼“,几十万、上百万人参加了欢庆。在这一点上,华盛顿与安卡拉别无二致。在一个成型的专制国家,他们会用公交车运送几十万群众来欢呼雀跃;但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情形,独裁者们最终并不在乎人们是否相信他们的话。他并没有打算说服每一个人--但他的确打算驯服每一个人。权力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不管它拥有了多大权力,它始终都无法完全确认这些权力。这种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慌的偏执,是权力执掌者天性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何他觉得有必要一遍又一遍地去征服大众。而谎言,比其它任何手段都更能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的执政党到今天仍然坚称这个国家是共产主义国家,并再次强迫老师、教授、公务员和商人公开宣誓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并非因为它真的相信这样人们就会信仰马克思。在瑞士神话故事威廉姆·特尔中,帝国官员赫曼·盖斯勒要求所有的农民都向放在一根柱子上的一个帽子敬礼。马克思主义就是盖斯勒帽子的中国版本:最要紧的是这服从的姿态。这就是独裁者怎样布置他的谎言的--你如果拒绝接受这个谎言,你就被甄别为敌人和靶子。
但恫吓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局。同样重要的还有传播混乱、瓦解理性、摧毁作为人们日常参考系统的现实感、拿走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指南针。如果你是个骗子或说慌者,你无法战胜有着上述武器保卫的世界,一个能分辨真相和谎言的世界。所以你得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骗子和说慌者。这样一来,你最坏也不过就是其中一个骗子。
汉娜·阿伦特,曾经深入研究集权主义政府,在1974年的一次访谈中曾说:“如果每个人都始终对你撒谎,结果并不是你会相信这些谎言,而是没有人再去相信任何事情。"(注6)一个民族如果再也不去相信任何事情,那就被剥夺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后连行动力也彻底丧失了。正如阿伦特所言,“对这样的人民,你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将是理想的主体--抑或理想的对手。
骗子的无耻在镜中的对应影像就是被骗者的耻辱--至少在被骗者还保持清醒的时候,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和其它被骗者一样,都在合力支撑着骗子的胡言乱语。对指鹿为马式的谎言鹦鹉学舌,这个行为本身就等于把自己绑在骗子身上,成为骗子的同谋。到头来,统治者的谎言哺育出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他们安于无力挣脱的现状,只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统治者的权力。到了这一步,统治者再也无需编造什么,因为他已是金口玉言,唯一的真理掌控者。
在一个无法分清真相和谎言的世界里,剩下的只有事实和伪装出来的事实。最重要的价值观不再是道德和责任感,而是效用和收益。如果你真的发现了真相,那最好不要说出来;说真的,那太危险了。最好就是弄假成真,假戏真做--狂热的信徒们就是这么干的。当然这样干的总是少数。次优选择就是有意绕开真相,活得呆萌一点--万一不小心知道了,悄悄走开,假装你没看见。这两种人占了人群的大多数。谁胆敢说出真相,不是太蠢,就是想找死。这个世界的聪明人不是耳清目明的智者,而是狡诈精明的鼠辈。这里已经容不下共识,换句话说,要想幸存亦或为借机钻营者正名,那就只能说:无知就是新的共识。
当然,真相这件事--发现真相并通过语言来表述它--从哲学上讲就是很难的。庄子是道家的鼻祖,他说:“名者,实之宾也”。2000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uller)写道:语词的声音必须选择魅惑,因为事物都用它们的质地来欺骗,情感则用它们的姿势去误导;我们写作所倚仗的,是"诡计的真诚“。(注7)米勒的”诡计“是善意的;它和他人的经验进行着自由的交换,对它声明中自带的偏差有充分了解。
类似情况还有,在一个社区中,人们努力向真相靠拢,试图对这个在每个人眼中都有一点不同的世界求得共同的理解。但对那个把雨天说成是晴天的独裁者来说,他是故意要让世界变得无序。他按照自身的意愿去创造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的意味往往和惯常的相反,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得紧紧地簇拥在领导者的周围才能保持平衡。这个领导者愿意为他的新世界创造新人类。从外部观察,这个世界看上去古怪极了,简直找不到一个词去形容它。可从内部来看,它构造得如此精巧,以至于到最后,那个仅剩的还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的人也会开始怀疑,究竟是别人疯了还是自己疯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和记忆,只管咀嚼他被强行灌到嘴里的反刍过的信息。
正因如此,出版自由是独裁的天敌。在权力把选择性事实作为徽章的所在,自由媒体所进行的考证和事实查验无疑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颠覆”(这词来自2013年共产党发布的九号文件,一篇对抗“西方价值观”的檄文,我们稍后还会讨论)。要不然就得宣战:正如川普在CIA总部巡视时的那个声明,他宣称自己正“和媒体干得热火朝天”。(注8)
想要创造属于自己的真相,独裁者就得征服词语。在中国,这不叫压迫,这叫“维稳”、“和谐社会”。在最近十年,和谐成为党最爱的词语:我命令,你服从,这很和谐。和谐就是没人发出杂音。
举例说,“和谐拆迁”就是城市管理者们把房子推倒,给房产开放商让路。在我居住的北京市中心的这条小街上,市政府仅仅提前了一个星期通知,就把街上的小吃店、饭馆、理发店、书报店和蔬果店一律取缔,把门窗都用砖封住。其中一些小店已经开了二十年,也是店主唯一的生计。这么干就是为了把这些人赶出北京,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北京本地人。大幅标语上写着:“我们为市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穿制服的警察全程监督,既负责保护砌砖的人,也防止街道上的住户骚扰。
当中国的领导人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捍卫全球化的时候,他谈到了更加“开放”的中国,可事实上他掌控下的中国正在走向封闭。他还提到了“全球协同联动”,但同时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在完成最后的信息封锁。接着呢,他的发言赢得了掌声,因为全世界都被搞糊涂了。有些人相信习,有些人试图去相信他。还有些人是被权力蒙蔽了双眼。更有些人鼓掌纯粹是耍政治花招,其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那扭曲词语的中国力量并没有止步在国境线上。
这是一个被验证有效的策略:把敌人的词语偷过来变成自己的。正如乔治·奥威尔教我们的,自由就变成了奴役,无知就变成了力量。那中国自然就是法治和民主国家了。这也正是党每天都在宣传的。有一点是真的:中国的确有一部宪法,其中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国也的确有个“国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也有“选举”,公民们过一阵就会被劝诫着去行使他们“庄严神圣的”投票权。
很久以前,列宁发明了“民主集中制”:从理论上讲,这个体制可以民主选举出各个职能部门。一旦当选,它们才有主持各项政策的权力,无人异议。毛泽东后来又传授了“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践中,集中制和专政用起来得心应手;民主则如鲠在喉,从来没有出现的机会。政权的主体们于是乎体验了他们的“选举”,他们“神圣庄严的投票权”和他们的“自由”也成了永恒的闹剧。词语丧失了所有的意义;也失去了信誉。这样一来民众就被接种了疫苗,对颠覆思想有了免疫力。当他们和外部世界接触时(在全球化时代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就不受那些代表着危险思想的危险词语的影响。这些反常的语言让整个民族免疫,并失语。
毒化语言的确行之有效,这绝非空穴来风。思想当然可以操控语言,但语言也可以操控甚至腐蚀思想。"词语可以是微小剂量的砒霜,“维克多·克伦佩勒写道,在他研究第三帝国的专著《第三帝国的语言》中,他这样描述词语的作用:”它们不为人知地被服用,看起来无害,但过不了多久毒化反应就会启动。“独裁的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它们出现的频率,之前为个人或小众保留的现在变成了共同财产,它还为党征用了之前的共同财产并用毒药浸泡了词语、词组和语句结构。把语言变成了它们令人生畏的体系的奴仆,变成了它们最有力的、最大众化的和最隐蔽的广告手法。“到最后德国人已无需刻意声明自己对纳粹主义的信仰,因为它已“通过一个个单词、成语、语句结构渗透到人们的血肉之中,这些被强加于他们的词语通过一百万次的重复,被机械地、无知无觉地采纳了。"(注9)
独裁者的目标是通过语言来占领控制思想。共产党宣传的最终目的是要”统一思想“。而且这是一个必须要再三重复执行的流程。在2017年秋共产党十九大召开前几周,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对宣传媒体呼吁:”我们要统一所有北京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注10)集权主义机器意图统一所有的思想和行动;每一次”思想工作“都有其目的。目的就是把每一个个体的个性、情感、判断力、梦想都剔除。在党担任艺术导演后,只能允许”中国梦“存在。个体只能融入伟大的乌托邦,并把自己的思想塑造成新的形状。毛泽东时代曾经如此,现在又来了习近平。这并非巧合,有一个中国词语因此进入了西方语言--”洗脑“--毛时代领导人的发明。解锁大脑,你需要合适的词语。斯大林称作家是”心灵工程师“。和孔夫子一样,毛也懂得”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
当然,偷用别人的词语是远远不够的。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为新人类创造新的语言。那些令人不喜的词语被剔除,换之以重新发明的新词。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党委派的语言学家就开始编纂《新华字典》,一部代表新中国的词典。政治方面、道德方面新出炉的海量口号和短语充斥了党的宣传稿和日常语言。
从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语言实践到现在仍然构成了“新中国官话”的基础(注11)--这是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Barmé)发明的词语--几十年的套话层层叠叠,逐渐沉积。最先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混入了传教式的、毛派军事风格的学说。之后,党内官僚主义的木刻字又混入了技术官僚的伪科学套话。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贸易的比重渐增,从贸易、广告业和全球化进程散落来的语言漂流瓶也出现在党的宣传中--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无意被渗透。近几年,为了教育读者,从互联网和高科技行业摘录过来的词语也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中。
宣传机器的排放是如此饱和,充斥着封闭的、不透明的语言,以至于很难被消化。习近平不是第一个反对“形式主义”和“空谈”的领导人。在1942年发表的著名讲话中,毛训诫他的同志们,清算“党八股”--因为它们“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这样的文章,毛认为就像“裹脚布”--这是旧时女性用来包住被折断脚骨的小脚的--它们“又长又臭”。(注12)
------------------
时不时的,就有很多人热情地使用中国新官话作为语言范本,在公众场合如此,在私人会面时亦如此。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时期就是典型例子。毛一度被党内的对手边缘化,因此发动了文革--一个权力横行无忌的演艺场。他号召全国的年轻人“炮轰司令部”,打倒他们的老师和教授、他们的父母和党的行政部门--这些部门更关心日常管理和有效的经济运行而非持久的革命。中国的年轻人们,不论男女,都为他们的红太阳毛主席燃烧,他们随时准备抛弃文明的桎梏:对父母的爱、对同胞的最后一丝情谊。等他们闹腾完的时候,中国已满目疮痍。
他们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日常的语言和共识。一个律师,当年的红卫兵,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我们已非人类,我们成了狼养大的狼孩。整个国家、整个一代人都喝狼奶长大。“他的名字叫红兵,意思是”红卫兵“。红卫兵最有名的成员是一个学生名叫宋彬彬,一个将军的女儿。1966年8月,在一百万其它年轻人的注目下,她登上了天安门被毛接见。扎着辫子戴着眼镜的宋彬彬,把印着”红卫兵(红色保卫战士)“三字的袖章给毛戴上。毛问女孩叫什么名字,彬彬,是彬彬有礼的意思么?是的,她回答。”那可不够“,毛评论道,”要武更好一点(要更强悍)。“从那时开始,这个17岁的女孩就改名宋要武。
有一些人更早从疯狂中醒悟。像顾城、芒克、北岛和杨炼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被毛送到农村去的城里人。他们互相都不认识,但被一个共同的愿望团结在一起:净化被宣传机器毁坏的语言,重新赋予它新生。他们写了一些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诗,用的词类似于太阳、大地、水、死亡。被标语轰炸了十年的人们,被这些诗吓了一跳。太阳?大地?水?这些年轻作家以”朦胧诗“出名。自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少此时汉语在他们的诗中重生了。
在独裁社会中,官方语言和非官方语言的隔阂要比其它社会更大。但因为极权体制对私人领域的挤压,人们会在更多场合使用官方语言。结果就是,他们发展出分裂人格--尤其当宣传语言充斥着荒诞的谎言时--最终演化出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双重思考和双重发言:”了解的同时假装无知;洞彻所有真相的同时表述精心构筑的谎言;同时保留两种正好相反的观点,明白它们互相矛盾但仍然对两者都深信不疑;用逻辑对抗逻辑;拒绝承认道德却又提出道德要求;相信民主无法实现的同时又坚信党才是民主的卫士。“(注13)每个主体都扮演一个角色,在邻居面前、同事面前、在政治机器面前--只要他自己能意识到这点,他还可以私下自嘲或叹息。但对多数人而言,这样的表演很快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根本无法彻底分开这两个领域,政治机器的语言总是时时腐蚀着私人语言。
你至今仍能感受到毛时代那些军国主义的革命和战斗口号对汉语的侵蚀,作家们对此尤其痛心。举例来说,美国文学家和汉学家佩里·林克(Perry Link)和社会学家安娜·孙(Anna Sun)就曾写过一个文章,研究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受到多少毛时代套话的影响。安娜·孙指出一种”病态语言“,莫言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从未曾摆脱。(注14)
在日常使用中,宣传式的词语也可能是曲中求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小资”--这个曾经被毛羞辱的阶层,忽然成为新生中产阶级的新宠:人人都想当“小资”。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意味着你可以在新开的星巴克点一杯卡布奇诺奶咖;意味着你懂得红酒应该单饮而不是混着雪碧喝(大多数党政官员和暴发户们在宴饮时都这么喝);意味着你去伦敦或巴黎度假。当个“小资”突然变得很酷。
时不时的,词语或公民都会反抗。很多党曾经用过的战时风格的词语都沦为了讥讽的对象。比如“同志”,它不再仅仅是中国热情的共产党员用来称呼彼此的称号,它还被用来称呼同性恋。还有这个“我被和谐了”。这句话意味着:我被审查系统逮住了,我在网上发布的内容--有时候甚至连我的账号一起--被删除了。当警察邀请某人去“喝茶”,那等着他的肯定不是一杯热饮,而是一次审讯。在党代会召开或有国际领导人到访的时候,或许出名的知识分子、作者、律师或不安定分子会“被旅游”:这个被动语态生动说明了他是如何不情愿离开这个城市。
中国的宣传系统不停地创造出新的词语和句式。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奇幻的矛盾之国,这个社会正快速地枝繁叶茂地成长,并展现出多元化--但这跟党竭力追求的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是冲突的。党试图创造出能统一所有矛盾的术语,然后才能消灭矛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例子。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范式同时包容了左和右、上和下、毛派和新自由主义。语言否定了逻辑,因此它认为自己不可触碰。当然在现实中,它变得更加空洞和荒诞,但在一个只在乎权力而不在乎文字的国度,这其实也没啥大不了。在这里更常见的情形是,词语的功能是要传达一个指令,而不是一个意义:点头!吞下去!遗忘!跪下!所以,宣传机器完全随意地把达赖喇嘛比作阿道夫·希特勒,同时还警告国内的报纸编辑们千万不要混淆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真善美的当然是党和它的词语。
自然而然的,党不能止步于阐释现实,它还得创造现实。“中国没有异议人士。”你要做的就是不厌其烦地重复。2010年,当作家刘晓波被判处11年徒刑时,外交部发言人如是说。2017年,刘成了自1938年卡尔·冯·奥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死于纳粹之手后首位死在牢里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十几年来,刘晓波一直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但在官方文件中,他一直是“被判刑的罪犯”。你说什么?异议人士?“在中国你可以自行判断是否有这么个群体,”2010年2月11日,发言人对记者说,“但我认为在中国这个用词是值得推敲的。”(注15)
在当时,艺术家艾未未是推特上最活跃的中国微博大V。他在推特上是这样分析上面的声明的:
1.异议者是罪犯
2.只有罪犯才有异议
3.区分是否犯罪就是看他们是否有异议
4.如果你认为中国有异议人士,那你就是罪犯
5.为何没有异议人士,因为他们已成了罪犯
6.现在还有人对上述声明有异议么?(注16)
当然,因为艾未未自己也是个异议人士,所以他在中国社交网络上的博客早就被删了,所以网民也很难和他互动交流。推特在中国早被封了。仅仅过了一年,艾未未自己也在牢里被关了三个月,理由是“经济犯罪”。
用孔子的一句话来作结语再合适不过了,这句话习近平最近刚引用过。当夫子的一个学生问他,如果他掌权了,第一件事情会干啥?这位哲学家说:”为政,必也正名乎“。(注17)
全书尾注:
6. 节选自法国作家Roger Errera和Hannah Arendt的访谈“汉娜·阿伦特:来自一次访谈” 纽约书评1978年10月26日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1978/10/26/hannah-arendt-from-an-interview/
7. 赫塔米勒(Herta Muller)《每一个词语都懂得恶性循环的那点事》”Every word knows something of a vicious circle" 诺贝尔演讲 2009年12月7日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09/muller/25729-herta-muller-nobel-lecture-2009/
9. 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 《第三帝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LTI trans. Martin Brady, London 2000 第14页
10. Viola Zhou "北京党的领导承诺在重要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前消除互联网政治谣言” 2017年9月27日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13041/beijing-party-boss-promises-eradicate-online-political
11. Geremie R. Barmé 新中国官话 《中国遗产季刊》2012年3月 29期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glossary.php?searchterm=029_xinhua.inc&issue=029
12. 同上
13. George Orwell 乔治·奥威尔 《1984》 1949年 第34页
14. Anna Sun 《莫言的病态语言》2012年秋季号《肯杨评论》Kenyon Review https://www.kenyonreview.org/kr-online-issue/2012-fall/selections/anna-sun-656342/
15. Geremie R. Barmé 新中国官话 《中国遗产季刊》2012年3月 29期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glossary.php?searchterm=029_xinhua.inc&issue=029
16. 引用自 http://chinaheritage.net/journal/on-new-china-newspeak/
17. 另一种翻译是这样的:上位者所求的,是他的言语不能有任何错误。https://china.usc.edu/confucius-analects-13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