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网络难民
关于他人的痛苦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怵、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我21岁,当时对我冲击之大,几乎惊惧颤栗并跪坐掩卷痛哭。那时我陷于个人情绪的泥沼,在这个充满痛苦不公不义并没有出路的世界里感到绝望并无法自处。那时我相信,对于所有眼见的他人的痛苦,同样的悲痛是唯一的道德。移开双眼就是逃脱,强迫症一般的痛苦是道德赎罪。我在种种地狱景象里惊惧抑郁而昏厥。而这段话像一记耳光:因这些照片(新闻)而痛苦,被它们吓坏,是道德怪物的反应,是想象力的失败,同情心的失败——我们未能把这一现实牢记心中。我发誓我再也不要忘记。
而当时我仍不能明白的是,把这些现实牢记的,还如何有可能不视幸福为不道德。这一问题缠绕了我那么多年,我甘愿困在形而上的道德困境里软成一滩烂泥,直到遇到几位教会我边界/责任/行动的老师才渐渐被注入骨骼。”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躯体症般的痛苦除了求得自己良心的宽恕,没有任何用处。要行动,而行动的匮乏是新的困境。解脱的一刻来自这次顿悟,尽管我是如今回看才发觉的:边界的明晰同时解救了庞大的无力感和无边的痛苦自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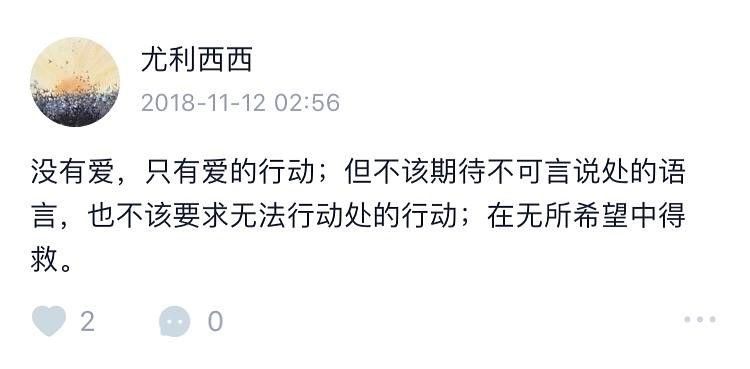
这些回溯是因为这次疫情中我惊讶地感受到/见到了巨大的失效:同情心的失效,共同体的失效,国际主义的失效。无法不再次回想起”关于他人的痛苦”这一话题和这本著作,重读发觉尽管文本本身是关于战争与摄影的,其论述却对当下种种现象依然有效。在试着解答自己的困惑前,想先借用桑塔格的另一篇文章《对灾难的想象》来梳理疫情至今的发展。
这篇文章本身是对科幻片套路的一次总结和分析,但,是的,就如”鄂尔诺贝利”所揭示的,近三个月的世界与一部灾难片的剧情惊人的吻合。标准的故事情节一般经历五个阶段:
(1)某物之来临(如魔鬼的出现,外来飞船的降落等,此时是新冠病毒)。通常,这是由某个单独的人、一个正在作实地考察旅行的年轻科学家首先看见或察觉到的。但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无论是他的邻居们,还是他的同事们。
(2)许多目睹此物造成的巨大破坏的目击者证实了主人公的报告。地方上的警察被叫来收拾局面,料理被杀害的人。
(3)在该国的首都,科学家与军方举行联合会议,主人公站在图表、地图或黑板前做陈述。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接连收到有关更严重破坏的报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乘坐黑色豪华小轿车接踵而来。在地球处于生死存亡的考虑下,国家之间的紧张冲突被搁置起来。摧毁来犯者的计划被制订出来。
(4)来犯者制造了更多的残暴行为。国际力量进行了大规模反击,火箭、射线以及其他先进武器接连精彩亮相,可全都无济于事。数座城市被毁或居民被疏散。这里肯定会显示一个人群惊惶失措的场面,他们蜂拥在某条高速公路上或某座大桥上。
(5)进一步召开会议,其议题是:“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无法抵御。”整个过程中,主人公都一直在实验室里,为寻找到这个东西而工作。全部希望所系的最终策略被制订出来;终极武器——通常是一种能量巨大但尚未进行过实验的核装置——被架装就位。倒计数。魔鬼或入侵者终于被挫败了。人们互道祝贺,而主人公则和他的女朋友紧紧拥抱在一起,眼光坚定地扫视着天空。“但愿不再见到他们了。”
危机发展至今,基本也符合了这一路数。又或者说,在面临真实的灾难而不是想象中的灾难时,我们的表现并没有比电影好太多,甚至远不如。最先观察到危险降临的是医生和科学家,现实比这份总结更进一步,不但不相信他们的预警,反而判为谣言,予以训诫。我们最终的希望——所谓终极武器的找寻——仍落在医生与科学家肩上:目前的种种证据表明,在有效药物和疫苗问世前,这场灾难都不会终结。重新拥抱彼此挥别病毒的胜利大结局就不会到来——而彻底赶走入侵者,回到日常状态的大团圆也是一种科幻想象,与入侵者共存的卵痛局面则从不在考虑之列。危机之后的记忆也自不会被科幻电影囊括,而现实中记忆的争夺和篡改已经开始:对苦难和殉难的悼念,不只提醒着死亡、失败、受害,(完全不)敦促着反思和保持警醒,在贵国这里,是对幸存奇迹和伟大胜利的讴歌,不许不喜庆。“根本不存在集体记忆这回事,但却存在集体指示。”
科幻片最naive的点则是,幻想一种足够大的灾难的到来,可以消除国家间的一切不和,并促使各国最大程度地把地球资源集中起来。这在且仅在科学与技术层面勉强成立,病毒编码的开源,各国的数据共享,共同的医药临床试验,是这场灾难中不那么糟糕的部分。而桑塔格所说的,科幻电影反映出的乌托邦幻觉,则在现实中彻底被证明只是幻觉。
“在古典的乌托邦思维模式中——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斯威夫特的慧骃国,伏尔泰的黄金国——社会达成了一种完美的共识。在这些社会里,理智取得了对情感的牢不可破的优势。因为所有的分歧或社会冲突在理智上都站不住脚,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现。”而事实上,所有之前潜藏的或多少加以掩饰的分歧都在这次危机中浮出水面。在此之前,曾痛苦于人类族群之间的分裂,身份像道牢不可破的屏障,限于某地的某些人的痛苦难以穿越这屏障而获得理解和共情。曾以为全球危机将我们置于同样的境地下,将带来更大的国际连结和更广泛的理解,现实却是万我归一仍是一滩泡影,这里并没有“我们”存在。对于他人之痛苦,在全球性的威胁下,有的不是更多的共情,而是人人自危之下的排斥异己与暂时安全的侥幸(若不是幸灾乐祸)。种族歧视与地域歧视大行其道,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愈发露骨,并仅仅是个开始。无论在中,在港台,在意大利内部,在欧盟,在美,在更广泛的整个世界。
另一个观察是,科幻电影中绝对没有社会批评。「没有对造成无个性和非人化的那些社会状况的批评,并且科幻的幻像还把这些状况归于某个外来的“它”的影响。」贵国人对这点应该毫不陌生。先前已经实践过的各种统治术和数字极大爷权手段,在这次之后只会越来越明目张胆。我为自己曾在初期认为人们会认清这些手段的压迫性而多一些反抗耻笑自己。可以为了“安全”而割让的自由,可以心甘情愿一割再割,并从此有了如此“名正言顺”的先例。就细节而言,西欧当然好得多,但总体上仍然是卡其亚里所说的:危机/紧急状态中行政力量必会加强,只要危机一天不结束,权力就高枕无忧。
尽管这个世界的灰暗前景让人悲观,我个人情感和理性上最不能接受、最感到困惑的却还是…个体共情与国际社会的失效。在面对病毒时,我们并没有作为整体的人类来面对,所有的惨痛代价,仿佛什么都没换来。不仅在国内,也在国外。没有经验,没有教训,病毒每敲响一扇门,门内的人都重新被病毒打得措手不及,狼狈之至,一而再再而三。
从1月底武汉封城开始,就生活在巨大的分裂中:注意力无法从疫情上转移开,那时发生的事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不为过,而同时却要走出家门走入一个照常运转的世界,打起精神面对所有若无其事的身边人。这种超现实感在意大利疫情爆发后又体会了一遍:在这里整个国家已经停摆,各项数字每天都在飙升,北边一些暂未爆发的国家却仍然一切照常,毫无紧张,大型蓝色卡通人物集会,照常的无防护的选举投票,换个地方开party的年轻人,人满为患的草坪,他人之痛苦、邻人之痛苦仿佛视若无睹。为什么人们可以像无事发生那样生活?当确实正在有颠覆整颗星球并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发生?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当世界某个角落发生战争,尽管也满是人道灾难但地球上其他遥远居民拥有有不关心的特权。但这次,于情于理都太难接受。为什么?
追问是必要的,若觉得当前的应对不够理想、若不想灾难再次重演。但或许首先该明确的一点是,在疫情下(在平时更加困难的命题是当面对遥远的苦难),究竟怎样的生活才是可接受的、“正当的”、“道德的”。我无意也无能力断言何种具体措施才是有效的,而仅能提供一些笼统的应然的想法。疫情比起平时在论述上的方便之处是,每个人都是直接受冲击的,每个人都是直接的责任体,无人能独善其身,无人可逃脱这种责任(而我们每个人普通应该为西非的饥荒负责任吗?应该为北极冰盖的融化负责任吗?应该为某地发生的屠杀负责任吗?如何负责?这艰难的多)。
但即使是全球化的危机,灾难也不是均质地降临的。每地的反应应当与当时所受的威胁相匹配,也因此,我们应允许多样的生活。众多无下限公众号在面对别国的存有差异的政策时,那种“满分作业不会抄”论令人作呕。这种种对别样生活的惊异和“痛惜”“恨铁不成钢”中并没有对他人真的关切,也并没有对“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供任何解释。况且,贵国算哪门子的满分作业。同样是“lockdown”,具体执行与其他配套政策千差万别,而正是这些细节形塑了我们在灾难中的生活。我们批评武汉式封城,批评的不是“限制流动性”这一点(相反,不少人觉得封得太迟),而是完全没有封城后维持社会运转的预案(“无政府”状态持续了几个星期之久)、没有任何弹性空间和保障机制以及后期非人性的措施,当时的惨状相信大家有记忆,就不再一一列举。拿“西方也封城了”作为贵国制度优越的证明,又蠢又坏又没自知之明。事实恰恰说明,封小区是不必然的,切断一切交通是不必然的,在家断粮、医务上不了班吃不上饭、儿童无人照看饿死、非新冠病人得不到任何救治丧生等等次生灾难更是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但我不认为西欧国家的应对就完全没问题。问题出在,措施仍然采取得太迟,遏制疫情蔓延的黄金时期仍是错失了。直接问责当然要问政府,可普通人的防疫心态也与国内大相径庭。不少人有与我相似的不解:为什么在意大利、美国感染和死亡数字如此可怖的当下,当地人都依然不太紧张?
首先,您国是否真的为全球争取过时间?我们的紧张和痛切比起统计数字,其实更多来源于在各种非官方渠道如微博微信豆瓣看到的活生生的个体的呼喊。有人认为西方媒体双标,先是极力渲染您国疫情之严重,当蔓延到自己时又轻描淡写说只是个大流感。我不太能认同。相反,我觉得西方从来就对疫情严重性的认识不够,而这是您国的责任。您国靠着一道高墙,有如一个黑箱。防“境外媒体”更甚于防毒。在1月份,墙外真的有哪个国家是完全掌握了武汉真实情况的吗?就我看到的意媒媒体,没有哪家能触及到这些非官方的个体叙事。在靠自己的记者无用的情况下,WHO的误导和包庇是另一方面——在疫情已经全球爆炸之后pandemic的定性才姗姗来迟简直是个国际笑话,您国“可防可控”极力淡化,最应该起到预警作用的国际组织又完全失职。没有一个对国际社会尽到了责任。但各国对疫情的判断失误和延宕也是难推其厩的,在已有惨痛先例的前提下,还在一段时期内低估潜伏期传染性、重蹈坚持重疫区旅行接触史才检测的覆辙因而错过了最佳防控期、只测有症状或重症者等策略(当然,这些也是写在WHO指导意见里的,若提前对这些预防关键点发出警示,现在的世界会不会完全不同?),是不能单纯推给检测能力限制的——是整个前期准备的不到位。
而另外有朋友提到过,在疫情蔓延至全世界前,西方世界对疫情的处理是他者化的——这是局限在某地的属于他人的问题,我们仅仅是旁观者,在心理上并未将自己纳入这场灾难的一部分(再次强调,“全球性危机”的预警来的太迟太迟)。旁观者心态解释了前期的掉以轻心,不得不承认,即使作为中国人,从初期开始密切关注疫情,在意大利刚刚出现10几个病例时,也完全不能、不敢去想象之后的情况会如此惨烈。可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后呢?分水岭应是封国令的下达,虽然我们大区停课停得极早,总感觉疫情仍然只存在于新闻里,身边是一如既往的宁静,在封国之后才真正感到人们紧张起来:大街上空无一人,超市店员强制性佩戴起口罩,路人的戴口罩率也直线上升——今天大概有80、90%,邻居们自发地在阳台上挂起 #iorestoacasa(我留在家中) "tutto andrà bene(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的旗子和意大利国旗,疫情好似终于来到了生活中(尽管它一直都在)。




而个人认为这种与疫情的距离感其中之一的原因是,与科幻电影靠视觉冲击直观展现人类社会的毁灭和危机不同的是,病毒这一人类社会的”入侵者”造成的危害虽大,却相对更加隐形:病毒本身是不可见的,病死数造成的冲击也更多是情感上由统计数字转化而来的,而非直观地视觉的(像Ebola 视觉冲击就足够震慑人)。这种由数字带来的对疫情的认识,为人们对受害者(感染者)的共情设置了障碍,也因此个体叙事是如此重要:在并无太多人道悲剧的社会,这种不可见性使人产生危险离自己很远的幻觉;而60岁以下较低的死亡率,更加使年轻人掉以轻心。论及本质,是当人们面对疫情时,从未作为一个共同体,而是割裂成了一个一个的“我们”与“他人”。如桑塔格所写,当问题涉及观看他人的痛苦时,任何“我们”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虽然随着疫情的加重和各国居家令的一步步升级,人们的认识已经产生了变化,却仍然有诸多“无感”和“轻佻”的不负责任行为:因违反法令开出的罚单在各国都不在少数。又或者回到当意大利已经“水深火热”别国人却依然在我行我素这一问题,我认为道德谴责无太多意义,我更关心“为什么”。在桑塔格的书中找到了两种解释,一是有关信息的长期过载有关,使人们更难有效对新闻作出反应、将其转化为与自身相关的事。公众注意力虽然受媒体注意力左右,「但在一个影像饱和,不,应该说超饱和的世界,本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文本虽是论述影像对新闻阅读者同情心反馈的影响,在我们这个已经步入“后真相”、信息严重过载的时代,却总体上仍适用。
她引述了对一位萨拉热窝人的讲述,读来戚戚:「“一九九一年十月,塞尔维亚人入侵克罗地亚,那时我住在平静的萨拉热窝,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我还记得,晚间新闻播出两百里外的武科瓦尔被摧毁的画面,我当时就暗想:‘啊,多可怕。’然后转台。你说,如果法国、意大利或德国有人日复一日在晚间新闻里看到发生在我们这里的屠杀,说一句‘啊,多可怕’,然后转台,我怎能愤慨呢?这是人之常情。”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这是她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的重要原因——就会冷漠。」当人们感到自己安全,外出野餐、驱车度假这种再正常不过的欲求,又怎好愤慨。
与之相关联的是第二点,灾难的尺度与人们行动能力不相匹配。「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就好像任何一场战争,看上去像无法阻止,至少个人的力量在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才对遥远的他人的苦难反应迟钝。而即使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也都有举手之劳的事情可做就可做出微小的贡献(如海洋垃圾或全球变暖问题),「苦难的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有必要多“关心”,但也会使他们觉得苦难和不幸实在太无边无际,太难以消除,太过庞大。一个这样的尺度上的苦难,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但是一切的政治,就像一切的历史,都是具体的。)」
这使我想到了对这次疫情中自组织行动在国内外的差别。国内爆发出的惊人的组织能力固然值得敬佩和骄傲,却不应忽视,其基础却是大量“本应当”的缺位。若不是因为政府之瘫痪和无能,红会之腐败和腐朽,对媒体和NGO长期的打压,本应有的或官方或民间支持机构/组织的缺失,大量的使人无法无动于衷的无比具体的个人的苦难,我们本不需要被逼成这样。每个人都承担了个人职责之外的由道义施加的责任。而在一个分工成熟的社会中,法令本身已经考虑到对各种群体的冲击,支持机制也非常健全,普通公民需要关心的自然只有自己和周边的生活。当疫情失控发展,人们最先审视的也是现有机构的职能是否履行、是否饱和,行使的是监督之权利与义务,而不是“越界”由个人去填补缺失。这并非在道德上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个人主义,而是在行动层面的无事可做无能为力——但依然,如前所述,成熟的社会分工也加固了“我们”与“他人”的分野,而在这场疫情中,每个人都必须要承担责任,这是每个人的事。
#iorestoacasa 也正是一种疫情与自己相关、站出来承担这部分责任的宣告。在意大利,这一hashtag的创建是决定性的:不但明确了每个人都与之相关,也给出了一种简单易行的行动方针,使“我们”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又不会使人茫然无力。看起来这是好的开始,截止今日,意大利重症监护人数已经连续10天下降,新增确诊百分数也以2.02%达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希望一切都很快能好起来。也希望这场疫情中的教训都不被遗忘。疫情过后,仍然有太多太多的苦难需要我们的行动,有许多更加可怕的事情,需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去避免它的发生。面对他人的苦难,如开头所说,希望我,希望我们,都能做道德上心理上的成年人。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