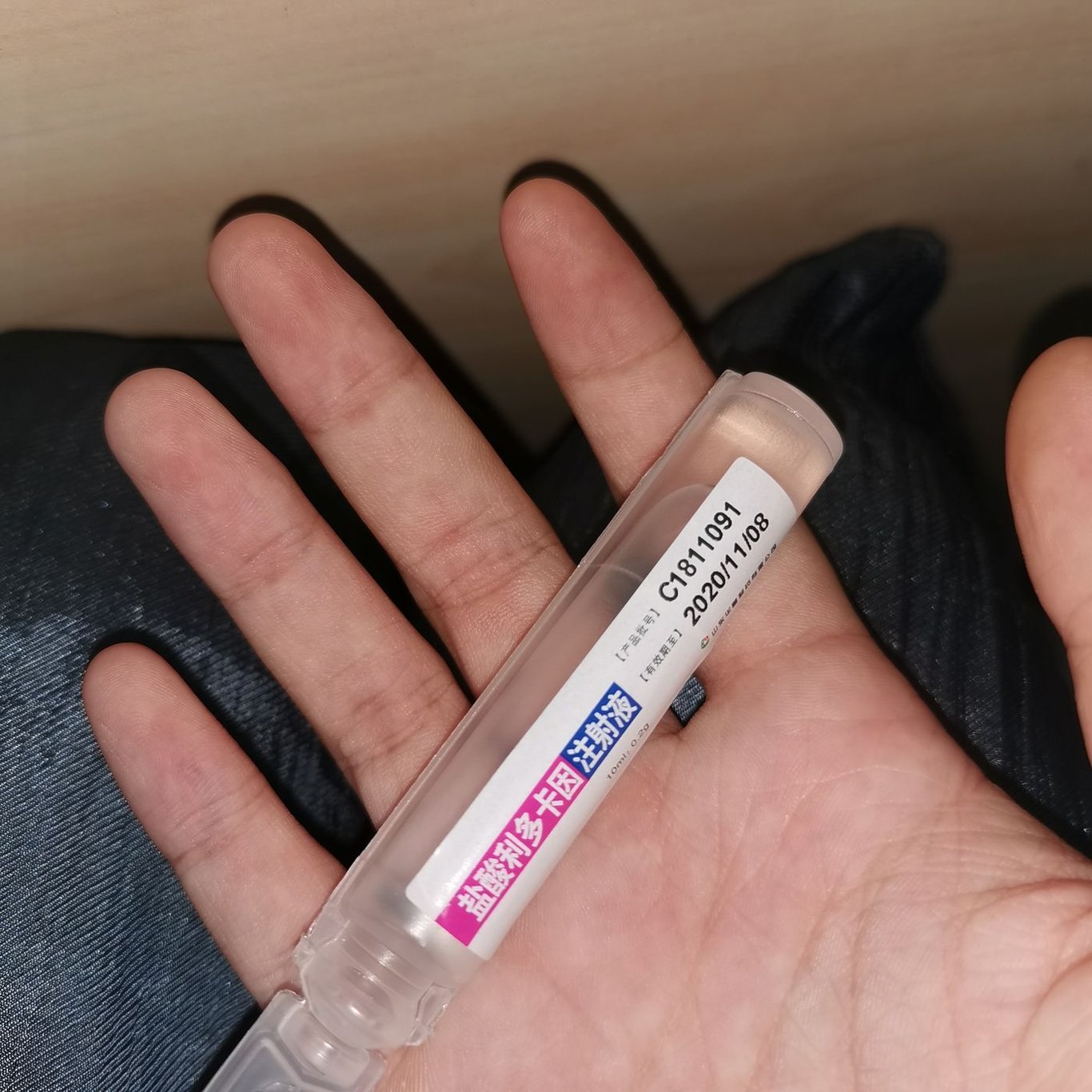
体认性别
与银幕的记忆
01
家乡第一个电影院建起来时,我已经读初中了。初一,2009年。正缝哈利波特最后一部上映,周日的晚上吃完晚饭买一张夜间的票,看完《死亡圣器》的上篇,然后等爸妈接回家,第二天继续上课,在社交网站发一条文字,表达一些幼稚的感想。
中学时期大抵都无法逃脱对奇幻故事的喜爱,在我跟我的笔友,一个同龄的、相隔2000公里的女孩的书信中,我们总是会提到《哈利波特》的故事——尽管我现在已经很少想起了。遗留下来的,似乎只有那天饭后走到电影院时的激动。
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用纸质钞票买票,检票,买爆米花,看电影,成为一种公式和共识。人很少,厅很小。
也就是说,在初中之前,其实并不能时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家乡的居民在此以前一直在政府的礼堂里进行一些观影活动,但是大多是带有浓厚宣传意味的非院线片。我们无法通过当时电影院的广告和咨询得知院线时兴的潮流。而后城建将礼堂推导,大人们言说是当官的考虑某种风水,自此唯一一个公开可以容纳多人的室内空间没有了。
所以直到2009年以前,我对电影院的记忆都是有限的。
但对电影院银幕和静坐观看影片这一行为的痴迷是一直在发生。因为被父母管教,而每次借口自习、上课却都是在看电影被发现时,似乎他们也并未真的责备我。初二时补习班认识的男生,在周末一众朋友约出一起玩时,我提出的看电影邀约显得非常幼稚。在他们的语言与时髦里,看电影并不是一件刺激的可以交换秘密的活动,不是足够认识朋友来展现自己魅力的场所。
而后便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02
2015年第一次念高三时的状态很复杂,游离在校园里,而总是三不五时地上电影院“避难”。
为了逃离一种无法适应的社交制式,逃离自己的失败,也为了建立起自己有限的、关于着迷的艺术体验的优越感。
赶着看《星际穿越》的首映,只买到午夜11点的票。当时我是诺兰的粉丝,半夜跑出家门时被家长大骂,但结局是一个人走出影院时还是能被沉默地接回家;临考前的三四月,《一代宗师》加长版上映,也去电影院与它相见,看完后回到教室与当时的同学A讨论加长了什么剧情,但因为与他讲话太过投入被班级里的小团体排挤。
我总是很不适应那些规则。并不是一个离群的人,但对于群与“我”的边界却无法辨析明确。我不知道为什么与大家都讨厌的同学A聊电影会成为一种“我也是异类”的标签。即便如若不是写这篇文章,我已经快要忘记这个人了。但我仍旧记得加长了电影里一线天的情节:“一线天封刀,为什么封刀,他与叶问的决斗……”,只此而已。
对话和银幕的光照停留在记忆里,伴随着沉默的氛围和充斥所有感官的声响。电影是视听的艺术,这是银幕给予的。
03
2017年除夕与她看的《降临》,是我至今为止最喜欢的科幻片。因为是年夜,街道的店铺都赶早关门。步行前往的路途中飘满了红色鞭炮燃放后的细屑。冬天是寒冷的,我不知道她的体温有没有我的高。但这部电影也是冰冷的,冷冽的克制的声效却讲述带有温度的故事。
从那以后我会留意特德姜的作品,尽管我并不是一个科幻迷,但很多时侯并无法找到从当时银幕里获得的刺激——当我与她,当只有我与她端坐影院正中,在所有家庭都认为自己需要“欢庆”和忙碌的日子里享受属于我们两人的时间时,我是得意和幸福的。
我很难辨明,我喜欢的是,只是她,还是喜欢的是,那一块光影。我时常会想起那个时刻,那一天,和那之后我们破裂的关系与情感、无法重温的默契、与之相伴的艺术的浸润。
04

2020年六月回到上海。当时供稿的自媒体老师要求我写与延期的上海电影节有关的文章。带着对70%座位被封条封住的愤怒,行文里充满着对防疫制度下有限观影人次的鄙视,以及自疫情开始关闭电影院的评价。质疑这“70%”是为何,质疑这封禁了近乎半年的、属于所有人的银幕为何不能向大众敞开(在当时的政策里,上海已准许其他聚集性文艺活动的出现,居民出行和商场等一切人流如常,所以电影院限流让我非常不解)——当然,这种质疑非常幼稚,也站不住脚,不过一位看不到电影的人的愤慨无处发泄的尴尬。
后来,果不其然这篇文章被批评“充满了自由主义的阴谋论”、“无稽之谈”,其实初稿发出时就已做好这样的准备,但最后修正的版本也未见去除我的愤怒太多。所幸平台并没有审查这样严格,我甚至也认为有人与我一样需要这份缺失了的关于银幕的记忆,尽管在人命关天的防疫政治之下,这是无足轻重的。
但对我来说却是很重要。逃离当时疫情时民众悲愤的窗口,我需要的是一个宽敞的视听空间,一个“避难所”,一个”港湾“。五六月时的上海,民众出行购物已然照旧,甚至话剧演出都在进行,当时寄希望于每年六月下旬的上海电影节,然延期后官方却只放票70%。
这一举动在尔后几个月后才慢慢放松。许多城市如此,需要被复兴的电影院并不是所有人生活的必须,而缓慢上映的影片,也都滞留于当时的生活之外。
当时在微博里写:”以后人回想2020年上半年,能想起疫情、疾病和死亡,可能还有逐渐显现的关于身体、欲望的记忆碎片。因为餐饮业逐渐恢复,娱乐场所也照旧营业,人们随时可以去到商场里购物,玩乐——但这些都跟电影和银幕没有关系。看电影这件事被天然地隔离在了整个看起来已经不再失序的日常生活,从所有国人(甚至世界上大部分人)的记忆中空缺了。这不可怕吗?太可怕了。”
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不需要这一个空间、这一份情感。他们不需要电影院吗,为什么呢?
05
对电影节的痴迷和上文的愤怒,大概也如出一辙。第一年参与siff,不熟悉上海的行政区划,跑到距离市区3h距离的地方看最晚场的《搏击俱乐部》,结束后大哭一场,把邻座的陌生人吓坏。从我尚在痴迷奇幻的霍格沃茨世界的年纪第一次看它,到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它已经过去了许久,这之中尽管反复看过许多次,我都免除不了它在银幕上放映时给我的激动。好像时间从这部电影、那部电影中走来走去,但留不下最稚嫩时的心境。
后来我因为看电影认识了一些朋友,我们的交流有限:通过在影展给对方互相抢票来维持。一年又一年的碰面,在电影院、在电影院门口的便利店、在电影院附近的地铁站。我们交换影票、票根、留念,聊天,分享最近看的电影,除此之外无他——其实几年前我与同学A也是这样的谈话。
得益于这些朋友,我收到了某部小学时最爱电影的ost,也收到许多抢不到的影展票。体验是宝贵的,记忆就是需要留在当时当刻。
06
人逐渐成长的过程,就是易于回顾过去,而惰于为事件赋予“意义”。
9月时上北京,看了北京电影节的几部老片。因为做了今村昌平的特展,但是却不够完备,胶片版《被偷盗的情》放映之前组委会到前排说胶片因修复问题无法放映,中间存在断裂,改为数字版放映。现场北京腔四起,大抵是要讨一个说法,但被主板方以退票“威胁”,寥寥几人散去,最后还是看了个数字版。因对胶片电影缺乏研究,这也构不成我的“意义节点”,不过是一次有趣的谈资:原来胶片电影的放映次数是有限的,它需要被保护。
独上北京的那段时间,大多都是一个人。我从未想为我“看电影的旅程”找一个怎样的伴侣。每天起床看电影,睡前看电影,辗转不同的影院,然后吃并不地道的北京美食。像过去几年间在上海辗转的6月,或者7月,在许多熟悉的地方,我时常能够想起“我在这里看过什么电影”,而不是“与谁做了怎样的事”。但那些私享的情绪很难分发出,成为淹没在浮躁生活里的碎片。
所以当向朋友解释“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北京看电影呢?”时,我有些不知从何说起。看电影为什么需要许多人一起呢?它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啊。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