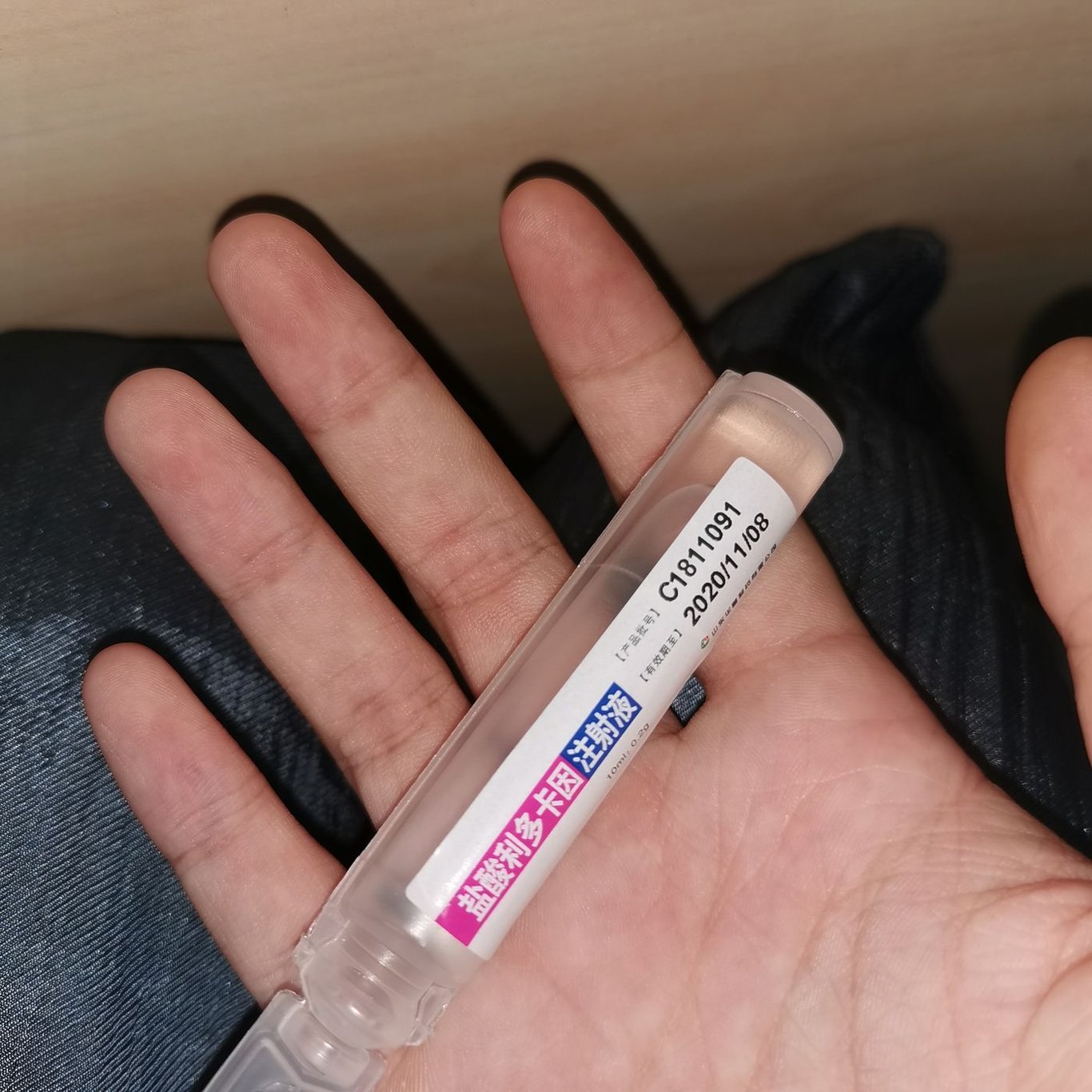
体认性别
梦日记 / 非论文写作 02
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 第一次,我步入她的场所,她在我的身边落座。讲着会跳跃、让人捉不住头脑的话,迷迷糊糊,有些会令人发笑,但是囿于体面和礼貌,人会聆听,我会聆听——那是第一次,二零二零年六月。 她当时说了什么?说自己的摇滚乐前男友,说自己偶发的性癖,还有说她会做清明梦。 “就是会做那样的梦,梦里你会让自己飞起来”,这句话是我说的。 她说了什么呢?我记不太清了。那是我唯一一次做清明梦,尔后很久都没有再经历过那个梦境。而她偏偏又在那个时刻跟我提起,以至当时的时刻我对于话题的回应只是兴奋和刺激。我或许漏掉了点什么:应是一个忽明忽暗的信号,在我们饮下的酒精之间,信号告诉我,我已经快要掉进洞穴、或者醒不来的梦里。 如果我知道第一次就是唯一一次的话,也许我会想方设法来干预自己的大脑:留住一些可以控制梦境的瞬间、手段,我知道这不可能,也无法促成我们对巧合、邂逅、奇遇的想象,但是我就是想要。 可能从那个时侯开始,梦境就已经发生了。

Rebel/语言
一年前,写作论文时,我在自己的田野笔记里写:“课堂没有教会我们,不要爱上自己的田野对象”。其实课堂正在试图教会我,只是阻隔了大约365天,才让我触摸到那些知识和信息。
十二月初,经导师反复提醒应当做的阅读,在酷儿方法的文章里有作者写Sexuality Study那些暧昧的时刻:受访者与研究者的调情情绪,在许多微妙的、互相识别身份的瞬间。我知道那“不合常理”,甚至也许,不应该被记录在“学术”之内——或者仅仅是我们习得的、我习得的有限的中文语言训练,在排除这一套不正确的记录方式,排除这种不规范的、缺乏逻辑框架、所谓“问题意识”的记录方式。
为什么呢?那我又应该如何去叙说,我对她的迷恋。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记录我在她身上闻到的气味——这并不是一种宿醉后的独有的气味。有时候我会想到,这种迷恋与朋友闻到自己伴侣身上的特殊气味很类似。只不过不同的是,她并不是我的伴侣。
一年后的如今,尽管我能够在方法文章里读到英文学者论述自己性研究的边缘行为,它们也并不能真正地开解我所遭受的故事。学者和论文能够在Conclusion里写下的,是去拥抱那些“酷儿”的时刻,拥抱酷儿的记录方式,拥抱不规范和琐碎的写作、色情的描绘。她们在文章里“大言不惭”地说:不应该放任这些不规范的数据被删除,也许留下来才是对这个充满霸权的学术界的反叛。
反叛。可我没有这么大的野心。甚至在叙述与报告我的“阅读成果”和回忆当初的田野故事时,导师也建议“你可以将你在田野里同样的经验写作成论文,会是非常好的方法论反思”,但是我不想,我不愿意,我只是清楚地知道,那些都是梦境而已。
梦境不会因为你有优秀的学术语言而变得更精彩,那只会带来毁灭。
Yume/名字
一年的时间其实很快,快到当我间隔365天再见到她时,才会警醒自己这一年的糟糕——这是一个瞬间的事情。我对她说,思思,我的二零二一非常糟糕。她没有说“我也是”,只是跟我讲如何与以前的同事全部划清界限,把她们一个个拉黑,然后把她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删除。
她讲,她开始尝试约会,使用约会软件,但是对方也许是介意她的身份和工作,而把她的联系方式删除,让她完全没有机会。
她还说,她现在去了新的环境,有了新的伙伴,还有新的名字。她们总会在不同的场所,有不同的昵称。名字总在变化。但她仍旧能够在ALWAYS吧台,找到写着自己旧名字标签的酒瓶。
我还是很喜欢听她讲关于她自己的琐碎。即便我已经不是那个研究者,我也应当跳出这个身份,但我还是无法免去在见到她时无端产生的好奇和希冀连接的心理。但这种心理曾让我惭愧。
而今我能够用“迷恋”这个词来概括与她相与的情境,是否也是因为我已渡过了在夜晚、无助、眩晕的清晨,对她的惭愧。
我反复回想,一年前在田野场所里穿梭、买卖酒精的日子,与她。反复回想,我们经常去的ALWAYS,木制吧台上的一排五颜六色中文名片,我反复回想,她的绒毛外套,白色的小貂皮、她的发卡、脸上的痣、红色的,古时候人们会称作是“蔻丹”的玩意。(为什么此时,脑海里是这个词语呢?)。我反复回想的同时,我又反复想要亲近,亲近关于她的回忆,和能够触摸到的木制吧台,气息。
我意识到我对她的迷恋,并不仅仅是情感上、身体上、生理上的,更多地,夹杂了我对情绪的贪图,对与她相伴的那些“梦幻时光”的贪图,对于一个放纵大笑、哭泣的时刻的贪图。
我想要拥有她。
她同我的潜意识般,会唤醒我对于声色犬马的记忆,在一些微不可察的时刻,一些我迷信的“巧合”的时刻出现时,我会掉入那个漩涡,那个我曾称为兔子洞的地方。
是的,有一个洞穴,有一个洞穴可以容纳这个思绪。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G,他以前会说,曾经碰见的令他心动的女孩,每一次与她的对话,都像是他们在自己创造的洞穴里。“一个属于我和她的洞穴、岛屿、独立的一隅”。
我以前会笑话他的语言,带有漂浮的酸气。他总是喜欢用比喻句,或者奇怪的通感。但今天却是真实的体会到抽象赋予我们的特权,让我们能够不真实地来描绘自己无法立即付诸具象的碎片。
G还总是喜欢说,“好像梦一样”,“Jing,好像在做梦一样”,“不可思议,就像做梦一样。”
这串话反复跳跃在我脑海里,不是因为G,也不是因为我确实与现实生活相割裂,只是因为她昨天耳语她的新名字,
“Yume,梦,我的新名字”
好像一场梦一样。
Yume,好像一场梦一样。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