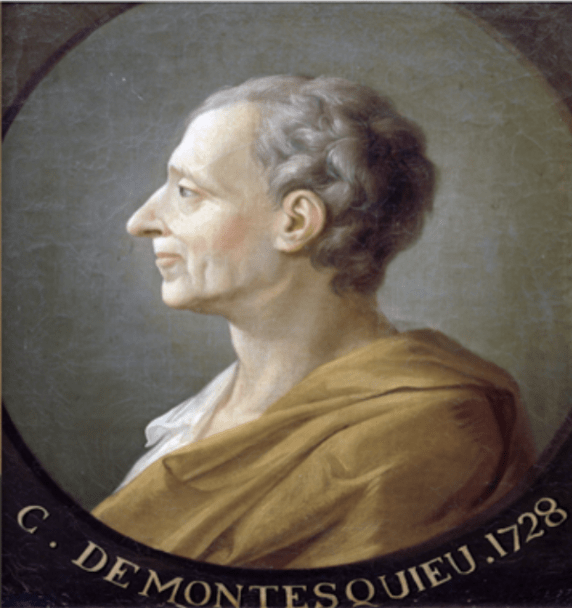
人一个
努斯鲍姆炮轰巴特勒:“我的一张大字报”
ps :昨天写努斯鲍姆一个札记时,发现她在1999年的新共和上与一群女权主义一场论辩,参与者有 Joan Scott ,斯皮瓦克等,令人心潮澎湃。找了很久,才在Martha C. NussbaumInterventions, Philosophical 一书中找到出处。看了,文笔并不难,一半借助软件,迅速翻译,并校对之,细读之。后发现有译稿:努斯鲍姆《戏仿的教授,评朱迪斯_巴特勒著作四种合评》(译文不错,略有小错,不太影响阅读),不足在于,斯科特等人的批评与努斯鲍姆的回应没有收录。下文全文译出,文章很长,文前做摘要。
我也着实没想到,努斯鲍姆竟如此猛烈地炮轰巴特勒。在同阿玛蒂亚·森合作许久后,努斯鲍姆对那种言辞华丽,扯东扯西,不知所云,与现实又无任何关系的左派激进,已无法忍受。观东观西,所谓的激进左派,差别不大。努的这篇文章,也让人着实看到,真正的左派是什么。无怪乎,斯科特在文后直接祭出了“罗伯斯庇尔”
努斯鲍姆, The Professor of Parody,评巴特勒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1997);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1997);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1993);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1990)(新共和,1999)
文章摘要
1、美国出现新的、令人不安的趋势:女权主义理论对美国以外的妇女的斗争关注相对较少;几乎完全从生活的物质方面转向一种口头和象征性的政治,而这种政治与现实妇女的真实情况只有最微弱的联系,以符号女权主义(象征女权主义)为代表,表现有两点,第一、他们的女权主义表现为在高深晦涩和不屑抽象的学术刊物上,以颠覆性的方式使用文字,而且认为这种姿态技术就是政治抵抗的形式,第二对变革持悲观态度,认为包裹性的权力结构无法挣脱,无法改变,能做的就是做一些象征性的、嘲弄性的反抗,这也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抵抗的形式。
2、巴特勒晦涩难懂的表述及其引用方式,与清晰地解说问题本身无益,只不过是一种延续某种大陆哲学的塑造自身权威的方式
3、巴特勒认为性别是社会权力建构(《性别麻烦》1990),毫无新意,而且她的观点自然引向一种悲观论点:我们已经彻底被塑造,无法自主自身身体,旋即转向表演性的实践,认为这是在无所不在的权力空间中的抗争;这便是人的能动性小小的用武之地,也是她在Excitable Speech说的一种讽刺性的希望。
4、巴特勒强调可以通过颠覆性的模仿性的实践,抵制无处不在的性别霸权结构,这是一种道德被动的立场,背离了甚至与她一样持有社会建构观点的早期女权主义者;事实上,颠覆的形式和反抗形式极多
5、巴特勒认为完全逃脱是白日做梦,能做的就是模仿性表演式的颠覆,这是一种危险的寂静主义,为虎作伥,等于告诉人们奴隶制无法改变。她传递的是一个残酷的谎言。受压迫的女性更需要的不是这些言辞,不是这些模仿性表演
6、美国的女权主义失去了公共担当,更愿意注重培养自我,而不是以帮助他人物质条件的方式来思考。这种寂静主义就是与邪恶合作。
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或译学院派)的女权主义一直与为妇女实现正义和平等的实际斗争紧密相连。女权主义理论被理论家们理解为不仅仅是纸上谈兵,相反理论与社会变革的建议是相通的。因此,女权主义学者参与了许多具体项目:改革强奸法;为家庭暴力和性骚扰问题赢得关注和法律救济;改善妇女的经济机会、工作条件和教育;为女工争取怀孕福利;开展反对贩卖妇女和女童卖淫的运动;为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社会和政治平等而努力。
事实上,一些理论家已经完全离开了学术界,他们觉得在实际的政治世界里更舒服,因为他们可以直接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那些留在学术界的人经常以成为坚定的实践型学者为荣,眼睛总是盯着真实女性的物质条件,写作时总是承认那些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斗争。例如,读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注: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任教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及哈佛大学法学院,主要关注性骚扰和色情文学)的一页文章,就不能不涉及到法律和制度变革的真实问题。如果有人不同意她的建议——许多女权主义者也不同意这些建议——她的写作所提出的挑战是找到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已经被生动地描述出来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女权主义者对什么是坏事,以及需要什么来使事情变得更好,有不同的看法;但所有的人都同意,妇女的处境往往是不公正的,而法律和政治行动可以使她们的处境更接更加公正。麦金农把等级制度和从属关系描绘成我们整个文化的特有特征,也致力于通过法律——国内的强奸和性骚扰法以及国际人权法——来改变,并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即使是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在《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和性别社会学》(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中译張君玫译,群学,2003)中也对压迫性的性别类别在育儿中的复制进行了令人沮丧的描述,她认为这种情况可以改变。男子和妇女在了解这些习惯的不愉快后果后,可以决定今后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法律和体制的改变可以帮助作出这种决定。
女权主义理论在世界许多地方还是这样的。例如,在印度,学术界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投入到实际的斗争中,女权主义理论化与实际的承诺紧密相连,如女性扫盲、改革不平等的土地法、修改强奸法(在今天的印度,强奸法的大部分缺陷曾为第一代美国女权主义者所贬斥)、努力使性骚扰和家庭暴力问题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些女权主义者知道,她们生活在一个激烈的不公正的现实之中;他们每天在理论写作和研讨室外的活动中,或多或少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与自己共处。
然而,在美国,情况一直在发生变化。人们观察到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趋势。不仅是女权主义理论对美国以外的妇女的斗争关注相对较少。这一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特点,即使是早期许多最好的作品也是如此)。在美国学术界,比排外主义(provincialism)更隐蔽的东西已经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几乎完全从生活的物质方面转向一种口头和象征性的政治,而这种政治与现实妇女的真实情况只有最微弱的联系。
新符号型(或译“象征性”)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们似乎会认为,从事女性主义政治的方法就是在高深晦涩和不屑抽象的学术刊物上,以颠覆性的方式使用文字。人们认为,这些象征性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抵抗的形式;因此,人们不需要参与立法机构和运动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可以大胆行动。此外,新女性主义还指示其成员,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几乎没有空间,也许根本没有空间。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权力结构的囚徒,这些权力结构决定了我们作为女性的身份;我们永远无法大规模地改变这些结构,也永远无法摆脱它们。我们所能希望做的就是在权力结构中找到空间,在其中模仿它们,嘲笑它们,在言语中超越它们。所以,象征性的言语政治,除了被作为一种真正的政治提供之外,还被认为是唯一真正可能的政治。
这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最近的突出表现。许多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无论她们与这位或那位法国思想家的具体关系如何,都受到了极其法国化的思想的影响,即知识分子通过发表煽动性言论来从事政治活动,而这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行动。许多人还从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无论正确与否)衍生出一种宿命论的思想,即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权力结构的囚徒,而现实生活中的改革运动通常最终会以新的、阴险的方式为权力服务。因此,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感到欣慰的是,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可以颠覆性地使用文字。在被剥夺了更大或更持久的变化的希望之后,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重塑语言范畴,从而在边缘地带重塑由这些范畴构成的自我,来进行我们的抵抗。
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比其他任何一位女权主义者都更多地塑造了这些发展。在许多年轻学者看来,朱迪斯·巴特勒似乎定义了现在的女权主义。作为一名哲学家接受培训,她经常被视为(更多的是文学界人士而非哲学家)关于性别、权力和身体的主要思想家。当我们想知道旧式的女权主义政治和它所致力于的物质现实变成了什么样子的时候,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巴特勒的工作和影响,并仔细审视那些导致许多人采取看起来很像安静主义和退缩的立场的论点。
二
要领会巴特勒的想法是很困难的,因为很难弄清楚这些想法是什么。巴特勒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公开讨论中,她证明了自己能说得很清楚,并能迅速掌握对她说的话。然而,她的文字风格却是庞杂而晦涩的。它密密麻麻地引用了其他理论家的典故,取材于各种不同的理论传统。除了福柯,以及最近对弗洛伊德的关注,巴特勒的作品还大量地依赖路易·阿尔都塞、法国女同性恋理论家莫尼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注:颇带情欲色彩的理论家)、美国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性压迫研究)、雅克·拉康、J. L. 奥斯汀和美国语言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逻辑学家)等人的思想。这些人物之间至少可以说并不都是一致的;因此,阅读巴特勒的一个最初的问题是,人们困惑地发现她的论点是通过呼吁这么多相互矛盾的概念和学说来支撑的,通常没有说明如何解决表面上的矛盾。
另一个问题在于巴特勒随意的引用模式(mode of allusion)。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从来没有足够详细的描述,以至于初学者很难入手(如果你不熟悉阿尔都塞的 “互斥 ”概念,你就会迷失几章),也没有向入门者解释,到底是如何理解这些困难的思想的。当然,许多学术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典故性:它预设了对某些学说和立场的事先了解。但在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传统中,面向专家读者的学术作家标准地承认,他们提到的人物是复杂的,是许多不同解释的对象。因此,他们通常承担着在有争议的解释中提出明确的解释的责任,并通过论证来说明为什么他们对这个人物的解释是这样的,以及为什么他们自己的解释比其他人更好。
我们在巴特勒身上找不到这些。不同的解释根本就没有被考虑:即使是在福柯和弗洛伊德的案例中,她提出的是非常有争议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不会被许多学者接受。因此,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写作的全能性不能用通常的方式来解释,即假设有一群专家听众热衷于辩论一个深奥的学术立场的细节。写作实在是太单薄了,无法满足任何这样的受众。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巴特勒的作品并不是针对渴望与实际的不公正现象作斗争的非学术性听众。这样的听众只会被巴特勒散文的浓汤所迷惑,因为其中有着一种“不足与外人 道”的调子,又充满了需要解释的人名。
那么,巴特勒是在对谁说话呢?她似乎是在对学界一群年轻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说话,他们既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不关心阿尔都塞、弗洛伊德和克里普克到底说了些什么,也不是局外人,不需要被告知其项目的性质,并被说服其价值。这种隐含的观众被想象成非常温顺的。这个想象中的读者顺从于巴特勒文本的口令,被其高概念的抽象性所迷惑,很少提出问题,不要求论证,也没有明确的术语定义。
更奇怪的是,隐含的读者预计不会很在意巴特勒自己在许多问题上的最终观点。因为在巴特勒的任何一本书中,很大一部分句子——尤其是接近章节末尾的句子——都是问题。有时,问题所期待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事情往往更不确定。在非问句中,许多句子都以“考虑......”或 “可以建议......”开头——以这样的方式,巴特勒从未完全告诉读者她是否赞同所描述的观点。神秘化以及居高临下的等级策略是她实践的工具,这种神秘化躲避了批评,因为它很少提出明确的主张。
举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主体能动性预设自己的从属关系,这是什么意思?预设的行为是否与恢复的行为是相同的,或者说预设的权力与恢复的权力之间是否存在着不连续性?考虑到,在主体再现自身从属条件的行为中,主体就体现了一种基于时间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属于这些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属于这些条件更新的迫切性(注:语出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 12)
再如:
这样的问题不能在这里得到回答,但它们表明了一个思考的方向,这一方向可能先于良知问题,即斯宾诺莎、尼采,以及最近的乔治·阿甘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作为构成性欲望的存在的欲望?在这样的描述中重新定位良知和质询(interpellation),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再加上另一个问题。这种欲望如何被利用,不仅被单数的法律,而且被各种法律所利用,以至于我们为了保持某种社会 “存在 ”感而屈从?(《性别麻烦》?)
为什么巴特勒喜欢用这种戏谑而令人气愤的方式写作呢?这种风格当然不是史无前例的。大陆哲学传统中的某些前人,虽然肯定不是全部,但有一种不幸的倾向,即把哲学家看作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明星,而且往往是以晦涩令人着迷, 而不是当作在平等的人之间进行论证的人。毕竟,当观念说得很清楚的时候,它可能就容易脱离作者:人们可以把它们带走,自己去追寻它们。当它们保持神秘时(事实上,当它们还没有完全被断言时),人们仍然依赖于阐发这些思想的权威。思想家只因其凝重的魅力而被听从。人们悬着心,渴望着下一步的行动。当巴特勒真的按照那个 “思考的方向”,她会说什么?请告诉我们,一个主体的能动预设自己的从属关系是什么意思?(就我所见,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给人的印象是,此人思想是如此深刻,如此有逻辑,所以TA不会轻率地宣判任何事情:于是人们在对它的深度的敬畏中等待着它最终这样做。
这样一来,晦涩就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光环。它还具有另一个相关的目的。它欺负读者,让他们相信,既然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就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有什么复杂的思想,而实际上往往是一些熟悉的甚至是陈旧的概念,处理得太简单、太随意,不能增加任何新的理解层面。当巴特勒的书被欺负的读者鼓起勇气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这些书中的观念很单薄。当巴特勒的观念被清晰简洁地阐述出来时,人们会发现,如果没有更多的区分和论证,这些观念并没有走远,也没有特别的新意。因此,晦涩填补了缺乏真正复杂的思想和论证所留下的空白。
去年,巴特勒在《哲学与文学》杂志主办的年度烂笔头大赛中,凭借以下一句话获得了一等奖。
从结构主义的论述中,资本被理解为以相对同源的方式结构社会关系,到权力关系受制于重复、收敛和重新衔接的霸权观,将时间性问题带入结构的思考中,标志着从阿尔都塞理论中把结构总体性作为理论对象的形式转变为对结构的偶然可能性的洞察,开创了霸权与权力重新衔接的偶然场所和策略相结合的新概念。
现在,巴特勒可能已经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集中于资本作为构建社会关系的核心力量, 将这种力量的运作描述为到处都是统一的。与此相反,阿尔都塞的论述,侧重于权力,认为这种力量的运作是多变的,是随时间变化的。” 相反,她更喜欢一种冗长的方式,使读者在解读她的散文时耗费大量精力,以至于几乎没有精力去评估这些说法的真实性。在宣布获奖时,该杂志的编辑说:“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写作令人焦虑的晦涩,才让南俄勒冈大学的沃伦——海吉斯教授称赞朱迪斯-巴特勒为‘可能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十个人之一’。” (顺便说一句,这种糟糕的写作,在巴特勒所在的“同性恋理论”理论家群体中,绝非无处不在。例如,大卫·哈尔佩林(David Halperin)写的关于福柯和康德的关系,以及关于希腊同性恋的文章,都具有哲学上的清晰性和历史上的精确性)。
巴特勒因为是哲学家而在文坛上获得了声望;许多崇拜者将她的写作方式与哲学的深刻性联系起来。但人们应该问,它是否本质上属于哲学传统,而不是属于与哲学和修辞学密切相关但又对立的传统。自从苏格拉底把哲学与诡辩家和修辞家的所作所为区分开来之后,哲学就成了一种平等的话语,他们在没有任何蒙昧主义手腕的情况下交换论点和反论点。他声称,这样一来,哲学就表现出对灵魂的尊重,而其他人的操纵方法只表现出不尊重。一天下午,在漫长的飞机旅行中,我被巴特勒弄得疲惫不堪,我翻到了一个学生关于休谟对个人身份的看法的论文草稿。我很快就感到精神振奋。她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我高兴地想,还有点小骄傲。而休谟,多么优秀,多么亲切的精神:他多么善意地尊重读者的智慧,甚至不惜暴露自己的不确定性。
三
巴特勒在1990年的《性别麻烦》中首次提出了她的主要观点,并在她的书中不断重复。她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伪装。我们关于男女的观念并没有反映出任何自然界中永恒存在的东西,相反,它们来自于嵌入社会权力关系的习俗。
当然,这种观念并不新鲜。性别的非自然化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存在了,它得到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极大推动,他在《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中声称,“现在所谓的妇女的本质是一种明显的人为的东西。”密尔看到,关于“妇女本性”(women’s nature)的说法源于权力的等级制度,并支撑着权力的等级制度:凡是能为使妇女受制于人的事业,或者如他所说,“奴役她们的思想”,就会使妇女性成为任何东西。有了家庭就像有了封建主义一样,自然的修辞本身就为奴役的事业服务。“妇女受制于男子是一种普遍的习俗,任何背离它的行为很自然地显得不自然....。但是,有哪一种支配对拥有它的人来说不显得自然吗?”
密尔很难说是第一个社会构造主义者。自古希腊以来,关于愤怒、贪婪、嫉妒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其他突出特征的类似观点在哲学史上已经屡见不鲜。而密尔将人们熟悉的社会建构观念应用于性别,需要而且仍然需要更充分的发展,他的暗示性言论还不等于性别理论。早在巴特勒出现之前,许多女性主义者就为这样的论述做出了贡献。
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和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表的著作中认为,对性别角色的传统理解是确保男性在性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继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方式。他们把密尔洞察力的核心内容带入了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哲学家很少提及的生活领域。不过,这些领域,密尔也不是从来没有提及。1869年,密尔已经明白,不把婚内强奸定为犯罪,就得把女人定义为男性使用的工具,从而否定了她的人格尊严。在巴特勒之前,麦金农和德沃金论述了女权主义对女性的田园式自然性爱的幻想,这种幻想只需要 “解放”即可;并认为社会力量如此之深,我们不应该假设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 "自然 ”概念。在巴特勒之前,他们强调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不仅使女性,而且使那些想选择同性关系的人被边缘化和从属化。他们明白,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一种强制执行熟悉的等级有序的性别角色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一种性别歧视。
在巴特勒之前,心理学家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对性别差异如何跨代复制进行了详细而令人信服的描述:她认为,这些复制机制的普遍性使我们能够理解,人为的东西如何能够近乎普遍地存在。在巴特勒之前,生物学家斯特林(Anne Fausto Sterling)通过对据称支持传统性别区分的自然性的实验工作进行艰苦的批评,表明了社会权力关系对科学家的客观性的损害有多深。性别的神话》(1985年)是她在当时生物学中发现的一个恰当的标题。(其他生物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也为这一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巴特勒之前,政治理论家奥金(Susan Moller Okin,1946-2004,自由女权主义)探讨了法律和政治思想在构建妇女在家庭中的性别命运中的作用;而这一项目也被一些法律和政治哲学领域的女权主义者进一步追求。在巴特勒之前,盖尔·鲁宾对从属关系的重要人类学论述《贩卖妇女》(1975年)对性别的社会组织与权力的不对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宝贵的分析。
那么,巴特勒的工作对这一大量的著作有什么补充呢?《性别麻烦》和《身体之重》(Bodies that Matter)中没有详细论证反对 “自然 ”差异的生物学主张,没有说明性别复制的机制,也没有说明家庭的法律塑造;也没有详细关注法律变革的可能性。那么,巴特勒提供了什么我们可能在早期的女权主义著作中找不到更充分的做法呢?一个相对新颖的主张是,当我们认识到性别区分的人为性,并避免将其视为表达一种独立的自然现实时,我们也会明白,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性别类型本应是两种(与两种生物性相关),而不是三种或五种或无限多种。她写道:“当性别的建构地位被理论化为从根本上独立于性别时,性别本身就成了一种自由浮动的假象”。
巴特勒认为,从这一主张中并不能得出我们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性别的结论。她认为,事实上,我们的自由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她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天真地想象,有一个站在社会背后的纯洁的自我,随时可以出现所有的纯洁和自由。“没有一个自我是在趋同之前的,也没有一个自我在进入这个冲突的文化领域之前保持着‘完整性’。只有在工具所处的地方进行承接,在那里,'承接'本身就是由躺在那里的工具所促成的。”不过,巴特勒确实声称,我们可以通过对旧有范畴的艺术模仿,创造出在某种意义上是新的范畴。因此,她最著名的思想,即她关于政治是一种戏仿表演的概念,是源于一种(严格限制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自于认识到一个人的性别观念是由社会的而非生物的力量所塑造的。我们注定要重复我们出生时的权力结构,但我们至少可以取笑它们;而一些取笑的方式是对原有规范的颠覆性攻击。
性别作为表演的观念是巴特勒最著名的观念,所以值得停下来仔细研究一下。她在《《性别麻烦》中直观地引入了这个概念,而没有援引理论先例。后来她否认自己指的是准戏剧表演,而是把她的概念与奥斯汀在《如何用语言做事》中对语言行为的描述联系起来。奥斯汀的“表演性”语言范畴是一类语言语句,其本身的功能是作为行动而不是作为断言。当(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我说 “我赌十块钱”,或 “对不起”,或 “我愿意”(在结婚仪式上),或 “我给这艘船取名......“我不是在报道一场赌局或道歉,也不是在报道一场婚礼或命名仪式,我是在进行一场。
巴特勒关于性别的类比说法并不明显,因为有关的 “表演 ”(performance,或展演)涉及姿态、服饰、动作和行动,以及语言。奥斯汀的论述仅限于对某一类句子进行相当技术性的分析,其实对巴特勒发展她的思想并没有特别的帮助。事实上,尽管她坚决否定那些将她的观点与戏剧联系在一起的作品解读,但思考 “生活剧场”对性别的颠覆性工作,似乎比思考奥斯汀更能阐明她的想法。
巴特勒对奥斯汀的处理也不是很合理。她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说法,即结婚仪式是奥斯汀文本中几十个表演性例子之一,这一事实表明“社会纽带的异性化是那些带来它们命名的言语行为的范式。”很难说。对奥斯汀来说,婚姻并不比打赌或船名或承诺或道歉更具有典范性。他感兴趣的是某些语句的形式特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们的内容对他的论点有任何意义。从哲学家随意选择出的例 子之中解读出重大的意义,这往往是一个错误。我们是否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用低脂饮食来说明实践的纲要,难道说明鸡肉是亚里士多德美德的核心?或者说罗尔斯用旅行计划来说明实践推理,表明《正义论》的目的是给我们大家放假?
撇开这些怪事不谈,巴特勒的观点大概是这样的:当我们以性别化的方式行事和说话时,我们不是简单地报告世界上已经固定的东西,我们是在积极地构成它、复制它、强化它。通过表现得好像有男性和女性的“本性”,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些本性存在的社会虚构。除了我们的行为之外,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总是在使它们存在。同时,通过以一种稍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模仿的方式来进行这些表演,我们或许可以稍微解除它们的制造。
因此,在一个受等级制度限制的世界里,能动性的一个用武之地,就是在每次性别角色成形时,我们都有小小的机会来反对它们。当我发现自己在做女性化的时候,我可以把它转过来,取笑它,做一点不同的事情。在巴特勒看来,这种被动的、模仿性的表演,从来不会破坏大系统的稳定。她没有设想大规模的抵抗运动或政治改革运动,只有少数知情人演员进行的个人行为。正如拿着烂剧本的演员可以通过把烂台词说得奇形怪状来颠覆剧本一样,性别也是如此:剧本依然是烂的,但演员们却有一丁点的自由。这样,我们就有了巴特勒在《动人的言论》(Excitable Speech)中所说的“一种讽刺性的希望 ”的基础。
至此,巴特勒的论点虽然比较熟悉,但也是可信的,甚至是有趣的,尽管人们已经被她对变革可能性的狭隘眼光所困扰。然而,巴特勒在这些关于性别的似是而非的主张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两种更强烈、更有争议的主张。第一种是,在产生自我的社会力量的背后或之前并不存在代理人。如果这仅仅意味着婴儿出生在一个性别化的世界里,几乎立刻就开始复制男性和女性,那么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但并不奇怪:一段时间以来,实验已经证明,婴儿被抱着和交谈的方式,描述他们情绪的方式,都是由相关成年人认为孩子的性别所深刻塑造的。同样一个婴儿,如果大人认为是男孩,就会被弹跳,如果大人认为是女孩,就会被拥抱;如果大人认为是女孩,它的哭声就会被贴上恐惧的标签,如果大人认为是男孩,就会被贴上愤怒的标签)。巴特勒对这些经验事实没有表现出兴趣,但这些事实确实支持了她的论点。
然而,如果她的意思是说,婴儿进入世界时完全是惰性的,没有任何倾向和能力,这些倾向和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先于他们在性别社会中的经验的,这就不那么可信了,也很难得到经验上的支持。巴特勒没有提供这样的支持,她更愿意停留在形而上学抽象的高层次上。事实上,她最近的弗洛伊德式著作甚至可能否定了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一样,这些研究证明,至少存在一些前社会冲动和倾向,尽管通常情况下,这一界限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发展)。此外,这种对前文化代理的夸大否定,使乔多罗和其他人在试图解释文化变化的方向时,失去了一些资源。
巴特勒最后确实想说,我们有一种能动性,一种承担变革和抵抗的能力。但如果人格中没有任何结构不是彻底的权力创造的,那么这种能动性从何而来?巴特勒不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她肯定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的方式要能说服那些相信人类至少有一些前文化的欲望——对食物、对舒适、对认知的掌握、对生存的欲望——而人格中的这种结构在解释我们作为道德和政治代理人的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希望看到她与这种观点的最强烈的形式接触,并清楚地、不带行话地说出她拒绝这些观点的确切原因和位置。人们还想听她讲讲真实的婴儿,他们确实似乎表现出一种奋斗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影响着他们对文化形式的接受。巴特勒的第二个强烈主张是,身体本身,尤其是两性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种社会构造。她的意思不仅是说,身体在许多方面是由社会规范所塑造的,即男人和女人应该如何;她还说,性别的二元划分被当作是基本的,是安排社会的关键,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观念,而这种观念不是在身体现实中被赋予的。这种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的合理性如何?
巴特勒对福柯关于两性人的简要探讨,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急于将每一个人归入一个或另一个框框中的执着,不管这个个体是否符合一个框框;但这当然不能说明有许多这样不确定的情况。她坚持认为,我们可能对身体类型做了许多不同的分类,不一定把二元划分作为最突出的重点;她还坚持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据称基于科学研究的身体性别差异的说法是文化偏见的投射--虽然巴特勒在这里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几乎没有像福斯·特林(Fausto Sterling,注:布朗大学南希·杜克·刘易斯(Nancy Duke Lewis)生物学和性别研究教授,研究性别认同以及双性人)艰苦的生物学分析那样令人信服。
然而,如果说身体的一切都是权力,那就太简单了。我们要是拥有鸟类、恐龙或狮子的身体,就好了,但我们并没有;这种现实影响了我们的选择。文化可以塑造和重塑我们身体存在的某些方面,但它并不能塑造身体的所有方面。正如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Sextus Empiricus,注:古希腊医生与哲学家,怀疑论者)很久以前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一个被饥饿和口渴所负担的人身上,不可能通过论证产生他没有如此负担的信念。”对于女权主义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妇女的营养需求(以及她们在怀孕或哺乳期的特殊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话题。即使是在性别差异方面,把这一切都写成文化肯定太简单了;女权主义者也不应该急于做出这种一刀切的姿态。例如,那些经营篮球事业或是打篮球的女性会乐于见到体育乃是男性支配的领域这个神话被破除,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她们也会出于很正确的理由要求对女性的身体进行专门研究,从而对女性在训练和伤病上的需要获得更好的理解。简而言之:女权主义需要的,有时也会得到的,是对身体差异和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的微妙研究。而巴特勒的抽象宣告,高高在上地浮于一切物质之上,却没有给我们需要的东西。
IV
假设我们到目前为止同意巴特勒最有趣的主张:性别的社会结构是无处不在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颠覆性和模仿性的行为来抵制它。现在还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应该抵制什么,以什么为基础?抵抗的行为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期望它们能达到什么目的?
巴特勒用了几个词来形容她所认为的不好的、因而值得抵制的东西:“压抑的”(repressive)、“从众的”(subordinating)、“压迫的”(oppressive)。但她没有提供关于抵抗的经验性讨论,比如说,我们在巴里·亚当(Barry Adam)的引人入胜的社会学研究《支配的延续》(The Survival of Domination,1978年)中发现,该书研究了黑人、犹太人、妇女和男女同性恋者的从属地位,以及他们与压迫他们的社会权力形式进行搏斗的方式。巴特勒也没有对抵抗和压迫的概念进行任何说明,如果我们真的对我们应该抵抗的东西有疑问,我们也无法从巴特勒那里找到有用的抵抗和压迫的概念。
巴特勒在这方面背离了早期的社会建构主义女权主义者,这些女权主义者都用反等级、平等、尊严、自主、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等观念,来为实际的政治指明方向。而巴特勒更不愿意阐述任何积极的规范观念。事实上,巴特勒显然和福柯一样,坚决反对人的尊严或把人性作为目的等规范性概念,理由是这些概念本质上是独裁的。在她看来,我们应该等着看政治斗争本身所抛出的东西,而不是事先给参与者规定。她说,普遍的规范性观念 “在同一的标志下殖民化”。
这种等着看我们得到什么的想法——一言以蔽之,是一种道德上的被动——在巴特勒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她默默地假设了一个志同道合的读者群,他们同意(算是)什么是坏事:歧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对于妇女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对待;这样的受众甚至会同意为什么这些事情是坏的:它 们使一些人从属于另一些人,它们拒绝赋予人应有的自由。但是,把这个假设去掉,规范性层面的缺失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试着在当代法学院里讲授福柯,就像我一样,你很快就会发现,颠覆有很多形式,并不是所有的形式都是巴特勒和她的盟友们所喜闻乐见的。就像一个敏锐的自由主义学生对我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不能用这些思想来抵制税收结构,或者反歧视法,甚至可能加入民兵组织?还有一些不太喜欢自由的人,可能会进行颠覆性的表演,比如在课堂上取笑女权主义的言论,或者撕掉法律系女同性恋学生会的海报。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它们是模仿和颠覆性的。那么,为什么它们不大胆、不美好呢?
嗯,这些问题有很好的答案,但你不会在福柯,或者巴特勒那里找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讨论人类应该拥有哪些自由和机会,以及社会机构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社会正义和人类尊严的规范理论。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普遍性规范保持谦逊,并愿意从被压迫者的经验中学习是一回事。说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规范是另一回事。福柯与巴特勒不同,他至少在晚期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迹象;而他的所有写作都是由对社会压迫的质地及其危害的激烈意识所激发的。
仔细想想,被理解为个人美德的正义,恰恰具有巴特勒分析中的性别结构:它不是天生的或“自然”,它是通过反复的表演产生的(或者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我们通过做它来学习它),它塑造了我们的倾向,并迫使我们压抑其中的一些倾向。这些仪式性的表演,以及与之相关的压抑,都是由社会权力的安排所强制执行的,正如那些在操场上不愿分享场地的孩子们一样。此外,对正义的嘲讽性颠覆在政治中无处不在,在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这些颠覆性的表演,我们认为应该极力劝阻年轻人不要用这种玩世不恭的眼光看待正义的规范。巴特勒无法用任何纯粹的结构性或程序性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对性别规范的颠覆是一种社会善,而对正义规范的颠覆是一种社会恶。我们应该记得,福柯曾为阿亚图拉(Ayatollah)欢呼过,为什么不呢?那也是一种抵抗,文中确实没有任何内容告诉我们,这种斗争的价值不如争取民权和公民自由的斗争。
那么,巴特勒的政治概念的核心是一个空白。这个空虚看起来可以是自由的,因为读者用一种关于人类平等或尊严的规范性理论隐晦地填补了它。但不要搞错了:对巴特勒来说,就像对福柯一样,颠覆就是颠覆,原则上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发展。事实上,巴特勒天真空洞的政治对于她所珍视的事业来说尤其危险。巴特勒的每一个朋友,热衷于从事宣扬异性性别规范的压抑性的颠覆性表演,就有几十个人愿意从事藐视遵纪守法纳税、不歧视、体面对待同学的规范的颠覆性表演。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说,你不能简单地随心所欲地反抗,因为有公平、体面、尊严的规范,就意味着这是不好的行为。但是,我们就必须把这些规范表达出来——而这一点巴特勒拒绝做到。
V
当巴特勒建议颠覆时,她到底提供了什么?她告诉我们要进行模仿性的表演,但她警告我们,完全逃离压迫结构的梦想只是一个梦想:正是在压迫结构中,我们必须找到小小的反抗空间,而这种反抗不能指望改变整体形势。而这里就有一种危险的寂静主义(quietism,注:路易十四时期的宗教信仰派系)。
如果巴特勒的意思只是警告我们不要幻想一个田园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性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她这样做是明智的。然而,她经常走得更远。她提出,确保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在我们的社会中被边缘化,以及女性持续不平等的制度结构,永远不会有深层次的改变;因此我们最好的希望是对它们嗤之以鼻,并在其中找到个人自由的口袋。“被一个伤害性的名字所召唤,我来到社会存在中,由于我对我的存在有某种不可避免的依恋,由于某种自恋把持着任何赋予存在的术语,我被引导去接受那些伤害我的术语,因为它们构成了我的社会性。”换句话说。我无法在不停止存在的情况下 摆脱这些羞辱性的结构 所以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嘲弄,并刺耳地使用从属的语言。在巴特勒那里,反抗总是被想象成个人的、或多或少的私人行为,不涉及任何非铁的、有组织的公共行动来进行法律或制度上的改变。
这不就像对一个奴隶说,奴隶制的制度永远不会改变,但你可以找到嘲笑它、颠覆它的方法,在这些小心翼翼的有限反抗行为中找到你的个人自由吗?然而事实是,奴隶制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曾经改变过:但不是被那些对可能性采取巴特勒式观点的人所改变的。它之所以被改变,是因为人们并不满足于模仿性的表演:他们要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得到了社会的动荡。塑造妇女生活的制度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一个事实。强奸法虽然仍有缺陷,但至少有了改进;性骚扰法存在,以前没有的地方也有了;婚姻不再被认为是让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君主式的控制。这些事情都是由女权主义者改变的,她们不会把模仿性的表演当作自己的答案,她们认为权力在哪里不好,就应该、也会在正义面前屈服。
巴特勒不仅摒弃了这样的希望,她还以其不可能为乐。她发现,思考所谓的权力的不可移动性(immovability of power),以及设想对奴隶的仪式性颠覆,她确信自己必须保持这样的状态,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她告诉我们——这是《权力的心理生活》的中心论点——我们都将压迫我们的权力结构色情化,因此只能在其范围内找到性快感。似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更喜欢模仿颠覆的性感行为,而不是任何持久的物质或制度变革。真正的改变会使我们的心理被连根拔起,以至于无法获得性满足。我们的性欲是坏的奴役力量所创造的,因此在结构上必然是受虐狂的。
好吧,当你是一所自由大学里有权势的终身制学者时,模仿性的表现也不至于太差。但在这里,巴特勒对象征性的关注,她对生活中物质层面的骄傲忽视,就成了致命的盲目。对于那些饥饿、文盲、被剥夺权利、被殴打、被强奸的女性来说,无论多么戏谑地重演饥饿、文盲、被剥夺权利、被殴打、被强奸的状况,都不是性感或自由的。这样的女性更喜欢食物、学校、选票和身体的完整性。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相信她们会虐待狂地渴望回到糟糕的状态。如果有些人不能没有支配的性爱,那似乎是可悲的,但这其实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当一个主要的理论家告诉处于绝望状态的女性,生活为她们提供的只有束缚,她传递的是一个残酷的谎言,而且是一个奉承邪恶的谎言,因为她给了邪恶比它实际拥有的更多的力量。
《动人的言论》是巴特勒最近的一本书,书中提供了她对涉及色情和仇恨言论的法律争议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寂静主义到底延伸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她现在愿意说,即使在法律变革是可能的地方,即使在它已经发生的地方,我们也应该希望它消失,以便保留被压迫者可以实施他们的虐待狂式的模仿仪式的空间。
作为一本关于言论自由法的著作,《动人的言论》是一本不合情理的烂书。巴特勒没有表现出对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理论论述的认识,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理论需要考虑到的广泛案例。她提出了荒谬的法律主张:例如,她说,唯一被认为不受保护的言论类型是以前被定义为行为而非言论的言论。事实上,有许多类型的言论,从虚假或误导性广告到诽谤性声明,再到目前所定义的淫秽行为,这些言论从未被宣称为行为而非言论,然而它们却被剥夺了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巴特勒甚至错误地宣称,淫秽已经被判定为等同于“斗嘴”(或译“骂街”)。巴特勒并不是说她对第一修正案需要涵盖的不受保护的言论的广泛案例的新颖解读有论据支持。她只是没有注意到有这种广泛的案例,或者说她的观点并不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法律观点。对法律感兴趣的人都无法认真对待她的论点。
但是,让我们从巴特勒对仇恨言论和色情的单薄论述中,提取出她立场的核心内容。这就是:对仇恨言论和色情的法律禁止是有问题的(尽管最后她并没有明确反对),因为它们关闭了被该言论伤害的当事人可以进行反抗的空间。巴特勒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通过法律制度来处理违法行为,那么非正式抗议的场合就会减少;另外,也许,如果违法行为因为其非法性而变得更加罕见,我们抗议其存在的机会就会减少。
嗯,是的。法律确实会封闭这些空间。仇恨言论和色情制品是极其复杂的话题,女权主义者可能会在这上面有合理的分歧。(不过,人们还是应该准确地说明争论的观点)。巴特勒对麦金农支的描述不够谨慎,她说麦金农支支持“反对色情的法令”,并暗示,尽管麦金农支明确否认,但他们涉及一种审查制度。巴特勒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麦金农实际上支持的是一种民事损害赔偿诉讼,在这种诉讼中,通过色情制品受到伤害的特定妇女可以起诉其制作者和传播者)。
巴特勒的论点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仇恨言论和色情制品的案例。它似乎不仅支持这些领域的寂静主义,而且支持一种更普遍的法律寂静主义,或者说,事实上,支持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它是这样说的:让我们取消从建筑法规、不歧视法到强奸法的一切规定,因为它们封闭了受伤的房客、歧视的受害者、被强奸的妇女可以进行反抗的空间。现在,这与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用来反对建筑规范和反歧视法的论点不同,甚至他们也把界线划在了强奸法上。但结论是趋同的。
如果巴特勒应该回答说,她的论点只与言论有关(鉴于有害言论与行为的同化,文中没有给出这种限制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在言论领域进行回答。让我们摆脱反对虚假广告和无证医疗咨询的法律,因为它们封闭了中毒的消费者和被残害的病人可以进行抵抗的空间!我们可以在言论领域中回答。同样,如果巴特勒不赞同这些延伸,她需要提出一个论点,将她的案件与这些案件划分开来,而她的立场是否允许她做出这样的区分并不清楚。
对巴特勒来说,颠覆的行为是如此的铆足了劲,如此的性感,以至于认为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好,这简直是一个糟糕的梦。平等是多么无聊啊!没有束缚,没有快乐。这样一来,她的悲观主义情色人类学就为一种非道德的无政府主义政治提供了支持。
VI
当我们考虑到巴特勒写作中固有的寂静主义时,我们就有了一些关键来理解巴特勒对变装和变装作为女权主义抵抗范式的影响力。巴特勒的追随者理解她对变装的描述,暗示这种表演是女性大胆和颠覆的方式。我不知道巴特勒是否试图否定这种解读。
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穿男人服的女人几乎不是一个新形象。事实上,即便在19世纪当这类现象还相对比较新鲜的时候,其中也还还是有一些旧因素,因为这不过是重复了女同性恋世界中既有的刻板套式和男 - 女社会中的高低等级。我们很可能会问,在这个领域里,什么是模仿颠覆,扮装之中的等级不还是等级吗? 难道支配和从属当真是女性在所有领域中都要扮演的角色, 难道不是从属就只能是男性化的支配?(《权力的心理生活》似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简而言之,女性异装是一个老掉牙的剧本——正如巴特勒自己告诉我们的那样。然而,她希望我们把这个剧本看成是被颠覆了,被变装者明知故问的象征性的风度姿态弄得焕然一新;但我们又必须怀疑这种新,甚至是颠覆性。考虑到安德烈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对一个巴特勒式的模仿性女权主义者的模仿(在她的小说《怜悯》中),这个人物这样说道:
认为坏事要发生,这个想法既是故意让人吃惊,而且也是不恰当的....要理解一个女人的生活,就需要我们肯定那些隐藏的或晦涩的层面,比如快乐常常是在痛苦中;选择常常是在胁迫下。人们必须培养出一双发现秘密迹象的眼睛--比如说,在当代的对话中,那些不仅仅是衣服或装饰的衣服,或者隐藏在明显的顺从背后的反叛。没有受害者。也许是一种迹象的不足,一种顺从的顽固表象,只是掩盖了选择发生的更深层次。
这段话用与巴特勒完全不同的散文,抓住了巴特勒一些著作中隐含的作者的矛盾心理,她一方面乐于自己的暴力实践,另一方面又坚决地把理论的眼光转向饥饿、文盲、被暴力、被殴打的妇女的物质痛苦。没有受害者。只有迹象的不足。
巴特勒向她的读者暗示,这种对现状的狡猾寄托是生活提供的唯一的抵抗脚本。但不是的。除了在个人生活中提供了许多其他做人的方式,超越了传统的支配和服从的规范,生活还提供了许多抵抗的脚本,这些脚本并不自恋地专注于个人的自我展示。这种脚本涉及到女权主义者(当然还有其他人)建立法律和制度,而不太关心女性如何展示自己的身体及其性别化的本质:简而言之,它们涉及到为其他受苦的人工作。
美国新女权主义理论中最大的悲剧是公共承诺/公共担当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巴特勒的自我参与型女权主义极富美国特色,它在这里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这里,成功的中产阶级更愿意注重培养自我,而不是以帮助他人物质条件的方式来思考。然而,即使在美国,理论家也有可能致力于公益事业,并通过这种努力有所成就。
在美国,许多女权主义者仍在以支持物质变革的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并对最受压迫者的处境作出反应。然而,学术和文化的趋势越来越倾向于以巴特勒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化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调侃。巴特勒式的女性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比旧式的女性主义容易。它告诉数十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性,她们不需要致力于改变法律,不需要为饥饿者提供食物,也不需要通过驾驭物质政治的理论来抨击权力。她们可以在安全的校园里做政治,停留在符号层面,通过言语和姿态对权力做出颠覆性的姿态。理论上说,反正这几乎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所有政治行动方式,是不是很刺激,很性感?
当然,从其小的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政治。它指示人们现在可以在不危及安全的情况下,做一些大胆的事情。但这种大胆完全是一种姿态,就巴特勒的理想表明这些象征性的姿态真的是政治变革而言,它提供的只是一种虚假的希望。饥饿的妇女没有因此而得到温饱,受虐的妇女没有因此而得到庇护,被强奸的妇女没有因此而找到正义,同性恋者没有因此而得到法律保护。
最后在欢快的巴特勒事业的核心是绝望。一个伟大的希望,希望一个真正正义的世界,法律和制度保护所有公民的平等和尊严,但这个希望已经被放逐,甚至可能被嘲笑为性乏味。朱迪斯·巴特勒的时髦寂静主义是对美国实现正义的困难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回应。但这是一种糟糕的回应。它与邪恶合作。女权主义要求更多,女性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反驳努斯鲍姆以及努斯鲍姆回应(为阅读方便,将原文中的回应文字拆开,分别放入每段反驳文字之后)
Warren Hedges(南俄勒冈大学,Assistant Professor of English)
在最近一期中,作为面对既晦涩难懂而容易让人轻信之行文的一个例子,努斯鲍姆拿出了一段二手引文,据说我在这段引文中认为朱迪斯·巴特勒:“可能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十个人之一”。
如果努斯鲍姆核实了这段引文,而不是仅仅引证,她就会找到一个文学理论网站,介绍 "大普巴:通常叫雅克,但也有海伦,卢斯,米歇尔,偶尔弗雷德”( The Grand PoohBahs: Often Named Jacques, but also Helene, Luce, Michel, and occasionally Fred)(其中也有米歇尔-福柯的头贴在Pez饮水机上)。原话是这样说的“巴特勒的思想足够复杂,人们通常会以卡通的方式将其简化。要想以深刻的方式参与到她的工作中,就必须了解一系列令人生畏的困难思想家....。可能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十个人之一,该死的她--他钦佩地说--她才34岁。”这就是所谓的讽刺。欢迎有眼光的读者和我一起讨论。
毫无疑问,有理论头脑的学者常常以无端的不耐烦来驳回反对意见。但当自诩为清晰的捍卫者不愿意做我们对任何一年级作文学生所要求的基本研究时,也许这种不耐烦是有道理的。有关巴特勒(以及现在的努斯鲍姆)的原始、营建性讨论,请访问。
http://www.sou.edu/English/IDTC/Swirl/swirl.htm.
努斯鲍姆回应
赫奇斯的信表明,我正确地引用了他的话。他这句话的大背景表明,它可能是夸张的;没有迹象表明它是讽刺的。也许赫奇斯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斯皮瓦克(哥伦比亚大学)(注:猛烈回应,你丫也是精英主义说到底)
努斯鲍姆在她最近对朱迪斯·巴特勒作品的评论中,抱怨说,像巴特勒这样的女权主义者 “从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可以颠覆性地使用文字的想法中找到安慰"。而与巴特勒的文章相比,努斯鲍姆自己的文章却更好地体现了这种想法。
努斯鲍姆认为,社会建构理论(social-construction theories)与把性别视为一种表演性的分析(gender as performative),没有区别。。而她不会允许巴特勒自由地将奥斯汀的表演性(Austinian performative)扩展到一个比言语更重要的范畴。她既然如此责备巴特勒不切实际,就应该估计到社会建构的性别理论从柏拉图开始就存在,而这种建构理论与从思想上指出我们都是通过实践使性别产生的,不太一样。巴特勒的表演理论与奥斯汀的表演理论不一样,与社会建构理论也不一样。她要解决的是使用中的惯习(convention)、社会契约效应、难以捉摸的物质性的集体“制度”(institutions)、政治的根基。不与惯习纠缠在一起,任何法律或政治改革都没有生存的机会。
作为一个居住在美国的印度女权理论家和活动家,并有幸与Flavia Agnes、Farida Akhter、Mahasweta Devi、Madhu Kishwar、Rajeswari Sunder Rajan、Romila Thapar、Susie Tharu等次大陆女权活动家,还有其他许多人结为友好,我拒绝了努斯鲍姆以 “在今天的印度,强奸法的大部分缺陷曾为第一代美国女权主义者所贬斥” 这种隐晦的婆婆妈妈的提法,她以印度女权主义者为开场白,作为批评巴特勒不是的例子。(比如,我们如何对待Anupama Rao(注:哥伦比亚大学女性史家)在Understanding Sirsgaon: Notes Toward Conceptualising the Role of Law, Caste and Gender in a Case of ‘Atrocity一文中中对巴特勒的认真思考。印度女权主义理论家使用巴特勒的例子可以举不胜举)。)
这种为贫困妇女摇旗呐喊的拥护,使努斯鲍姆最后断言:“那些饥饿、文盲、被剥夺权利、被殴打、被强奸的妇女......更喜欢食物、学校、选票和身体的完整性“。听起来不错,从一个自由派大学的有权势的终身教授口中说出。但她是怎么知道的?这可能是她的想法,她觉得他们应该想要什么。在这种信念下,她可能想训练他们要这个。这就是所谓的 “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这个概念是庶民研究的核心)。但是,如果她曾经在全球南方从事过无中介的草根行动主义,而不是拥护行动主义理论家,她会发现,农村穷人的性别实践相当多的时候是在表演模式下,在一个更普遍的乐于服从的场景中刻画权力。如果她想否定这种性别文化的普遍性,并以自己的形象让妇女们过关,她就必须进入她们的协议,并学会比这篇恶毒的评论所表现出的更大的耐心和理解。
努斯鲍姆总结道:“巴特勒的时髦安静主义......与邪恶合作。”任何对反全球化的参与都会显示出她那种针对“他者女性”(other women)的仁慈是同样未经审视的、同样时髦,而且也是同剥削合作。解决办法,如果有的话,就是不要在国家期刊的版面上进行辱骂性的评论。
努斯鲍姆回应
斯皮瓦克说我把社会建构理论等同于性别是表演性的论题是错误的。我说,后者虽然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但却是巴特勒的一个有趣的新贡献。当然,巴特勒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展奥斯汀的观点,但我的说法是,奥斯汀的观点,无论如何她都歪曲了,对她所追求的项目没有多大帮助。
我很佩服斯皮瓦克在部落妇女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当我写到印度的女权主义者,不管她们的知识取向如何,仍然是贴近实际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点。但她在做出假设之前,应该先打听一下我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印度的活动家和妇女发展项目接触。我参观了不同地区的许多不同类型的项目。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贫穷的妇女告诉我她以服从为乐,尽管可能有一些人这样做。我见过无数的妇女,她们为获得信贷、教育、就业机会、政治代表权和躲避家庭暴力而奋斗。
我关于印度强奸法的说法是正确的:例如,受害者的性史仍然是相关证据。我认为,让美国读者了解像英迪拉·杰辛这样的活动家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出色工作,并没有什么 "婆婆妈妈 "的意思,我很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启发。在我即将出版的《妇女与人类发展》一书中,我对印度妇女的主张有充分的记录,这在简短的评论中是不可能的。
Seyla Benhabib(哈佛大学,土耳其裔)
Nancy Fraser(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Linda J. Nicholson(纽约州立)(注:赞同,但否认辱骂)
我们对Martha C. Nussbaum在《新共和》上对Judith Butler的攻击感到不安。
我们认为特别令人反感的一点是,努斯鲍姆一再试图把巴特勒当作哲学家来看待。努斯鲍姆一度声称,巴特勒被 “更多的文学界人士而不是哲学家 ”视为主要思想家。她问巴特勒的写作方式 “是否根本属于哲学传统。”作为一个在拉近文学和哲学距离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的人,努斯鲍姆对巴特勒的尝试的质疑是不真实的。此外,努斯鲍姆的举动还让人想起那些试图将女权主义关切排除在哲学之外的人,理由是 “这根本不是哲学。
虽然努斯鲍姆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文章中的辱骂因素令人不安。巴特勒的贡献不仅被描述为“无意识地做了坏事,”而且努斯鲍姆声称从这些贡献中得出的安静主义被说成是“与邪恶合作。”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辞与努斯鲍姆对凯瑟琳·麦金农和安德里亚·德沃金的毫不怀疑的崇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鉴于麦金农和德沃金政治中的专制主义倾向,巴特勒强烈的反专制主义是一剂有益的解药。
努斯鲍姆回应
本哈比布、弗雷泽和尼科尔森说,我说巴特勒更像是诡辩家而不是哲学家的说法是“虚伪的”,因为我曾写道,哲学可以从文学中获得洞察力。如果提供一个默许的前提,即诡辩是文学,或者说巴特勒是一个可以与普鲁斯特和亨利-詹姆斯相提并论的人物,那么这种奇怪的非续集也许是成立的。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接受这两个假设。我所说的 "不合情理的坏事 "不是指巴特勒的一般作品,而是指她在《动人的言论》中使用第一修正案的法律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是恰当的。最后,读过我所写的关于麦金农和德沃金的文章的人都会知道,我对他们的态度不是“毫不怀疑的崇拜”,而是深深的尊重批评。
Joan Scott(普林斯顿)(注:批评努斯鲍姆批评背后摩尼教式方案,善与恶)
努斯鲍姆对朱迪思·巴特勒的评述,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前提,即检验一种理论是否良好的标准是其积极的政治结果。然而,我们并没有为这一主张提供任何经验证据。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摩尼教式的方案,它把“好”的理论定义为 “与实际承诺紧密相连”、与 “真正的”问题、与 “真正的妇女的真实情况”、与 “真正的政治”和 “真正的正义”紧密相连的理论。与努斯鲍姆的论辩无关的是,朱迪斯·巴特勒在言行上被视为一个对“真正的政治”有“实际承诺”的政治关注者,而且她的著作影响了连努斯鲍姆都认为是“好的”政治的同性恋活动家、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和从事妇女权利工作的律师。按照这个论点的逻辑,既然巴特勒不认同努斯鲍姆的“社会正义和人类尊严的规范理论”,那么巴特勒只能“与恶合作”。努斯鲍姆打着严肃书评的幌子,构建了一个自私自利的道德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她(与凯瑟琳·麦金农和安德里亚·德沃金一起)代表了历史上真实的、政治上有效的女权主义,而朱迪斯·巴特勒(以及据说追随她的那些年轻的、弗朗索瓦式的、萨多玛斯主义的爪牙)则沉溺于“非道德的无政府主义政治”或“时髦的安静主义”,因此背叛了女权主义的目标。
努斯鲍姆在她的文章中方便地轻而易举地省略了所有关于“真正”政治的实例的讨论,也许是因为证据对她的论点如此不利。像努斯鲍姆那样从理论中推导出政治,是对两者的运作的误解。理论的工作是开辟新的理解途径,用困难的问题来困扰传统智慧。政治的工作(至少在民主社会中)是在一个有争议、有冲突的领域中确保某种目的。政治和理论可能在某些时刻相互通报,结果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结果是无法预测的。但从历史上看,有一点是肯定的:当理论和政治之间的差距以美德的名义被关闭时,当罗伯斯庇尔或阿亚图拉(Ayatollahs,注:什叶派宗教学者等级)或肯·斯塔尔(Ken Starr,注:前美国副检察总长,曾主持弹劾克林顿案)试图将他们的“善”,曾的愿景强加给社会的其他成员时,恐怖统治随之而来,民主政治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用努斯鲍姆的推理来说,太多的“善”最终会变成“恶”,而女权主义与所有其他解放运动一样,失去了它的公共发言权。
可悲的是,努斯鲍姆的善与恶的计划取代了道德主义原教旨主义,取代了女权主义者之间真正的哲学和政治辩论--如今有很多东西需要辩论。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吗?谁能为“女性”的需求和利益说话?政治行动如何解决关于性别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朱迪斯·巴特勒以极大的诚意和技巧参与了这些问题。我们这些人在寻找反思当今女权主义状况的方法,可以理解,他们更喜欢朱迪斯·巴特勒的挑衅性、开放性理论,而不是努斯鲍姆的封闭式道德化。
努斯鲍姆回应
斯科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区别。我说的不是理论家所追求的实践活动,而是理论化的方式给实际的政治努力指明了方向。巴特勒很可能有令人钦佩的实践承诺,但这并不能改变她作为理论家所写的东西没有为实践提供任何有益的方向的事实。我讨论了许多确实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的理论化的例子,包括关于强奸法改革、性骚扰法以及更普遍的性别平等概念的著作。我也不认为阿亚图拉和罗伯斯庇尔的吓人名字如何破坏了那些帮助法律改革取得进展的女权主义者的工作价值。
Drucilla Cornell(罗格斯大学)
Sara Murphy(纽约大学)(注:批评努斯鲍姆简单化的区分)
女权主义理论家现在是否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即行动派和“臀部失败派”(“hip defeatists”)?虽然玛努斯鲍姆提出了一些关于女权主义理论与世界各地妇女为获得对其尊严的承认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之间的关系的严肃问题,但她将那些“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s)的女权主义者与那些 “新符号型”(new symbolic type)的女权主义者二分法,后者“认为从事女权主义政治的方式是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在高高在上的晦涩和不屑一顾的抽象的学术出版物中使用文字”,这不仅是简单化的,而且掩盖了第二波女权主义对表象在塑造我们的现实中的作用的关键关注。我们认为,包括朱迪斯·巴特勒在内的任何一位女权主义者都不认为女权主义的政治目标可以通过努斯鲍姆归结为这种“新符号型”的方式来实现。但各路女权主义者——以及本世纪下半叶的许多其他群体——早已看到,我们如何代表自己和被他人代表的问题是追求正义的核心。在她的文章中,努斯鲍姆将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作为“好的”行动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典范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为 "坏的 "语言导向女权主义者的缩影进行了对比。然而,对麦金农和巴特勒来说,女权主义的工作都建立在对语言和视觉等表象的物质力量的坚持上。凯瑟琳-麦金农和其他反色情女权主义者告诉我们,色情图像和文字残害了作为女性的我们,抵制压迫意味着要从这些表象中寻找出路。
朱迪思·巴特勒的作品,包括她对身份认同的表演性方面的著名见解,同样关注表征具有构成性力量的方式,即我们是谁与我们被表征的方式深深相连。但麦金农对表征的物质性的关注转向了法律改革,包括与安德烈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共同撰写的创新民权条例(innovative civil rights ordinance),而巴特勒则认为,关于表征的斗争应该在政治上进行。
这是他们之间的真正区别,需要解决。包括作者之一在内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多年来一直在寻求解决这个法律改革的参数问题,以及通过政治进行变革的可能性。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历史上一直困扰分析法学的问题。我们如何在权利概念中协调自由和平等?
鉴于这两位理论家工作的利害关系和严肃性,以及他们的工作和其他许多人的工作所要解决的复杂性,努斯鲍姆将理论家简单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不仅不准确,而且也没有什么成效。读她的文章,其实不过是对巴特勒的广告攻击,人们确实会想起——如果说是讽刺的话,如果说是悖论的话——大卫·休谟,努斯鲍姆准确地将他描述为 “一个优秀的......一种亲切的精神:他多么善意地尊重读者的智慧,甚至不惜暴露自己的不确定性”。但愿努斯鲍姆在自己对朱迪斯·巴特勒作品的评论中,能尊重休谟的哲学精神。
努斯鲍姆回应
康奈尔和墨菲写了一封有趣的信,涉及到我实际论证的实质。他们指出,麦金农的思想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一点是正确的。麦金农和福柯之间的差异值得细细研究。我希望他们能写出这样的研究报告。我远没有把思想家分为两个阵营,我明确表示,我尊重福柯-符号传统的一些工作,包括福柯本人的工作。在我看来,巴特勒并不是一个相同水准的思想家。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