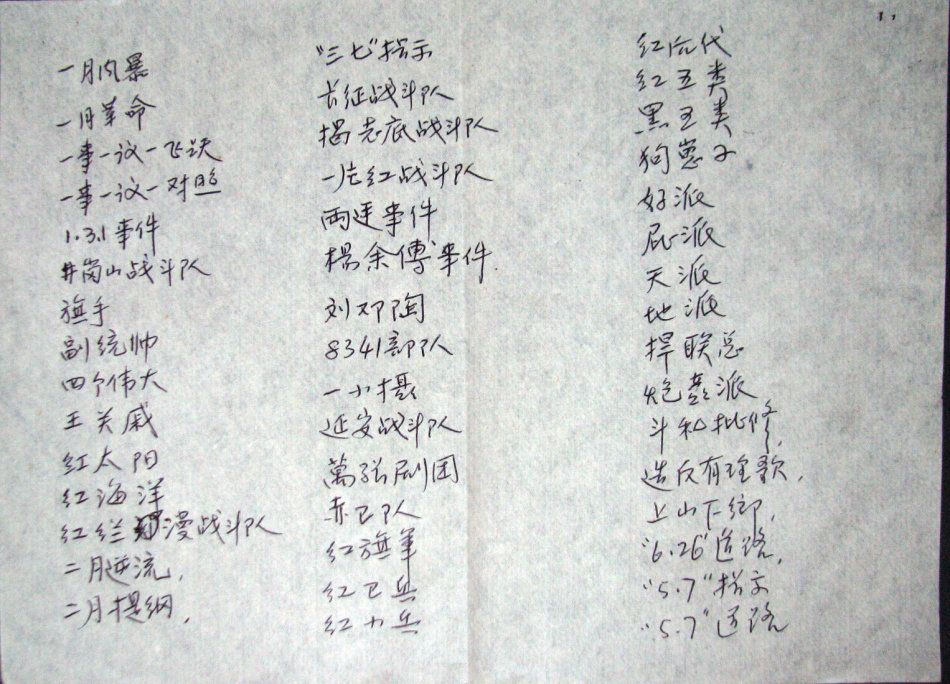
对49年以后中国历史感兴趣,鉴于中文互联网有关的记忆和记载正在被大规模地有计划地移除,本博主要用作收集网络“垃圾”,“拯救”网络记忆和记载,可能偶尔会有点原创,稍微会转一点资料性强创见多的不被主流刊载的学术性文章。另外,凡华夏文摘刊登过的文章一般不cross post,当然也会有例外,视情况而定。
夏其言:"文革"十年琐忆
"文革"十年琐忆
《解放日报》是十年浩劫的"文革"重灾区之一。人们都说"文革"是一场可怕的大恶梦,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可是人们记忆犹新。前不久,同几位老同志闲谈中,谈到现在好多年轻人竟听不懂"斗批改"、"触灵魂"等等"文革"流行语,更不知道十年"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都不胜感慨。我说,作为十年浩劫的受害人,写一点关于十年"文革"的回忆,让年轻一代对这暗无天日的十年也有所了解,似乎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大家说,非但很有意义,而且也很有必要。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决定撰写这篇"琐忆"。
问题是我们这些当年的"牛鬼蛇神"被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不许乱说乱动,连大字报也不准许看,因此对于报社'文革"期间的全面情况,很难了解,也不敢去主动了解。这里回忆、记述的,仅仅是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一些事实。不过,虽属个人经历,从中也不难看出当年造反派在报社横行不法、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种种罪恶行径。
回忆这漫长的十年岁月,终生难忘的受迫害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这里只能就印象较深的,按时间先后,简要地记述几件具体事例而已。
在报社
"文革"开始时,我在解放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是最早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之一,除被不断批斗、陪斗之外,就是每天早早来到报社,在上班之前打扫厕所。
作为"牛鬼蛇神",我有六项"帽子"--老反革命、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人物、叛徒、特务、假党员、死不改侮的走资派。本市和外地好几个造反组织进驻报社后,我的办公室也被强占了,无处落脚,只得缩在走廊角落里,或坐在楼梯口。由于全报社各部门--编辑部各部组、经理部各科室、工厂部各车间日夜都有人工作,因此连日连夜24小时都有人轮流来揪我去批斗。当时我已50多岁,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有次实在太疲劳了,坐在三楼楼梯口稍事休息,坐下不久,便打盹入睡了。突然,感到头颈奇痛,原来是被皮鞋脚踢痛的,一看,编辑部的两个造反"战士"气势汹汹地又来揪斗了,大声喝叱:"还有胃口打呼!快走,快走!"我心里想,正因为自己不是"反革命"才会打呼,说明我心中无"鬼"嘛!我当即被押着去三楼会议室批斗,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还未结束,经理部某科室又有人等着来揪我了。
抄家是"文革"中造反派对"牛鬼蛇神"例行的斗争手段之一。我既然被戴上"老反革命"的帽子,当然也就在劫难逃。先后两次,第一次从写字台、书橱、五斗橱、所有的抽屉等等,抄去所有的采访本子、通讯录、笔记本、全部信件(包括好几个国家新闻界同行的贺年信),以及一些稿件的草稿留底等等。他们临走时我要求给个收据,他们根本不理,拿着大包小包头也不回就走了。第二次来抄家,一进门就恶狠狠地把我赶在一边站着,看他们翻箱倒箧,连衣橱、壁橱,甚至我老伴的皮包也不放过。房间里乱七八糟,狼藉满地。这次抄去的,有照片一大叠,特别是其中的一张是1965年周总理在上海接见由陈丕显同志直接领导的、包括丁柯、杨瑛和我在内的城市"四清"试点(在综合仪器厂)的工作队,接见时总理与我们一一握手,并拍照留念。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我特别珍贵。此外,除我与同志、朋友、亲戚的合影以及家庭生活的照片之外,连我当话剧演员的小女儿的舞台剧照和某时装公司请她试穿新设计的时装样品时替她拍摄的好多张照片,也全部抄去。更荒唐的是把我老伴5O年代的人党报告底稿和其它不少同我本人毫不相干的材料也统统拿走。尽管他们不出收据,但我对这两次抄家印象极深,记忆犹新。"四人帮"垮台后我曾向原造反派头头提出,抄家抄去的该全部发还给我了。他们先是说,等他们找出来就还给我,但一拖再拖,最后竟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找不到,遗失了!"我当然很着急,也很气愤,但有什么办法呢?!
由于我是解放前就在上海念书、工作的,是旧社会过来的,同学、同事、同志,社会关系比较多,因此"文革"中前来报社向我外调的也特别频繁,几乎每天都有,有时一天两三批。因为我戴的是"老反革命"帽子,报社造反派还要派人陪同"审问"。而且不称外调,而叫"勒令交代"。更有甚者,来者几乎都是带着事先定好的框框来的。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原上海江苏银行的地下党员赵铮同志,三十年代末期由我单线联系,1940年经地下党上级组织批准,打入汪伪特务机关"76号",潜伏下来为我们党收集敌伪情报。他曾在我家里宣誓,并由我代表组织向他宣布纪律:①严格保密,绝不暴露地下党员身份,不宣扬任何进步言论;②生活上要与"76号"汉奸特务打成一片,吃喝玩乐,花天酒地,都要同他们混在一起,藉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不久后,上级组织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入党的情报部门,从此同我断绝往来,即使在路上遇到,也祥作不识,不打招呼。"文革"开始后,他便被打成"76号"汉奸特务。不久,就有人来报社向我外调他的情况,"勒令老实交代"。我当然义不容辞地把经过情况详详细细作了"交代",说明这是组织上要他打进去收集敌伪情报的,我完全可以为他证明。他们将信将疑,要我写下书面"交代"。隔了几天,又来找我,问当年我的上级领导是谁,我告诉他们是中央银行的袁君实同志。我以为此事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到此可以宣告结束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第三次这些人又由报社造反派陪着来找我了,来势比前两次更凶,拍桌子,瞪眼睛,口口声声"再不老实交代,要你好看!"我莫名其妙,被恶狠狠训斥一顿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去找袁君实,袁表示"记不起来","没有这个印象"。这下问题就严重了,他们硬说这是我同赵铮"串通的",是"假交代",是"包庇汉奸特务",甚至说我同"76号"也有关系……。忽然,不知谁大喝一声:"不准站着说,给我跪下来!"一言未了,拳头皮鞋脚,还有耳光,如同雨点般落到我身上,前前后后足足半个小时。直到"文革"后期,我才知道,赵铮同志的情况,结果是由南京一位老同志(可能是当年我们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给予证明,确实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他打进去的。这个不白之冤总算了结,但我为此也受够了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和迫害,赵铮同志本人的遭遇就更不必说了。
这不过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但类似这种带着框框来"外调"--"勒令交代"的太多了,所谓"外调",实际上是批斗逼供,口口声声说是他们已掌握了证据,只是向我"核实"取得"旁证"而已。例如,硬要我"交代"邹凡扬同志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硬要我"交代"高流同志是台湾的派遣特务……等等。事关这些好同志的政治生命,我当然列举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证明他们绝不是什么特务,否则就无异作伪证诬陷他们。对此,我是铁定了心,坚持不干的。于是遭到残酷的批斗、凶狠的辱骂,就成了"家常便饭"。
这里还应该提一笔的是,我接待的几十批"外调"人员,他们要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地下党员,从外调人员的口中,我知道这些地下党员几乎无例外地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不是"叛徒",就是"特务";不是"反革命分子",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几乎所有的地下党员都是坏人。事实上解放前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出生人死,拎着脑袋过日子,为党为人民作出过大大小小的贡献。但在"文革"中,地下党员几乎全部都是坏人。他们地下时期历尽艰辛,冒着坐车和杀头的危险,为党为人民做了各种各样的好事,到头来反而都被歪曲成为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我有这么一个直觉的感受,十年"文革"中对地下党员的歧视、诬蔑、丑化、陷害,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达到无出其右的顶峰了。
作为"老反革命",我的一大罪状是"招降纳叛"、"拉帮结派",说我解放初把大批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介绍进报社来。这不光是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的问题,而且是政治上把阶级敌人技进党报来的问题。其实,此事"老三反"初期当我还在经理部工作时就有人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提出来过。但客观事实是,刚解放时,报社编辑部都是解放区来的同志,不熟悉上海的情况;经理部则都是原《申报》的老职员,且其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当时的正副社长、总编辑范长江、恽逸群两位同志知道我长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联系着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就要我设法介绍一些党员、进步群众到报社来。根据他们的指示,我通过组织先后介绍了地下党员田钟洛(即作家袁鹰)、金铿然、钦本立等来编辑部,白广荣、蒋湘军、徐明康、应庶康等则来经理部工作,这怎么能说是"招降纳叛"、"拉帮结派"呢?"三反"运动中幸亏副总编辑冯岗同志在一次编委会上为我澄清了事实,为我说了公道话,他说此事的经过情况他一清二楚,并愿意负责作证。这样,我总算顺利"过关",事后还蒙编委会的信任,让我负责领导报社的"三反"运动。对冯岗同志仗义执言,澄清是非,我是由衷感激,没齿不忘的。想不到"文革"中又有人贴出大字报,硬把解放初的这件事重新提出来,作为我的一大罪状。当时范长江、恽逸群两位同志也在"次革"中受到迫害,自身难保,只有冯岗同志还可以为我讲几句话,我曾提出要求,请报社造反组织派人去向冯岗同志调查,他可以为我作证。造反派是否去调查过,我不知道,但对我的这条"罪状",照样批斗不误。但仅一两次,很快就中止了,估计也是冯岗同志为我作证起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件难以释怀的事情。记得"文革"开始不久,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的很多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大意)。对我来说,我认为不理解倒是正常的。一开始就不断挨批斗,不断写检讨,正因为不理解,所以思想是根本不通的。大约在工宣队进驻报社后,我曾给一位在外地的好朋友写信,我同他从小在一起,深情厚谊,有如同胞手足。平时也经常通信,从国家大事到街谈巷议,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多的是共同语言。"文革"开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未通音讯。那次我去信,主要是因为突然被打成"老反革命",诉述了内心的委屈和苦恼,信的后半部分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按我们党的传统,任何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总是先经过调查取证,在准确可信的事实基础上做出初步结论,有时往往还向本人进行调查核实,最后才做出正式结论。我信上说,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工作,谈不上功劳,总也有点苦劳……。现在一下子把我打成敌我矛盾,当反革命分子批斗,实在想不通……等等。大出我的意料,他来了封简单的回信,说读了我的信,感到很意外,很不以为然,认为到了现在还说这些话,实在为我感到羞耻。从上下文的语气看,这里所谓为我感到羞耻,其实质就是批评我可耻!这封信我没有给一家老小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同他的关系,深怕他们感情上受不了。到了深夜,我偷偷地又念了好几遍,终于禁不住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了。我想,可能他也参加了造反派,也可能受造反派"革命大批判"的影响;不过,无论是属于哪种情况,这样的辱骂,竟出自他的手笔,它给我心灵的创伤太深了。
在干校
1968年9月,报社正式划分大班子和小班子,小班子继续办报,大班子专搞"斗批改",顾名思义,我们几十个"牛鬼蛇神",作为"斗批改"的对象,理所当然是属于大班子的。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被审查、清理"的对象数十人;此外就是报社造反派的头头、造反派骨干、工宣队、军宣队以及一般的干部和群众,共约2O0多人。最初是在报社,1968年底或1969年初搬到淮海中路上海教育学院搞过一阵,但时间不长,1970年即撤出上海教育学院,先在奉贤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半年后就到钱桥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去了。
进驻干校的各个单位均按军事化的部队编制,《解放日报》是十七连,有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等。住的都是由"尖刀连"临时盖起来的棚舍,睡的是上下两层的小铁床;棚舍里挤得满满的。"牛鬼蛇神"除了挨批斗之外,就是劳动改造。一早起来,先是倒小便桶,接下来便是下田、挑河泥……等等。当时我已年近花甲,由于在报社长期从事夜班编辑部的工作,经常失眠,身体虚弱,所以初到干校一段时间,既要挨批斗,又要参加强劳动,被折磨得实在难以忍受。这时我就很自然地想起,在报社时听说过的,造反派的某些头头,曾经公开扬言,"就是要把这批家伙(指"牛鬼蛇神")整死!"每念及此,不寒而慄。看来不用多久,我很可能就此死在干校了。
语云:天无绝人之路。事实上我非但并未陈尸干校,倒反而逐步适应过来了。原本是"斗批改"内容之一的劳动改造,日积月累,慢慢地变成劳动锻炼了。开河、筑路、挑担子,什么强劳动都干。我记得很清楚,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大冷天,海风扑面吹来,寒彻骨髓,但由于超负荷的重体力监督劳动,先是穿着棉袄棉裤子,干了一阵,脱下棉袄,再过一阵,把棉裤也脱了,穿着单布衫裤干,照样还是汗流浃背。收工后回到棚舍,用热水擦擦身,穿上刚才脱下的棉袄棉裤,非但没有感冒,稍事休息恢复一下体力后,反而通体舒畅,又神气活现了。这对于长期当夜班。从来没有干过体力劳动的我来说,客观上倒起了一种极好的体育锻炼的作用。我尝到了甜头,开始沾沾自喜。
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对于"牛鬼蛇神"来说,监督劳动绝不意味着体育锻炼,而只能是劳动改造,而且是惩罚性的。谓予不信,有事实为证。
记得有天清早,我在干校附近一个土墩下,把碎石块和泥土装入竹筐,一担一担挑往干校正在铺设的一条煤屑路旁去。以我当时的年龄和体力,挑7O-80斤已经很勉强了。一位"监工"模样的造反派看到我挑的担子里碎石和泥土并未装满,便走过来大声喝令我停下来,责问我"为什么不装满?"我说挑这一担已经很吃力了,再重挑不动……。他不等我说完,拿起铁铲就往两只竹筐里装泥土。我连忙说,请你不要再装了,我实在挑不动。他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再加装两铲,并大声命令:"挑不动也要挑,快走!快走!"我把担子压在肩上,站也站不起来,他还是大声喝叱:"挑起来啊,快走!"我只得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屏住呼吸,勉勉强强站了起来;刚走一两步,便停了下来,原想要求他帮我稍为减轻些,一看他正弹着眼珠怒目注视着我,我也就死了这条心,便用足吃奶的力气,挑着担子,走走停停,摇摇晃晃,总算把担子挑到煤屑路旁。这样一连好几天,走走停停,摇摇晃晃地挑,半个多月以后,竟然能够中途不停,虽然仍要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到后来,终于出现了奇迹--竟然可以不再摇晃一口气排到底了。惩罚性的强迫劳动,结果倒反使我得到了切实有效的锻炼,大大增强了我的体质,胃口好,吃得多,睡得香,与在报社当夜班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哩!前几年,我年届八十,除两耳重听,双目有点白内障之外,身体还相当硬朗,精神抖擞,好几位同志问我,有什么养生之道、保健良法,我总是开玩笑说,我根本没有那一套,说句老实话,身体倒是"文革"中做"华鬼蛇神"做好的!
在干校,挨批斗的除"牛鬼蛇神"之外,便是那些所谓可疑的审查和清理对象。我"文革"初期在报社虽然已被批斗过不知多少次,但来干校后仍然在劫难逃,不过没有像当初在报社那样恐怖、紧张,认为反正是这么回事,思想上好像已经把自己当作"死老虎"了。但有的"牛鬼蛇神"特别是那些所谓可疑的审查和清理对象却不然,每次批斗,有如大祸临头,既紧张,又害怕。作为同病相怜的过来人,我虽然很同情他们,很想安慰安慰他们,但又深怕万一被造反派发现,那就是"反革命串连"、就是"教唆对抗",那就罪莫大矣。于是只得违心地"明哲保身",无可奈何地袖手旁观。
至于轮到我自己,不论大会批、小会斗,虽然也感到委屈、难受,特别是对有些恶言恶语,感到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内心极为痛苦,但也日能自我安慰,自我解脱,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思想上只能泰然处之,因为我对自己最清楚:绝非反革命,绝非叛徒特务,暂时只能忍受,坚决相信党和群众,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还我清白的!
但是,我又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更可怕、更大的灾难紧接着就降临到我头上了。
这是1970年11月的一天,原来第二天要休假,正盼着可以喘一口气,中午,连部突然通知包括我在内的4-5个"牛鬼蛇神",下午要开全连大会,事先要把会场布置好。说这次大会非常重要,一律不许请假,你们一定要在会前把会场收拾、打扫、布置好。于是我们几个人午饭后就赶到会场去了。会场离我们住的棚舍不远,听说也是"尖刀连"用竹条子搭起来的,较简陋,可容纳200多人,是泥地,没有椅子,与会者都得各人带着小木凳或砖头去;也没有主席台,只设一桌子和几条长凳,我们几个人有的打扫泥地,有的用畚箕出垃圾,然后大家一起高高挂起一条长长的红布横幅,上书"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十个大字。大约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干完了。会场不但很干净,而且气氛严肃,一望而知这里即将召开一次很重要的大会。我一边打扫、布置,一边想,今天不知又有哪个"可疑的审查或清理对象"要挨整了。
大会开始前,人们陆续来到会场,地上几乎坐满了人,我们"牛鬼蛇神"则坐在靠近门口边上的最后几排。当连队几个头头和工、军宣队坐定后,遂即由一位连部的头头指着高高挂在上面的横幅,提高嗓门,大声宣布"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并讲了一大段开展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然后又讲了几句,大意是:我们的任务还很重,还必须再接再厉地更深入地开展下去……等等,紧接着便声色俱厉地说道,现在坐在你们中间的就有一个最凶恶、最狡猾、最隐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夏其言!我因两耳重听,"夏其言"三个字没听清楚,便轻声问坐在我旁边的郑拾风,他还未回答我,不料坐在我背后的一个高个子早已把我的衣领拎起来,叫着"到前面去!到前面去!"这对我来说,无异晴天霹雳,实在太意外了。被揪到前面,我手足无措,面对大家站着。这三个"最"字,份量有多重啊!但直到此时,我还如坠五里雾中,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刚才讲话那个头头,又开腔了,简要的大意是,报社有革命群众,接连向市革会领导检举揭发,这个家伙(指我)用畜牲般的语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领导同志……我本能地想辩白,绝无其事。但是头头看见我想说话,又严厉地训斥说,复其言的罪行是"防扩散"的,不准说话,接着就由另一个头头当场宣布:夏其言犯的是"扩散罪",罪行十分严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专政对象,要立即隔离起来。就这样我被押出了会场。当时干校大礼堂旁边有专门关押隔离对象的地方,我以为我也是被押送到大礼堂那边去隔离的,哪知刚出会场,就把我交给候在会场门口的两个陌生人,但他们押送着我不是往大礼堂的方向走,而是把我押送到干校的煤屑大道上,原来那里已经有一辆黑色轿车在等着,押上车,我坐在中间,他俩坐在我两边,我这才意识到,他们是公安局的便衣,这时我想,我要去坐牢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到了目的地--漕河径的上海市少年犯教养所(简称"少教所")。
"文革"后期,据好几位老同志告诉我,在我被押送去"少教所"的当天,干校就出现了"严惩规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之类的大标语,他们说,当时确实感到非常意外和吃惊:本来说是"老反革命",怎么一下子变成"现行反革命"了?我对他们苦笑着自我解嘲说,这叫做"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是恩蒙造反派越级提拔步步高升嘛!
我到底犯了什么严重罪行?在囚车上、在囚室里,我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我也不至于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啊,这点头脑还是有的。这个谜底,一直要在"少教所"关押了两三个月之后,才慢慢揭开。原来问题是出在三十年代我同唐纳(马季良)、蓝苹(江青)的一段关系上。在少教所
"少教所"原是关押少年犯的。由于"文革"中所谓的"犯罪分子"激增,全市监狱、拘留所等人满为患,张春桥表示:未成年的少年,主要是正面教育的问题,并下令把少年犯统统放掉,改为专事隔离审查"牛鬼蛇神"的专政机关。我当时弄不懂,既然已经把我定为"现行反革命"、"专政对象",怎么还要隔离审查?事后才搞清楚,审查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守"的具体罪行、犯罪的具体经过、来龙去脉等等,因此它不是我原来想象中的监狱,因为监狱是关押判了刑的罪犯的,而我则尚未正式判刑。是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这就需要通过隔离审查才能决定。此外,据说被关押在"少教所"的,都是市级党政领导、各界的著名人士和局级以上干部。
尽管这里是专门关押隔离审查对象的专政机关,实际上它与监狱没有什么两样:被关在里面的人,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同犯人无异,市革会专案组来人找你谈话,叫做"提审"……诸如此类。事实上人们也都是把它看作监狱的。
上海解放前我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下,冒着敌人血腥的白色恐怖,长时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组织上反复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包括万一被捕入狱后的纪律等等,因此对于坐敌人的牢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但是直到上海解放,从未坐过敌人的牢,想不到在"文革"中,却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押送到"少教所"这个专政机关去坐牢。对我来说,没有坐国民党反动派的牢,而坐我们共产党的牢,这简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讽刺,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被押送到"少教所"后,首先是搜身,检查所带的行李,把裤带、钥匙、硬币等全部取下,目的大概是防止我自杀。所内一律不叫姓名,而用代号,我的代号是"321"。然后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不许东张西望,"放风"时在走廊上或园子里走路,必须目不斜视,必须低着头直往前走,以及写思想汇报必须狠触灵魂、交代真实的黑思想……等等。此外,家属不准来探望,有事情如送伙食费、送备用金、送衣服用品等(不准送食物)必须通过组织--《解放日报》,由报社指定专人与"少教所"联系。所以,这里的规矩其实是比监狱还要严厉。
接下来便把我押送到一个类似堆杂物的小屋,很闷、很潮湿,墙壁上的石灰都已剥落,室内灰暗,没有阳光,只有一个小小的扎着铁丝网的窗口,但很高,根本看不到外面。屋子里堆着一些柴草、杂物,墙边屋角都是蜘蛛网,墙上和泥地上则有小虫子在爬行。门是反锁着的,除了送饭,没有人来过。我直觉的感受是恐怖,担心长期关押在这里,即使不用刑,也会窒息而死的。
谢天谢地,幸亏这里只关了两天,第三天便把我押送到正式的囚房里去了。我这才发现,这里有好多幢三四层楼、砖石水泥结构的房子,我被押送到最西面一幢的三楼,囚房在长长的走廊西端的最后一间。由于我是"现行反革命",属重犯要犯,所以独囚一室。房间朝南,大约10平方米左右;有一排窗子,全部都装上铁栏。水泥地有点高低不平,房门板厚,上面开了一个小洞,外面盖着一张白纸,揭起白纸,从小洞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室内的一切。但因为有白纸盖着,里面则根本看不到外面。走廊上有全副武装的狱警来回巡视,并不时揭起各个囚房门上的白纸,通过小洞察看室内囚犯的动静。
相对说来,同楼下的小屋子相比,那简直是上天堂了;比在干校挨"斗批改"的日子也好过多了。既不批斗,亦不劳动,每隔半个月左右还"放风"一次,到下面园子里去活动活动,园子里除大片草坪和树木之外,还有一排排整齐的冬青树,树高2公尺左右,两排树中间,留出一条狭弄,所谓"放风",就是给囚犯单独在这条狭弄里来回走走,活动活动,做做深呼吸。每次"放风"约一、二十分钟。当然来回都是有人押着的,并且按规定双目严禁斜视。
尽管没有受到在干校时的那种折磨,但有些情况却是出乎意料的难以忍受。例如:孤零零的独囚一室,除了有时听到大声的惨叫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真是死一般的静寂。当然,更没有人可以交谈(据事后了解,大部分是双人囚室,虽然室内也严格禁止谈话,但终究可以偷偷地轻声交谈)。在这里,我除了读《毛选》,看《解放日报》,就无所事事,闲得发慌,此时此刻,才对"度日如年"这四个字,有了崭新的、更深切的体会。《解放日报》是每天午前收到的,但我却如获至宝地舍不得一下子把它全部看完,往往先看头版要闻,有时只看半个版,下半版只看看标题,下午再看内容;二、三、四版则分别留在下午和晚上看,副刊和大大小小的各种广告则留在第二天早上看。这样,一张对开4版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第二天午前,而且确实是认真仔细,一字不漏的。
但报纸总共只有4个版,即使分成几次看,终究费时有限,空闲着的时间还是很多很多,于是想了个办法--抄《毛选》、抄报纸。为此几次写条子要家里半打半打地买练习簿,请报社哪位同志送到"少教所"来。到出所时为止,所抄的练习簿,竟有高高的一大叠。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报社造反派篡夺了《解放日报》的领导权以后,就千方百计为"四人帮"服务,把党的机关报变为他们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舆论工具。说句老实话,我在报社是不大看报纸的。现在为了消磨时间,非但硬着头皮看,还要逐字逐句抄。这一来使我感到触目惊心,--从版面到内容,从报道到言论以至各种文章,连篇累牍地都是不堪卒读的造反舆论,诸如攻击诬蔑刘少奇、陈丕显等好多位中央和上海的党政领导,鼓吹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煽动极左思潮,歪曲篡改党的政策,猖狂诬陷小平同志,影射攻击周总理,竭力美化江青和"四人帮"一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正是由于读报、抄报,使我对于《解放日报》造反派在制造反革命舆论方面的罪恶行径看得更清楚,有了更形象、更具体的新认识。
不过,抄书抄报纸虽然无可奈何地消磨了一些时间,但毕竟还是解决不了"度日如年"的问题。于是又动脑筋、想办法。"上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上午在抄报纸副刊时,得到启发,灵机一动,"对了,不妨试着写点旧体打油诗呀!"于是在读、抄书报之余,便开始踱方步,吟打油诗了。
我中学时代有位语文老师,对古体诗词造诣颇深,他自己也经常写诗填词在报刊上发表。这位老师授课时很风趣,特别是讲授旧体诗词深入浅出,大家都很爱听他的课。他经常鼓励我们要仔细欣赏并学习写旧体诗词,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对旧体诗词发生了兴趣,直到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以后,经常跑书店购买这方面的书籍,常常以阅读这类书籍自娱。但是,说实在的,直到现在,我只是爱好,还谈不上欣赏能力,连平仄、诗韵、格律也不懂,当然更谈不上写诗了。偶尔兴之所至,想用旧体诗词来抒发一点感想或情绪,也只会不按平仄、不计格律,诌几句十足道地的打油诗而已。
写打油诗的主意虽然定下来了,但在囚室里是不能写在纸上或练习簿上的;因为经常有人来"查房间",床上、桌子上、抽屉内、乃至《毛选》内,报纸上、练习簿里都要仔细检查,连墙壁角落也不放过,万一被发现我在写旧体诗词,那问题就大了。因为按规定,除了思想汇报、交代(包括外调材料)和向家里要钱物的条子之外,别的都不准写,连日记也禁止写的。他们很可能认为,我写旧诗一是明目张胆搞"封资修",二是蓄意影射……罪名可大了。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一面来回踱方步,一面在肚子里打腹稿,在肚子里修改,在肚子里定稿,并牢牢记住;然后反复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尽管只是几首蹩脚打油诗,但因"得来大大费功夫",因此敝帚自珍,押回干校后就马上从肚子里倒出来,写在小本子上,当做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为节省篇幅现在摘录三首如下:
一、思念亲人(七律)
西风落叶霜满天,彻夜灯明难成眠(注一);别梦依稀肠欲断,泪眼相视觉无言。
遥念三老(注二)风烛残,尤愁全家锅蚁煎;咫尺天涯一"窗"隔(注三),何年何月重相见?
70年农历除夕
注一:囚房全夜不关电灯,通宵达旦室内极亮注二:指我双目失明的老父和年逾古稀的岳父母注三:指"铁窗",即牢狱
二、追忆三个"最"字的大会(五言)平地起风波,晴天惊霹雳;明日休假始,今朝自由失。
会场布置毕,批斗如突袭;强调三个"最",罪大且恶极。
正询指何人,衣领已被挈;道是"防扩散",早有人揭发。
念彼揭发者,居心实叵测;信口雌黄事,敢否来对质?
不容作申辩,"现行"罪已立;忽闻送隔离,天旋地昏黑!
滔滔黄河水,滚滚浊流急;河清终有时,冤清知何日?
度日如度年,离愁伴孤寂,最怕熬黄昏,偏逢元宵月。
佳节倍思亲,泫然老泪滴;梦魂徘徊处,依稀亲人泣。
71年农历元宵节
三、光卿诞辰(采桑子)
天公不识人间忧,今又中秋;今又中秋,别恨离愁何时休?
当年拜月焚香斗(注),痴情依旧;痴情依旧,心香一炷遥祝寿!
注:与志光同志结婚后,每年中秋节(她的生日)晚上,我俩一面赏月,一面在白天买来的香斗中插下香烛,并焚烧一张"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纸条,以庆祝她的生日。
我在"少教所"除了度日如年、寂寞无聊之外,另一件苦恼的事,便是半夜里挨饿。在报社夜班编辑部工作了十多年,每晚11点钟就吃夜餐,长时期来,"习惯成自然",即使后来不当夜班,临睡前总得吃一顿宵夜。有一年住华东医院两三个月,每天总是买两份夜餐,其中一份就是留着临睡前到浴室里去吃的,在干校也不例外。现在到了"少教所",每月缴本人定量的粮票,每天供应三餐--早晨稀饭、馒头,中午晚上白饭不限量,让你吃饱,但当然不可能再吃宵夜了。因此往往半夜里肚子饿有时硬是饿醒失眠。这种苦恼,在干校倒是不曾有过的。怎么办呢?大约到了单人囚室4-5天后,觉得非解决不可了。灵机一动,有了,他们每餐送饭到囚室来,都是房门开一条缝,把饭菜塞进门口,由你自取。于是我就在取早餐时,多拿两只馒头,关上门,把馒头偷偷塞进被子里,到晚上就寝时,因室内灯光通明,先例一杯开水凉着,然后把被子蒙上头顶,钻在被窝里吃馒头,因口干,起来再喝半杯水,这时热水已变成温水了。就这样,我在囚室里也吃上了宵夜。不料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突然来查房间,当查到床上时,他们随手把被子拉出来查看正反面,两只白馒头就滚在地上。他们厉声喝斥,"你这坏蛋,竟敢偷馒头!"我先是惊若木鸡,接着就向他们"解释":我有"胃病",多年来临睡前必须吃点东西。否则非但胃痛难受,而且饿了肚子就失眠。"这里有医生,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谎称,我们单位里医务室的医生开过药,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说这是老胃病,不大好治,要我临睡前吃点容易消化的东西就行了。果然,就这样止住了胃痛,已经十多年了。他们似乎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板着脸大声说:"不许再多拿馒头!胃病我们找医生商量。"说完就走了。不过我馒头还是照样多拿,万一再被发现,我可以强调实在胃痛难忍,同时也可以反过来证明我确有胃病。不料隔了几天,他们来了,说下午有人陪我去瑞金医院检查治疗。当时我进所已两个多月,还未理过一次发,头发、胡子都老长老长,到了医院,医生一看我这副模样,旁边还有人押着,一目了然是个犯人。他用听诊器在我腹部听了一会,按脉搏、看舌苔,于是像是对我,也像是对押我的人说,主要是营养不良,胃病不太严重,但长时期来临睡前吃东西,突然停止,胃部不适应,就会有条件反射性的隐痛,他开了三种药,要我临睡前服下。可能是他开的药含有营养成份,再加上我的心理作用,这以后一段时间睡前�
夏其言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