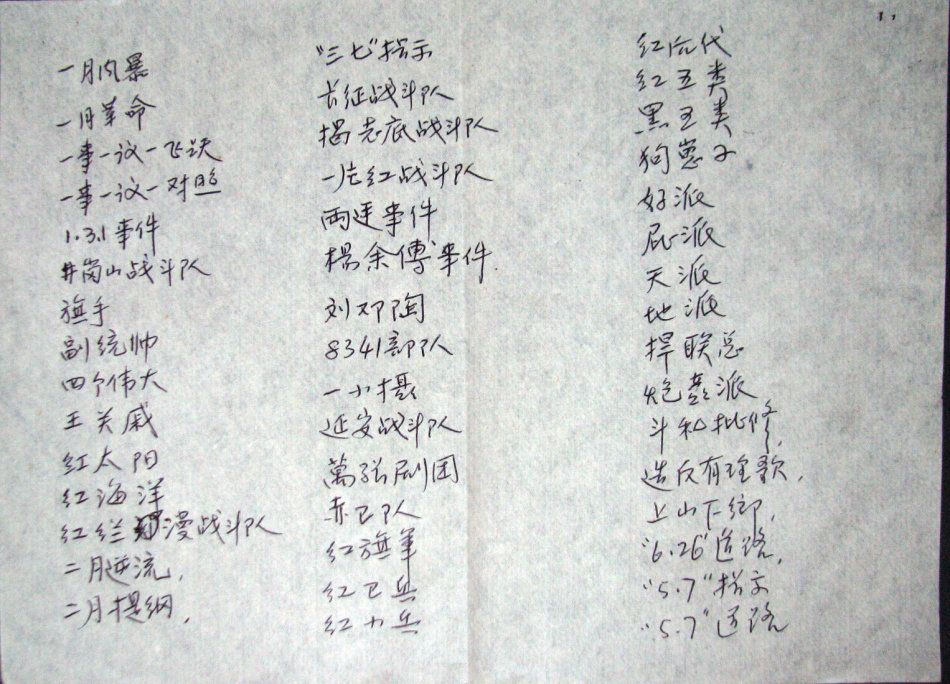
对49年以后中国历史感兴趣,鉴于中文互联网有关的记忆和记载正在被大规模地有计划地移除,本博主要用作收集网络“垃圾”,“拯救”网络记忆和记载,可能偶尔会有点原创,稍微会转一点资料性强创见多的不被主流刊载的学术性文章。另外,凡华夏文摘刊登过的文章一般不cross post,当然也会有例外,视情况而定。
老田 专门控诉文革期间的“法西斯迫害”
专门控诉文革期间的“法西斯迫害”
老田
在一些自由派网友看来,如果谈论文革同时不控诉法西斯暴行和迫害问题,就必然是为毛泽东辩护甚至是为四人帮翻案的文革余孽,当然就因此丧失了起码的道义地位,需要被剥夺说话资格。所以,老田这一篇文章专门来控诉这个。
有影响力的高官们反复申说,文革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代,有超过八千万乃至一亿人口受到迫害或者牵连。我们无妨假定这个数字经过严密的统计,或者至少出于审慎而负责的估计,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文革期间是什么人和什么力量把如许之多的人口推到受迫害的地位上?官方宣传给出的一个标准答案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
文革无疑是文革派发动的,但是长期存在着强大的反文革派。由于文革十年中间政治博弈有多次反复,参与的群体都有积极表现,因此区分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有着很清楚的依据。显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文革派,周总理也是,文革派的群众基础是造反派群体,文革司令部和造反派组成文革派阵营。反文革派也是有司令部的,各级对文革特别抵触党政系统的当权派都属于反文革派阵营,1967年军队支左之后,绝大多数军队干部也是反文革派的,而反文革派的群众组织则有有些演变,第一个反文革派群众组织是北京的“老红卫兵”和各地当权派及其派出的工作组组织的多数派,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多数派逐渐趋于瓦解,在二月逆流时期由支左的军队干部扶持的新的反文革派组织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为代表的拥军派,此外广州的东风派和重庆的“革联会”都是。双方最大的分歧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到底是向上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向下对准“黑五类”,反文革派要求对准黑五类,文革派要求对准走资派。在文革期间,造反派担心被反文革派攻击为“右派翻天”一般不敢接纳黑五类参加组织,所以,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多数属于“非文革派”。
从武汉的文革实际看,文革期间的迫害事件,至少有70%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不少于25%的数字是“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大约4%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另外可能有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与武汉的情况接近。
从文革的时间段看,1966年516通知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反文革派主导的,省市委当权派派出工作组并组织多数派,对付“非文革派”和“准文革派”,例如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抛出的“三家村”就是典型的“非文革派”,李达就是在此期间被反文革派批判而死的;而各个大学进驻的工作组所重点打击的少数派则是后来十年文革的中坚分子,但是此时他们还没有主动参加到文革运动中间来因此只能算是“准文革派”,这是“反文革派”转移运动大方向的第一次浪潮。1966年8月十六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主导的第二次转移运动大方向的浪潮是“抄家破四旧”运动,以王任重的小儿子王三宝为首领的“反文革派”中学生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在一个星期之内抄了23000家,这是一次非常集中的由反文革派发动并由反文革派执行的迫害“非文革派”的行动,全国约发生过数百万起。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期间,造反派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形成文革派的基层力量,在十年文革期间,文革派对反文革派采取主动进攻姿态的唯一时间就是这个时候,时间不长,大约只维持了4个月,在一月夺权前后,文革派又一次“迫害”反文革派的高潮,例如召开批判大会给当权派戴上高帽子等等。由于中央文革控制的“两报一刊”公开支持基层文革派,各地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普遍转入“罢工”状态,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亲自部署了所谓的“三道防线”——组织小官轮流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中级官员组成轮流值班小组、高官如张体学等人穿上军装躲进军区——而实质上进行了全面罢工。这其实就是造反派自我夸张的所谓“斗垮走资派”的真实情况——当权派既非“被斗垮”也不是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更不是被“夺权”,而是自己主动选择“政治罢工”的。
当权派的罢工实际上是向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施加压力:要么你们同意回到文革初期当权派所选择的运动方式——在武汉水院透露出来的计划是“57年加58年的形势”(按:指反右大跃进)——要么老子不干了,你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想办法建立党政系统之外的第二套指挥系统。由于毛泽东拒绝后退,结果只能是选择军队支左——让国家机器从后台走上前台担负恢复秩序的智能。军队支左之后,就有一个“二月逆流”或者“三月黑风”,反文革派直接调用军队的力量对文革派进行镇压,这个期间的典型案例有青海的“二二三事件”(赵永夫命令军队开枪打死学生和工人造反派180余人,打伤数百人,此外还抓捕上万人),四川的成都军区一夜之间抓捕了十多万人,武汉是在317夜晚抓捕了“工人总部”头头近500人。这一次是反文革派调用军事力量迫害文革派。
在1967年4月6日“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失去了以军事力量维护自己地位并打击文革派的政策“缺口”,由此各地开始组织“新保守派”——拥军派来实现对文革派的镇压(此时,文革初期由工作组组织起来的老保守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逐步陷入瓦解),全国拥军派的经典代表是武汉的“百万雄师联络站”,他们在军区的“64公告”之后,组织对武汉三镇造反派据点的“扫平计划”——先扫平汉阳地区、再对汉口逐条街道进行扫平、第三步扫平武昌的各个据点,在此过程中,百万雄师围攻各个在造反派力量集中的单位以及造反派的宣传据点,杀死造反派100多人,杀伤数千人。在另外一个极端上,重庆的54军成功地把“老造反”中间的815争取成为自己的“扫平”工具,没有像武汉那样通过人武部去组织武装基干民兵来压制文革派,重庆的武斗实际上从属于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并非造反派的内讧。拥军派代替军队来实现当权派的意愿,是当权派适应“军委十条”之后的政治形势需要,在正式的国家机器之外寻找替代力量的产物,是反文革派优越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手腕的成就。武斗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属于反文革派镇压文革派的需要。
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全国的新保守派逐步陷入瓦解,文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是反文革派对于文革派的仇视和矛盾并未缓解,而是稍事休息留待革委会的工作程序中继续解决。武汉的造反派在720事件之后,发生了“钢新之争”,比较重要的全市性事件有“新中原事件”,局部的有武重的“五三事件”等,这是从属于文革派对文革派的迫害性质。与此同时,由于造反派的翻身,也有少量的针对反文革派的清算事件,例如揪斗百万雄师坏头头,揪斗百万雄师的黑后台,此时发生的“迫害”算是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说是720事件之后受造反派迫害的干部群众和战士人数高达184000人,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期,武汉军区高官信俊杰自己坦陈“零头也没有”,应该说,信俊杰在74年的说法更为接近真实。
1968年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发起“捅马蜂窝”行动,把部分造反派头头从革委会赶出去并“交给群众批判”,在年末革委会军队干部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间,有大量针对造反派的行动,这都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的事件。同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间,有大量的“非文革派”再次受到反文革派的迫害,例如许多大学教授自杀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运动期间。因为,新中国成立还只有十多年,混到大学教授地位的人士多数因为是旧统治阶级出身并在解放前就完成了大学教育的,因此“历史很不清白”成为一个共同问题,同时由于文革期间绝大多数高校教师和学生都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反对当权派把文革变成“反右大跃进”,是中央文革真心实意的“社会基础”,所以,受到优先重点“清理”,因为很多老教授出身不好未能明目张胆地参加正式的造反派组织,所以看起来是“非文革派”,但是反文革派却认定这些人之所以同情造反派观点乃至出于阶级本能想要实现“右派翻天”,故刻意打击。所以,非文革派受迫害中间本来就含有反文革派的复仇意志。
1969年九大前后,造反派不忿新任当权派的镇压,发起“反复旧运动”,体现的是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群众对于当权派压制的不满和反抗意志与力量。九大之后,中央召集造反派头头集中北京开会,制止了这一反抗形式,实际上取消了“四大”。反文革派此后敢于放手整治文革派,通过清查“北决扬”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把绝大多数文革派都打成反革命分子,胡厚民从1969年就开始被监护,杨道远1971年被隔离审查之后直到1983年判刑后才出来,各种“五不准学习班”隔离了绝大部分文革派头头和骨干群众。这一反文革派主导的运动,多数使用保守派(包括老保守派——三字兵和后来的新保守派——拥军派)作为“动力”,军队当权派在背后主持、党政当权派积极参加,实际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是一次由反文革派的领导层次(军地当权派)协调领导的、以新旧保守派群众作为依托的、对文革派力量进行全局性清算的“运动群众”。这次运动的成果是在全国的造反派中间查出了超过1000万反革命分子,如果刘少奇一个人重要性还没有超过普通人1000万倍的话,那么文革最大的冤案就应该“五一六冤案”。某元帅和某总书记所提供的文革受迫害人数中间,不知道是否包括这一部分受害者,如果包括这的话,这一大批反革命及其家属的数量就高达数千万之众,那么他们的估计应该不会脱离事实太远。
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一生中间“最不民主”“个人独断”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开始了。为了终结军事波拿巴主义的幽灵,他一个人对军地当权派与新旧保守派结成的、以清算文革派“造反罪行”的强大“神圣同盟”发起了反击,这一次反击的重点集中在军队当权派身上,很多军队高官失去权力和地位仅仅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和一个不给任何证据的判断——林彪死党。各地领导清算造反派最为积极的军官高官,几乎没有例外都被毛泽东宣布为“林彪死党”——例如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有些人例如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15军军长方铭被宣布为“活党”在政治上被矮化了。自此之后,“神圣同盟”中间最坚定的迫害文革派的“坏分子”退出了政治场域,剩下来的当权派和新旧保守派在文革派的舆论攻势面前居于手势,所以武汉发生了“两赵一王”向造反派妥协答应并安排“补台”的事件。大体而言,由于神圣同盟的破裂及其内部矛盾一时不能解决,因此,当权派出于被动退让态势。王克文晚年的回忆文章中间说:他一生最为后悔的事情就是在1974年的“三大讲”中间做出了丧失当权派一贯立场的发言和检讨,以至于在临终前的回顾中还要作自我批评。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文革派的巨擘,那些在此期间丧失地位乃至丧失立场的迫害,都应该记载在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账上。
毛泽东本人亲自出来终结了“批林批孔运动”,因此“补台”的事情在过了1974年夏天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正是这个夏天,北京成立了一个医疗组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一位天津来的专家发现毛泽东得了“运动神经元病”,这个病无法治愈而且患者生命一般不超过两年。毛泽东以极端专制的手段破坏了反文革派的神圣同盟之后,显然没有选择让造反派“补台”,而是让神圣同盟中间的党政当权派全面补台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文革前期的“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在“军干群”的“三结合”中间毛泽东采取步骤——从庐山会议开始中间经过林彪事件最后于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对调”——彻底驱逐了“军”,没有提拔“群”,而是恢复了“干”的优势。这个驱逐“军”的过程,实际上是邓小平重新上台的主要政治前提。恐怕不能认为毛泽东很新任邓,或者邓是毛的人,而是毛泽东已经做出明确判断——造反派不可能掌权甚至是“在野比在朝有利”——同时军队当权派掌权的消极作用最大,因此,只剩下一个唯一的选择:选择一个次坏的群体掌权,这样的判断做出之后,在次坏群体中间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就应该出来了。看来,毛泽东连次优选择都没有,只有次坏选择,而且这个次坏选择还是他本人不得不以最不民主的方式驱逐了党内强势群体之后才具备条件的。1974年毛曾经有一首词赠周,颇能反应他的心境和选择空间:“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批林批孔”在1974年夏天就被文革派自己终结了。反文革派并没有因此满意,而是由此看到了进攻的利益,如果说早期对于文革派的清算还主要是集中于文革派的群众身上的话,此后反文革派的清算矛盾则转而指向文革派的司令部。当时北京有“四大金刚”之说,这四个人是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和张爱萍。邓小平的女儿写书说,这个时期他父亲对于四人帮是采取攻势而不是守势,为了坚定胡耀邦的信心邓小平曾经给他交底说:“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耽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人的呀。我问小平:‘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小平说:‘可以,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地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小平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只要叶剑英能够控制了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至于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8年春天)
在邓小平领导“四大金刚”进行反攻过程中间,也有涉及到下层的部分,根据王克文的回忆,在1975年初他和赵辛初去中央找负责同志回报,这个负责同志给了他们30个抓人指标,他们返回武汉之后于2月7日就立即执行,被抓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在针对文革司令部的反攻中间,四大金刚最开始阶段是把毛、周和江一体看待的。国防科工委情报所核心组副组长告诉我,张某在国防科工委就职之后,曾经指示情报所刘某组织16名高级翻译,搜罗海外的有用材料,其中就有一篇国民党特务所写的污蔑周总理的文章,这篇文章说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破获共产党案件是周为了权力斗争需要而故意泄露给特务的,因为张的这个行为过于露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由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三个副总理亲自抓国防科工委的运动,张的干将刘某此时来反戈一击提交书面揭发材料,陶鲁笳原本不想涉及张爱萍的事情,但至此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就是陶鲁笳迫害张爱萍的背景。在后来的“非毛化”事业的起始阶段,张某的智慧被再次启用,这一次是大量流亡海外的共产党叛徒写下的攻击矛头集中于毛泽东的书籍,例如王明张国焘等人的书,以“现代稀见史料译丛”名义出“内部版”,然后摆在新华书店里公开出售。
把周总理从文革派中间区别出来,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情,周逝世之前对反文革派过火行为进行过弹压,此后不再是一个引发反文革派不满的问题,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四五事件中间民众对周的好感,使得反文革派理性地看到这是一个必须费心争取的政治资源。此次针对文革司令部的“反攻”后来被缩小范围定性成为“反对四人帮”,但是开始并非如此,首先是针对毛和周的,特别是周荣鑫表述的各种教育观点就是与毛针锋相对的,对于江青的攻击反而是他们最不认真对待的:多数以“传播谣言”的方式来进行,例如说江青的头发牙齿屁股都是假的,还说庄则栋是江青的什么什么等等,在批邓时江青则反过来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胡耀邦所在科学院是“黑风口”。
很多造反派有意见,他们在挨整的时候被反文革派告知,是文革司令部某某人下令整治他们的,例如1975年就流传说是王洪文要把谢妙福等人“关起来”的说法。而且,武汉造反派一向认为自己跟四人帮没有什么关系,许多重大行动都是接受了周总理的直接指示,不承认是四人帮的帮派骨干体系,但是,反文革派现在需要跟周总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样一份政治资源,这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1967年三月间,方宝林就曾经被找去北京,周总理亲口说过:“现在全国上下有一股暗流,要葬送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红卫兵要奋起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便是有这样强有力的证据,造反派并不能因此免于进监狱。与一般底层文革派不同的是,在毛和周生前,他们没有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从后来的事态演变看,他们没有被革除马克思主义的教籍被定性为反革命,也仅仅是因为与他们的名字相联系的政治资源为人家所需要,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早就准备了“摔得粉碎”。
1976年之后,大量的文革派被送进了监狱,反文革派直接调用司法机关。这一次反文革派对文革派的行动,是在他们直接而全面掌握了国家机器之后,捍卫自己的地位不再需要“非正常”地调用军队力量,也不需要“运动群众”的外在包装了,所以,邓某人说“两派都错了”——连反文革派“百万雄师”也包括在内了。这一次反文革派的行为,与文革期间的各种迫害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和逻辑一致,这倒不是外人栽赃而是反文革派自己承认的,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文革派,他们在文革期间被正式关押的时间乃至被非正式关押的“五不准学习班”时间,都可以折抵刑期。一位百万雄师的基层头头余某倒是比某些高层反文革派更有政治家风度,他说某某人动用司法机关来处理政治案件是破坏了共产党政权的传统,海内外都没有这么办的。可能自由派人士痛恨的斯大林要除外,如果斯大林时期被判刑入狱的苏联官员都算是迫害的话,显然因为参加政治运动而锒铛入狱的人数也应该计入受迫害数字。
从文革初期开始,反文革派对于文革派的迫害时间段,最具体地体现在文革初期的50天的白色恐怖、二月逆流时期、1967年四月份之后的武斗阶段、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期、1970年开始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1975年的治理整顿和1976-1983年的司法清算阶段。一个文革派人士可能全部经历这多次迫害,所以,文革派受迫害的人数有大量的重叠,受迫害数量大大减少了,否则可能要占据文革期间受迫害数字的80%以上。非文革派受反文革派迫害的时间段集中于文革初期的50天、1966年8月底的红色恐怖时期、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合计起来可能达到数百万起,相当于文革派受迫害数字的三分之一左右,受迫害程度也比较轻微,基本上不把他们作为“五不准学习班”的对象;毕竟,反文革派并不认真把这些黑五类人士看作对手和威胁,只是在觉得方便的时候需要借助打击他们来缓解自己的处境——按照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的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就是:“先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护他们过关”。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的时间主要是一月夺权时期和720事件之后。文革派迫害文革派的时间,主要是一月夺权时期和720之后成立革委会之前。
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的时间,主要军队支左时期针对“亮相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和“三结合”革委会成立之后,文革前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对一个与自己“监护”在一起的老记者说:造反派群众喊口号说打到我那只是说说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我就真的倒了但是主席是了解我的不会打倒我,要是那些穿军装的人要打倒我我真的就倒了。宋侃夫这个说法非常切合实际,被毛泽东定性为林彪死党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就说过“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看起来,除了军队干部之外基本上没有好人,造反派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军干群三结合最好留下一结合。
因为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很多,但是出书写文章进行控诉的人却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高官群众中间,特别是集中于省部级高官中间,他们许多人都出了回忆录亲自控诉,在回忆录之前有家属和记者专门帮助控诉迫害。这一部分人的情况挺特殊,大多数人在1966年领导罢工之后都失去了官位,新成立的革委会中间没有得到位置。在失去官位期间,大多数人都被北京卫戍区监护过,这个监护待遇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截然对立的描述,有时候是说自己得到保护特别是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所以“监护”属于“大树参天护英华”;在另外一些场合,同样的人又把监护待遇作为控诉“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依据。同一个事情由同一个提供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与我们在中学语文学习的形式逻辑有矛盾,看来语文教材的编写受到四人帮余孽控制使得我们在把握高官们控诉时发生思维混乱。
从卫戍区这个机构的情况看,也许能够得到另外一些信息。1966年在林彪的“518政变经”讲话之后,成立了一个“首都保卫组”,在这个保卫组下辖北京卫戍区,根据吴德的回忆:“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四人帮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参加过首都保卫组,也缺乏施加影响的条件。吴忠接替温玉成掌握卫戍区,直到1976年,工作时间最长。吴忠对人说过,那些当时监护对象,档案他都亲自看过,人也亲自去看过,档案上百分之八十几的人都是总理批准监护的。一些人从卫戍区解放出去的时候,他也曾经亲自去送行,被送行的就有万里这些人,当时都是紧握他的手,感激得哭哇,他们讲:这都总理是为了保护我们,担心被红卫兵揪走批斗,还说一些感激不尽的话,怎么后头都变成控诉迫害了?吴忠还说,他们写文章说四人帮迫害贺龙,说不给水喝,吴忠就很奇怪,这也是我们卫戍区管的,他在西山住的地方,是中央的战备疏散点,隧道外面建了几座小楼,贺龙住的小楼是给总理准备的,楼上还住着乌兰夫。战士把他们都是当作首长看待的,哪有什么虐待?高富有的回忆就说得更为详细,原先傅崇碧不愿意接受监护贺龙的任务,说战士们不会做首长的饭,怕怠慢了不好,结果是高富有直接给曾绍东师长打电话,师长很主动说做不好饭可以慢慢学。(《从宝塔山到中南海:高富有记忆中的一代伟人》赵桂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出版第323-326页)
在高官的控诉中间,还有一个控诉专案组逼着监护对象交代历史问题的情节。根据宋任穷的回忆,相关人士亲口告诉过他说没有什么四人帮插手的问题:“我刚到中组部时,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首先遇到的是接收并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移交给中组部的大量案件。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本来党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确定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专案办的主要负责人把着不交,说什么:专案办没有‘四人帮’干扰。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能复查平反。”“被审查的人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南征北战的元帅和将军,有原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正、副省长,有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司局长和一批专家、教授、作家、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还有少数居民和学生。据统计,被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21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7人。”(《宋任穷回忆录》,77-79)宋任穷听到的这个说法肯定不全面,后来在两案审判中间,曾经查证说江青插手过王光美专案组并在其中11个人的监护或者监禁(该专案组监护或监禁的总人数64人)报告上有圈阅或者同意的批复。吴德的回忆可以佐证“专案工作没有什么四人帮的影响”这个说法:“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一、二、三办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
显然,本文仅仅只是说明了文革期间法西斯暴行的实施者身份,并不代表实施者要自己承担责任。为了表示本人在自由派人士教育下所取得可喜进步,谨把过去数十年久经考验的几条著名公理罗列在这里,根据这些公理,即便不是文革派迫害的人也仍然要由文革派承担法西斯名义和责任。
第一公理:缺乏经验者可以免责,这个公理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表述方式“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虽然中央高层业已经过了四清时期“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的争论,二十三条已经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方向上本不再有丝毫疑问,但是那些法律上被称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仍然应该免责,因此,派出工作组和在群众中间横扫牛鬼蛇神的人,其责任应该转归文革派承担,法律上也明确规定监护人应该为他承担监护责任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士的损害行为负责的,所以,50天的问题和红八月的问题都归文革派负责,官方的权威文革史就是这么处理的;由此,第一公理得到一个另外的表述模式:文革派是反文革派的监护人,反文革派人士都是限制行为能力者。
第二公理:缺乏理智者可以免责——缺乏基本判别能力的人可以要求免责。例如著名的自由派教授秦晖认定反文革派“老红卫兵”之所以犯下那么多的血腥罪责,是因为他们是唱着“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这样的歌儿长大的,所以理性不健全缺乏判别能力,因此要求免责,根据这个公理,罪责要归于制造个人崇拜的人和享受个人崇拜的人。不过,后来的老红卫兵演变为“保爹保妈派”,忽然一下子恢复了理智,这个演变难以解释,需要秦晖教授继续研究,看是不是这些人唱了新的歌儿所以一夜之间就恢复了理智。本来,第二公理是第一公理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但是,由于个人崇拜现象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深远,是一代青年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间经历了有缺陷的教育过程的结果,按照秦晖教授的研究成果就是那一首歌儿唱下来都对青年人的社会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需要独立出来。
第三公理:阶级关系不变论——解放前是阶级敌人的、文革中间仍然是阶级敌人;这一公理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光荣的清华四一四派,他们就是这么讲的;根据这一公理,一切阶级斗争都必须指向黑五类,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就肯定属于“右派翻天”,必须给予最严厉的镇压,二月逆流时期武汉军区就是把“工人总部”描述成国民党还乡团那个样子,并给自己的镇压行为赋予保卫红色江山的意义,所以,不是造反有理而是镇压有理;毛泽东1968年才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是后知后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这样的高人在1967年二月逆流时期就已经认定他的对手是国民党还乡团了。看起来,在某些部分问题上,文革派和反文革派还是有这高度共识的。后来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以及治理整顿时期,乃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权派们继续发现那些人不过是国民党第二。而且,根据第三公理,除非不搞阶级斗争,要搞就必须搞黑五类,因为是毛泽东坚持要搞阶级斗争的,所以黑五类受迫害当然就转而由毛泽东承担责任。
第四公理:只能打江山的坐江山——这些人不仅仅是当权派掌握权力的官员,还是党和国家的化身,革命的化身,社会主义制度的化身,因此,批评这些官员都必然只能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行。为了抵消这些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行的不良影响,文革后学界和政界曾经紧密结合,做了大量的工作,胡华曾经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出了数十卷之多,由陕西人民出版社。胡华在第一卷前言中间说的很清楚:“一九七九年三月,全国十八所高等院校的党史工作者在郑州集会,筹备成立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今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了有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二百余人参加的中共党史人物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五十七份党史人物传记,制定了一九八O年编写计划和今后三年规划,并选出了党的老革命家何长工同志为会长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会。这些活动,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河南省委、广东省委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目的“是肃清林彪‘四人帮’诬蔑攻击革命先烈、英雄人物这一恶毒阴谋的流毒,拨乱反正的需要。我们要为革命先烈、革命前辈恢复名誉,树碑立传。”在第五十一卷的前言中间,另外一个学者兼高官在回顾了一个时期的树碑立传工作之后说:“《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作者近千人(参加收集传记资料的人员还未计在内),这是一支很大的党史人物研究力量。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解决他们撰写传记必需的人员、档案、经费等困难问题,写出文情并茂的传记来。我们这个研究会是个长期没有设专职办事人员、没有专门经费的学会,如果不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调动了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学界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很难设想仅仅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样一部12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所以,不管文革派如何受到镇压和迫害,都是咎由自取,并不由此产生反抗的权利,根据第四公理,即便在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号召下参加运动使用“四大”武器的,也需要坚定不移地追究为反革命罪行。一代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在政界和学界的紧密结合中间得到信息的。
当然,这些公理的概括可能不完全,在说服力上还有欠缺,还需要各位自由派大腕继续补充完善。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2046303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