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study, I think, I pray, I love and of course I hate ….
生活倒影(上) - 待得清夷

外婆的父母睡在一座小山丘上。
我们会在清明时去看望他们。几家人,几辆车,前前后后走上几十里路,先到一个叫陶吴镇的地方,停下来买些纸钱,再继续开。
小山丘坐落在一个村子里,离陶吴镇几公里远。我一直想知道起那座小村子的名字,可是似乎从没人告诉过我,入口也从没写过什么标识,它就默默无闻的呆在一个不知名的道上。
可我又总认识它——当车子拐进来时,我就知道是这里了。
驶过一段印着车辙土路,又驶过一段沾满黄泥的公路。一开始,路边只是稀稀落落的白色砖瓦房和翻过土的耕地;清明又多雨,灰色的天接着裸露的土,厚重的如天上低低的云。
越往前,视野便越开阔,田里的生气也多了些。规整的小麦,伴着几株不规整的杨树和灌木。小麦一直跑,跑到远处的村落里,树也跟着,跑出新芽儿来。
漫山遍野的绿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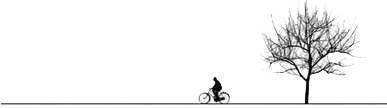
车停到远方亲戚家,大人们拿着一包包纸钱和金元宝准备上山。
路途泥泞,上了年纪的姨婆需要支着竹棍,偶尔也要人搀着才能走过。但是她却执意要自己提金元宝——那几大袋子都是清明前她自己折的。
领路的人叫大陈子。陈是姓氏,他在家里排老大,便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别称。
他总穿着一件藏青色耐脏的袄子,黑色的布鞋。爱笑,笑起来眉眼憨憨。因为待大家都热情,所以我们都同他亲近。
可是有一年,他脸上的笑容似却少了。
家里人说,他前阵子得了癌症,家里掏空了钱,都是靠村里人筹款帮忙的。不知吃了多少痛,又挨了几场手术的折腾,终于捡回了一条命。如今拖着病弱之身,又背负几十万的借款,原来的笑也全苦没了。
可是,他见着我们,还是那样的热情;家里人关切的问他近况,他挤出些笑来:我的身体已经好些了,你们不用担心。
大陈子是长辈远方的亲戚,在这个村子里还算富裕,有个三层的小土房。
他们家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麦子成熟的时候,地面会铺满麦粒。我和妹妹喜欢蹲在地上抠麦粒玩;或者抓起一大把,趁大人不注意了拿去喂鸡。
鸡被圈在一堆砖块垒起的地方,入口处被尼龙网围着,小麦子就顺着缝滑下去——有时候表哥会调皮,直接把麦粒往网下重重的一扔,惹得鸡群乱叫扑腾,他、妹妹和我此时看了鸡的窘态,都大笑起来,一时热闹非凡。
大陈子听了笑声,以为我们喜欢他家丰收的麦粒,从屋后拿出耙子,笑着想教我们怎么翻麦子。
可耙子又大又重,没有那群胆小的鸡好玩,我们便随便使使劲,把铺好的麦子推的乱七八糟;大陈子也不气不恼,就笑着看我们瞎玩;只是其他大人看见了我们这样,纷纷责备我们捣乱,翻麦子这件事只好作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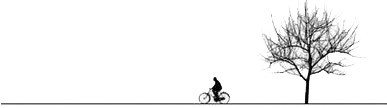
空地旁有几株香椿树。只有春天才能吃到香椿头,它们其实就是树梢上抽出的嫩芽——从树枝的最前端冒出头来,和暗红色的叶尖混杂着,一个枝丫只长这么一小丛,所以城市里一小把就要卖到三四十元。
我和他就是因为香椿树相识的。
对于小孩子来说,采摘野菜像是一场易上瘾的游戏。掐它们好玩;采完了低矮的树枝,爬上树去摘也好玩。我们都喜欢吃香椿,用它炒鸡蛋有股别样的好吃滋味;还有什么比又玩又吃更开心的呢?
于是,我们一群小家伙热情高涨,见到香椿就眼尖心跳,一会就横扫了大陈子家的几株。发现隔壁有更多的香椿树之后,不禁又对那几株伸出魔爪。
正当我们采的正在兴头上,突然看到一个男孩从家里走了出来。
我们彼此隔着一排香椿树,看不清他的脸。于是便不知道他的表情:不知道他有没有恼怒,有没有要告诉他的家长来抓我们........
我们心虚起来:“这是你家的树吗?抱歉,我们不知道........”
他没答话,就只站着。
我们赶紧走过树,想和他解释什么,可是我们一挨近,他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样,赶紧跑回了屋子,仿佛摘香椿的小贼是他。
或许是后来我们玩的笑声太大,又或许是他一个人在家太孤独,我们离开之后,他总会站在家门口怯怯的望着我们。
他个子很矮,年龄比我还小的样子,脸庞却不算太稚气,又尖又瘦,有些蜡黄。
他看上去怕我们,又想接近我们,嘴巴张了又闭,半天哀愁自卑的吐不出一个字来。
我们冲他笑,喊他一起玩,他犹豫的抓了抓衣角;我们又努力走近他,他却紧张的退后半步。
“嗨呀!你怕啥啊!”表哥哈哈大笑:“还没见过你这样胆小的!”
他又跑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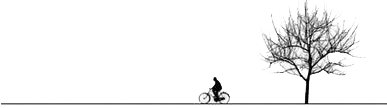
直到一家人招呼着准备东西上山时,他才终于接近了我们,蜡黄的脸半天憋得通红:“你们待会去干嘛呀?”
“去扫墓。”我回道。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嘛。”
“好。”
我们从大路走到小路,小路越来越窄,最后只能一群人排着队走。
农田离我们越来越远,路也就长的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充满野味:随意生长的树和野草,偶尔刮着裤脚;黄鹤菜、点地梅黄一片白一片的散落其间,菜蝶在花草之中随处可见。
我们还要绕过一片河塘,那里的路更加潮湿。我走路从不小心,经常把鞋子踩得全是湿泥。
“那个跟着的男孩是谁啊?”大人问道。
男孩羞怯极了,不答话,只顾跟着我们一起走。
“隔壁家的!”表哥答道。
“很乖的孩子。”大陈子走在最前面领路,他认识这个男孩,便又加上一句。
那个男孩终于不像原来那样拘谨,抿嘴笑笑,开始和我们说起了话。
“我们到哪去呀?”他问。
“一个小山上。”
“你和大陈子认识?”我问。
“嗯,他对我好。”
“你们怎么认识的?”
他没答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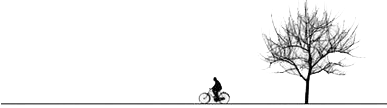
他们在这里长眠。
几丛低矮的灌木围着他们,再往下是几片茶树。春天,灌木和茶树都长出了芽,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绽放的白色茶花。
那个时候,大陈子还很未患病,身强体壮。他和几个年轻的哥们在小山丘下挖几捧泥土,堆成一个小堆,在上面插上柳条放在墓前,告诉他们,我们来了。
姨婆将金元宝拿出来,眼前的山丘、树木和墓碑透过火光在热浪之中来回荡漾,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
在这安静的山丘之上,后辈们按着顺序在墓前磕头。烟雾会迷住眼睛和鼻子,我总会不自禁的呛出泪来,真正流泪的却是外婆。
下山时,小孩子的心情便再也不沉重了,彼此的话也多了起来。
“姐姐,”小男孩又主动找我说话:“这附近有个地方我很喜欢。”
“什么地方?”
“让我带你们去吧。”
妈妈觉得这里路难认,怕我走远了回不了家。小男孩这时竟有了勇气,信心十足的说道:“这里我很熟的,到时候我带姐姐回去。”大陈子听见我们之间的谈话:“放心吧,他是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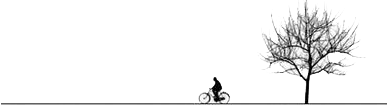
他带我们来到了一片秸秆地。
一堆堆像茅草一样的空壳,铺满了目光所及的一切地方——从低处爬上小坡,从地里漫到天上。一刹那,天空、草坪和树....似乎全世界都被渲染成了枯黄。可是,我又望得见远方,远方明晃晃的油菜花田从枯黄中生长出来,像是秸秆堆外一道灿烂的金边.....
男孩直接躺了下来,和我们说他喜欢来这里看天空,可是我没跟着。相比于天空,我更喜欢看远处的地平线。
这里不像城市,所以我可以尽情远眺。我尽力看向很远很远,尽头茫茫的,是灰色柏油路和油菜花的边界。我看见白色的车慢慢的驶向花开的烂漫里.......
我们在秸秆堆上发呆,偶尔说话,男孩说的更少。我们就这样呆了几个小时,分开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男孩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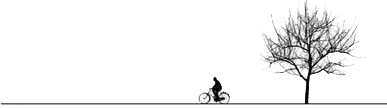
我和小男孩保持着特殊的友情 —— 一年一面。
第三年的时候,他性格似乎不像从前那样腼腆了。那天,他说了很多话,我们玩了很多游戏。
捉迷藏的时候,他负责抓人,我们躲。有次我藏在了大陈子家的三楼,因为是毛坯,所以很少有人去。原来准备把这里装修起来,留着当他孩子的婚房,可是他们后来都去城里赚钱了,很少回来,所以这件事就被搁置了。
如今这里面挂满了腌肉,白色的肥油流出一股咸咸的齁味。我半屏着气,半蹲在窗口看着外面瘦小的男孩,他老实的捂着眼睛默默念到了一百。
上了几年小学之后,除了数学,他还学了更多东西。他热衷于写字,让我们用竹竿教他我们名字的写法。“姐姐,你猜我姓什么?”未等我答话,他就说:“我姓朱,姐姐,我告诉你怎么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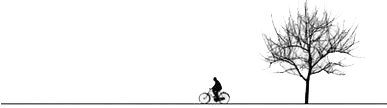
大陈子似乎格外喜欢这个男孩。
中午大家聚餐时,他让男孩同我们一起吃。男孩害羞,不敢同陌生人上桌,我们四个伙伴就各自拿着碗盛饭装菜,然后端着一起到别处吃。
大陈子总要给男孩多夹几块肉和菜。
表哥打趣道:“叔,你对他可真好呀。”
“也就我疼他。”他回。
“你再疼他,能有他父母疼?”我们笑了。
“他父母从小就不在身边。”
“为什么?”我们不笑了。
他把男孩的碗慢慢放下,满眼疲惫的叹道:“全跑去城里挣钱了呗!一年到头也不回来看看!”
大陈子开始絮絮叨叨起来:“有天,我收完麦子经过秸秆地,看见有个小孩蹲在那里哭.....我看衣服、身型都很熟悉,感觉像是隔壁家的孩子,就赶紧走近去看.....发现果然是他。我一直问他怎么回事。”
“他话少,总不回答我,就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半天才问出几个字.....我这才知道,他才上学就叫人欺负了....还是几个女娃!说他没爸没妈,是野孩子没饭吃!我气的问他:‘到底是哪几个女娃瞎说八道,我去找她们!’结果,他却哭道:‘我不想去想了...我不想去想了....’”
“我心疼他,想多陪陪他。至少得等他不哭了再回去。他那天哭完了就躺在秸秆地上看天,我坐着——因为秸秆太戳背了,我可不愿躺下来。说实在的,我也不懂天有啥可看的,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他不哭了,却啥话都没说,一直憋着,也把我憋得要死。不过,我看他情绪缓和了,就准备离开,这时他突然说话了。”
“‘叔,他们真的不要我了吗?’他这么问我。”
他又继续给小男孩夹肉,把饭碗装的满满的。
我们沉默了。
他也止住不说了。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