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宣传主义:舆论,新闻自由与新媒体(上)

建国以来,中国的新闻业始终在宣传新闻主义的主导下发展。宣传新闻主义以宣传目的取代了新闻的传播目的,以宣传内容取代了新闻的事实内容,以宣传主体取代了新闻的编辑主体,使中国新闻业的发展长期囿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未能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以至于推动舆论表达、参与权力制衡等种种社会功能。基于公民对某一社会事实的看法形成的舆论,因新闻内容的失实,亦失去了其反映民意的作用,沦为了拟态环境下可被任意塑造的群体意识。舆论本质的丧失加剧了拟态环境对于现实的取代,被维持这一取代所不容的新闻自由则更加无从实现。这是本文前半段所要叙述的观点。
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能否为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带来转机?
如今依托互联网通信技术获得发展的新媒体,以其个人化、现实化、互动化的传播特质打破了新闻仅仅经由传统媒体流向受众的单向传播格局,使公民个人参与到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中,得以便捷地通过生产新闻反映事实、通过传播新闻制造舆论。
本文后半段将指出,此过程一方面澄清了舆论的反映对象,以公民亲身经历的社会事实取代了经由新闻宣传代为告知的拟态事实,使舆论回归其反映民意的本质;另一方面则通过舆论本质的回归与现实化,消解了传统媒体经由新闻宣传营造的拟态环境。或将使宣传新闻主义难以为继,从而利于推动新闻自由的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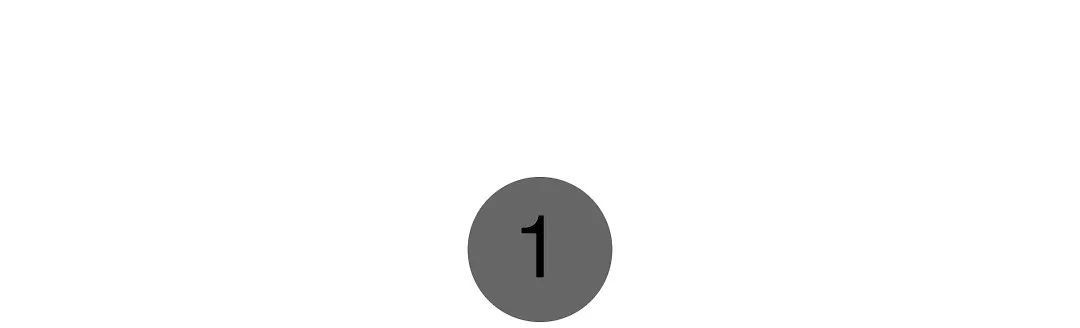
有别于在私有制环境下创立、发展,且经由资产阶级革命与启蒙运动的演进而最终实现高度自由化、商业化的欧洲新闻业,社会主义新闻业在诞生之初便受到政治宣传的有力影响。解放后的中国政权以苏联新闻体制作为范式,确立了中国新闻业一律实行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使中国新闻业服务于执政党的需要,最终形成了中国新闻业高度一元化(Unified)、宣传化(Propagandized)的特征。
列宁在俄国工党时期首先提出了「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1]的主张。列宁认为,新闻不仅要能够代表党的观点、立场,而且这种观点、立场还必须得是「正确的」,即是不能偏离党的路线、方针的;且新闻一定要能够体现党在政治问题上的取向,成为党在政治问题上进行表态,由党指导政治风向的耳目喉舌。

在布尔什维克时期,列宁创办了《真理报》(Pravda),将其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宣传革命路线的主要阵地。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随即将其上升为苏共的中央党报,并作为苏共政治局下属的宣传鼓动部(Agitprop)最初允许刊发的报纸之一大量印发。宣传鼓动部作为苏俄以至苏联时期的最高文化管理部门,不仅决定报纸是否得以出版,更以行政手段严格限制报纸的报导内容及宣传目的,使一切新闻都成为了宣传苏联共产党伟大成就的颂词,列宁倡导的宣传新闻主义至此付诸现实。一如施拉姆所言:
「报导新闻并非康米主义报业的首要功能,其职责是在解释新闻、依照党的目的选择新闻,并扮演起教育与指导人民的角色」[2]。
彼时的苏联新闻媒体不再以报导新闻作为第一要义,而是将如何分辨事件是否被党允许作为解释的对象、如何解释事件使其合乎党的宣传需要、如何进行再叙事(Renarration)使人民接受这一党的宣传作为首要任务。
本应作为新闻产生的出发点,以决定新闻内容的事实(Fact),却反而沦为了需要经由党的宣传要求重构(Reconstruct),并以新闻的形式覆盖原先的事实,投影向受众的最终的归宿。由此可见宣传新闻主义对苏联新闻传播事业倒果为因的异化(Alienation),这种异化不仅贯穿了整个苏联时期新闻业的发展,并且在日后深刻地影响了仿效苏联新闻体制发展起来的中国新闻业。
中国现代的新闻传播产生于清朝末期出现的民间学团或社会报刊,在形成之初多以宣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成果、救亡图存思想作为主要内容,体现了晚清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对于改革旧制度的呼吁,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催生下发展壮大的欧洲新闻业拥有相近的出发点。
而延安方面则学习苏联的新闻思想,在党内确立宣传新闻主义为党进行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党报不仅是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而且是鼓动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3]。
我国当代新闻学者亦有指出国内的新闻工作,具有与苏联高度一致的宣传性特征:「报刊是党的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喉舌,它的一切宣传活动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党报不但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4]。边区的新闻发展在此时便开始服从于宣传的需要,其后的各届领导层亦一脉相承地延续了宣传新闻主义的传统;宣传新闻主义对新闻的异化亦发生在中国社会,并在其后逾半世纪的实践中,逐渐催生出中国社会独特的新闻业态与舆论环境。
在宣传工作成为中国新闻工作的本位后,新闻原本具有的诸多社会功能渐渐被单一的宣传目的所改造、取代,使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受制于极为有限的范围,不得不每时每刻都与国家政策和党的方针路线保持一致,「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5],无从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自由性。政治压力的不断发散与政治宣传的持续要求,不仅使新闻自由成为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近乎禁忌的话题,亦使得高度依赖于新闻自由进行表达的舆论,一齐噤声不语。而这一社会环境的形成,首先是通过将新闻传播异化为宣传工具开始的。

笔者认为,宣传新闻主义对新闻传播的异化,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的举措实现:
一、以宣传目的取代新闻的传播目的。要了解新闻为何进行传播,我们就必须先要知道何为新闻。美国传播学者班尼特曾如此定义新闻:「新闻是最基本的信息来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社会、政治以及政府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他们的利益」[6]。这一定义不仅解释了新闻的实质,且同时阐明了新闻传播的目的:在性质上,新闻是对社会事实(Social Fact)进行反映的载体,是民众认知周遭环境的信息来源;在用途上,则是帮助民众汇总以一己之力难以窥知的包含着社会事实的种种信息,以便民众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处境。易言之,无论新闻所反映的事实为何,其目的始终是作为「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7],向民众反馈其所处社会中的信息,帮助民众认识社会的全貌,也即马克思言下新闻的“人民性”。而宣传新闻主义,则放弃了满足民众了解社会的需要这一目的,使宣传工作成为了新闻工作的本位,「既是新闻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新闻工作的直接归宿处」[8]。这一宣传方法通过减少新闻报道中的事实内容,代以对某一宣传目标进行的大篇幅的评论,使受众将注意力集中于宣传内容,而或多或少忽视了其中包含的事实。受众是否能够从宣传中认知到事实、能够认知到多少事实,在宣传目的已经达到的情况下,自然成为了不必考虑的事情。
二、以宣传内容取代新闻的事实内容。新闻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众用来观察周遭社会的「精神上的镜子」,正是因为其反映的是对象是真实的客观世界、其反映的内容建立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这一基础为民众真切地了解社会提供了保障。宣传新闻主义在对某一事件进行宣传时,往往会面临现实中存在着不利于对这一事件进行宣传的对立事件。此时,该主义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对于某一事件的宣传,往往会采取对不利于宣传工作进行的事件不予报导,乃至于采取曲解、掩盖的方式应对。例如,苏联政府为宣传其推行于斯大林时期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闻中禁止出现对于政策执行不当引发的局部饥荒这一事实的报导,仅准许报导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在局部饥荒爆发期间,斯大林仍然坚持在接受新闻采访时将个人对于政策的乐观预期杜撰为事实宣传,而对政策失败的事实则只字不提:「大家说工人们的物质状态戏剧性地的提升,生活变得更好更有趣。这当然是事实。这也使得人口繁衍比起过去更加快速。生育率提高,死亡率降低,而整体人口增长更加强劲了」[9]。

然而这一时期,苏联整体的人口生育率事实上连年下降,民众的生活水平亦发生了严重倒退,而这一事实在新闻报导中却被宣传内容中民生安乐的虚假信息所取代,致使远离饥荒地区的民众长期无法了解真实情况,宣传内容中的虚假信息反而成为了被民众相信的「事实」。中国在「大跃进」时期出现的种种宣传上的所谓左倾错误,亦是以宣传内容取代新闻事实内容的实证。各级媒体在报导地方粮食产量时大放卫星,以杜撰出的产量掩盖真实产量,也是最终致使三年困难时期爆发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以宣传主体取代新闻的编辑主体。任何新闻,都需要对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叙述、加工后,方可形成便于受众阅读、理解其内容的体裁。而新闻编辑主体,正是承担了将事件转写为新闻这一再叙事的过程的能动主体。由于撰写新闻实际上是对新闻事实进行的再生产,这一再生产过程「始终离不开编辑主体意识的指导和制约」[10],编辑主体的意识将会影响新闻反映事实的准确程度、新闻中所包含的观点与立场等种种非客观内容,从而造就了新闻的多元形态。由于编辑主体并非仅仅代表自身,而是代表着与自身持有同样观点的一类人,多元形态新闻的存在给予了不同的群体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立场、诉求的媒介,使少数观点不至于湮没在主流舆论中。在宣传新闻主义中,始终存在着指定的宣传主体,即需要在撰写新闻时贯彻其意志,并体现其要求的对象。此时的新闻编辑主体虽然形式上仍具有独立编辑新闻的能力,但由于其编辑新闻的唯一目的即为满足对特定对象的宣传,编辑主体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身的能动性,被宣传主体的意识侵夺了自身的主体意识。此时,「指导和制约」新闻编辑的对象将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编辑主体,而是由遥不可及的宣传主体弥漫开来的意识形态,使少数观点在一元化的舆论环境中逐渐沉寂。党的宣传新闻主义表面上看只在党媒的范围内推行,在党媒以外本应存在其他的编辑主体;但由于中国与苏联一样对新闻媒体采取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进行管理,实际上并不存在「非党媒」,不受控于宣传主体的自由媒体也就无从谈起了。
至此,新闻由某种事实的传播者,转化为了某种宣传目的的接受者;由对某种事实的反映,转化为了由某种宣传内容去反映的宣传方式;由某种编辑主体对于事实的能动的再叙事,转化为了遵从某种宣传主体的要求进行的命题叙事,被改造得不可名状的新闻彻底沦为了忠实的宣传工具。

在持续高压的政策环境中,群体意识的一元化在中国得到了相当成功的推行。而作为群体意识外在表现的舆论,与同舆论的形成相伴相生的新闻自由,在彼时的中国皆销声匿迹。
舆论(Public Opinion)这一概念发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用以指代某一社会群体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代表了某一社会群体在某些社会问题上共同的利益取向,是群体意识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具现化。自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各学派对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莫衷一是。在此,不妨引用中国新闻学者何冰的阐述:「它是一个具有政治功能性的概念,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公开讨论,往往表现为社会秩序基础上一种共同的公开反思结果,因而可视为现代社会政治正当性的来源,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11]。在何冰看来,舆论不仅是一种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看法的公开表达,而且还是一项政策或某一社会事务的实行在公众中被接受程度的反映,是执政者在治理社会时必须将其纳入考量的晴雨表。公众通过营造舆论风向来凝聚社会共识,为执政者制定、推行政策指出某一取得了公众的大量同意的方向,在事实上使执政者行使权力的过程部分受制于民意,使舆论成为了以民意制约统治权力的重要制衡机制。由此可见,舆论的本质,即对民众意见的反映。
舆论在公共领域的畅通表达,则高度依赖于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的实现。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公共事务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难以对公共事务进行深入的理解,并对衍生而来的社会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这一事实降低了民众新闻进行舆论表达、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利于舆论制衡功能的实现。此时,作为民众认知社会的「最基本的信息来源」,新闻便起到了整合社会中的各种资讯,并将其如实地反映给民众的重要作用。籍由新闻,公众得以较为便捷地接触到来自社会的各种讯息、增进对于社会议题的了解,进而形成对某一议题的个人观点,最终令与之相似的众多观点汇集而成方向一致的舆论。可以说,新闻在舆论的形成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而新闻想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扮演好传播媒介这一重要角色,就必须以新闻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作为前提条件。新闻自由,通常被认为是言论自由在公共传播领域的概念延伸,泛指新闻传播过程中应当享有的诸多「制度性权利」[12],如国际新闻学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对新闻自由进行的四项定义:探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自由、批评自由。新闻自由学说强调新闻媒体应当尽可能地脱离政府的管控、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存在,应当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免遭受行政干预而导致报导内容的失真。新闻自由的实质即以新闻的形式实现社会资讯的自由流动,提高社会资讯对于公众而言的透明度,从而保障公众对于社会事件的知情权,为舆论的形成扫清阻塞信息传播的障碍。在这一社会资讯自由流动的过程中,作为载体的新闻只不过是资讯的一种表达形式;「新闻自由」这一概念运行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仍然由舆论的形成需要决定。舆论的本质即反映民意;而唯有实现新闻自由,才能使民意得到最为真切的表达,所以新闻自由只是舆论实现其本质的一种途径。
在实行民主政体的现代国家中,舆论自由、新闻自由普遍在宪法层面即获得保障,例如著名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Amendment 1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便明文规定了美国宪法对于新闻自由的保障,要求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法律[13],从而为舆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法理依据。
中国同样在宪法层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14];然而遗憾的是,在法律实践中,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却往往受到诸多下位法的限制,而无法得到实现。例如,《刑法》中规定了由一系列罪名组成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刑法》对其的描述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15]的行为,却没有对这一行为的定性标准、严重程度的判明进行详细的规定,从而使「危害国家安全罪」可以被相当宽泛地解释,一切有违国家政策、与国家的方针路线持不同看法的言论,皆承担着被冠以这一罪名的风险。即便国家并不一定会对发表相关言论的个人以该罪名进行事实上的制裁,但这一罪名的存在本身已形成了一种政治恐怖(Reign of Terror),迫使公民在舆论表达上进行自我规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工作时刻意规避风险话题,使本就趋于一致的群体意识中的少数意见更加噤声于由政治恐怖构成的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中,舆论与新闻自由彻底消寂于不容杂音存在的一元化群体意识中。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版,卷4,《我们现在的任务》
[2]威尔伯˙施拉姆. 《人类传播史》,远流出版公司,1994版,页260
[3]中gong三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年9月28日
[4]马光仁.《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刊载,1992年9月
[5]习.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
[6]W.兰斯˙班尼特.《政治的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版,页1
[7] 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 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版,页12
[8]杨保军.《“后新闻业时代”开启后的中国“新闻主义”》,《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9月,卷14,期5
[9]斯大林.《致人民公社的讲话》,1935年12月1日
[10]张秀红.《编辑主题的主体意识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6月,卷30,期2
[11]何冰.《舆情:本土概念与本土实践》,《传播与社会学刊》,期40,2017,33-74
[12]林子仪.提出于《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13]Amendment 1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