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事實,躲避宣傳。
我們都是革命派:關於“樣板戲”藝術政治化的思考

2019年6月22日,當筆者第一次坐在劇場裏,親眼觀看一部“樣板戲”作品,發現自己對這種藝術形態如此熟悉又陌生,以至想要更多了解有關“樣板戲”的前世今生,於是便催生了這篇文章,企圖為自己做出壹個回答:“樣板戲”是如何被創造並影響了數以億萬計的中國觀眾,又如何在上演50年後的今天,同時被官方施以封禁和允許。
01、從舊劇革命到革命現代戲
對於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來說,從來不曾聽過、接觸過“樣板戲”或許是一件概率頗低的事情——
“奶奶,您聽我說!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今日痛飲慶功酒,壯誌未酬誓不休”、“這個女人不尋常。刁德一有什麽鬼心腸?這小刁壹點面子也不講。這草包倒是壹堵擋風的墻”……
即便是生活在後“樣板戲”時代的年輕人,也一定不會對這些朗朗上口的戲詞感到陌生。
正如芭芭拉·米特勒所說,“中國戲曲故事本身就是一個變革的故事,就革命京劇而言,這種變化只是披上了一種新的裝束。”[1]當我們回顧“樣板戲”從無到有的生命軌跡時,會發現,它並非一種突發性事物,而是一個有著特定歷史溯源的文藝形態。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幾年中,伴隨著一系列文藝政策和意識導向,“樣板戲”的母胎已經開始被有計劃地孕育著。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自清末民初以來,傳統戲曲不斷革新的自發進程,包括20世紀30年代的“主題先行論”、40年代的“舊劇革命”,直到50年代,激化演變為對於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革命之間的強烈沖突。
1958年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戲曲工作者應該為表現現代生活而努力》的社論,明確指出“表現現代生活是今後戲曲工作的發展方向”,“以現代戲為綱,推動戲曲工作的全面大躍進。”[2]奠定了傳統戲曲在新社會中的創作方向和思想基礎。
進入60年代,在領袖意誌與政治鬥爭之間,多重因素直接促成了傳統戲曲的革命性轉變。毛澤東經常將傳統中國戲曲的面貌概括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1963年11月,毛兩次批評《戲劇報》和文化部,說:“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工作方面,特別是戲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註意這方面的問題。如不改變,就改名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3]半年後, 1964年6月5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召開,此時的毛澤東,對文藝界的傳統主義傾向仍舊感到不滿,幾天後的6月11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評文化部門說:“唱戲這十五年根本沒有改,什麽工農兵,根本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那個封建主義同資本主義,所謂帝王將相,才子佳人。”[4]

正是這一次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的展演,以及毛澤東對文化界未能對戲曲展開徹底革命的強硬態度,為幾部京劇現代戲日後成為革命“樣板戲”提供了意識指導和藝術雛形,如中國京劇院的《紅燈記》、《紅色娘子軍》,北京京劇團的《蘆蕩火種》、《杜鵑山》,上海京劇院的《智取威虎山》,山東京劇團的《奇襲白虎團》等,但是,這一批新創現代戲還沒有被冠以“樣板”的名稱,仍被稱之為“革命現代戲”。
事情的轉變發生在第二年春天。1965年3月16日,《解放軍日報》一篇名為《認真地向京劇<紅燈記>學習》的短評寫道:看過這出戲的人……眾口壹詞,連連稱道:“好戲”“好戲”!認為這是京劇革命化的一個出色樣板。[5]這是“樣板”一詞見諸報端的起始,隨後,在文藝界和戲曲界,“樣板”這個新穎而別致的詞語,開始被頻繁地用來形容革命現代戲。
02、“样板戏”正式确定
1967年5月1日,上海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劇《白毛女》,山東的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北京的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在北京舉行了會演。
5月10日,《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了江青親自署名的文章《談京劇革命: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的座談會上的講話》,同時發表的社論《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指出:《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等京劇樣板戲的出現……不僅是京劇的優秀樣板,而且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優秀樣板,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個陣地上的“鬥批改”的優秀樣板。
至此,八個最著名的“樣板戲”被確定下來,它們在全國範圍內被官方迅速宣傳推廣,達到了空前的普及程度。有記錄表明:自六十年代後期正式推出以來,僅僅是1967年5月和6月在北京的演出中,第一套八個樣板戲的演出就達到了37天218場次,累計觀看人數達到了330000人次。[6]



第一批“樣板戲”(包括5個現代京劇、2個芭蕾舞劇和1個交響音樂)上演後,全國各地樣板團也加緊了新樣板的創作與排演,不久就推出了第二批“樣板戲”,共計10部,包括京劇:《龍江頌》、《杜鵑山》、《磐石灣》、《平原作戰》、《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草原兒女》、《沂蒙頌》;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革命現代交響樂:《智取威虎山》。
據統計,至文革結束前,(第二批)仍處於試驗修改階段的京劇“樣板戲”還有《紅雲崗》、《審椅子》、《戰海浪》和《津江渡》、《草原兄妹》、《夜渡》,以及舞劇《杜鵑山》,合計7部。這些作品還在打磨完善過程中。第三批計劃中的“樣板戲”有7部,包括京劇:《決裂》、《春苗》、《第二個春天》、《戰船臺》、《警鐘長鳴》;歌劇:《抗寒的種子》;話劇:《樟樹泉》。[7]這些未經打磨的作品,要麽因為全國觀眾對多年以來的單一視聽產生厭倦,要麽因為江青和四人幫勢力的倒臺無疾而終,未能在舞臺上留下過多資料,也沒有產生諸如18個早期“樣板”作品那般廣泛深刻的影響力。
文革期間,雖然仍存在革命歌曲、群眾舞蹈、紅色歌劇等形式的文藝演出,但“樣板戲”無疑占據了絕大部分的中國戲劇和音樂舞臺,“八億人民八年八個戲”的口號被用來形容這個紅海洋般的“樣板戲”中國。

03、江青與“樣板戲”
60年代極左意識形態為“樣板戲”的產生營造了濃厚的社會氛圍,但不言而喻的是,如果缺少江青的個人推動,“樣板戲”也很難成為壹種獨特而影響深遠的藝術模式。
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布後,江青壹躍成為政治風雲人物,她對“樣板戲”的關照與影響超過了正常文藝生產的人為尺度,“樣板戲”也因此帶上了江青的個人印記。正如她自己所說:“我就叫做緊跟壹頭,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緊追另壹頭,那就是革命小將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8]”毛澤東及其階級鬥爭理念給江青樹立了強有力的文藝幹預屏障。
江青非常在意自己在“樣板戲”創作過程中的個人介入——
在觀看《蘆蕩火種》(後改名《沙家浜》)演出結束後,她表示:“不行!這出戲是我管的,我說什麽時候行了才能對外演出”[9];
與《奇襲白虎團》劇組見面時,她明確表示:“這個戲不經過我不行”[10];
在召集《白毛女》劇組開會時,她說:“這個戲我要了。上海,我就要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11]
用權力之口將樣板戲收歸己有,同時,試圖弱化作品創作團隊的存在。“玻璃杯是工人制造的,但誰見過他們在玻璃杯上留下自己的姓名?”是江青的壹句名言,藉此邏輯,她要求凡是“樣板戲”範疇內的作品,均被冠之以“集體創作”、“集體改編”等名目。
沒有江青,就沒有最終形態的“樣板戲”,拋開“樣板戲”,江青“文藝旗手”政治標榜的合理性也將大打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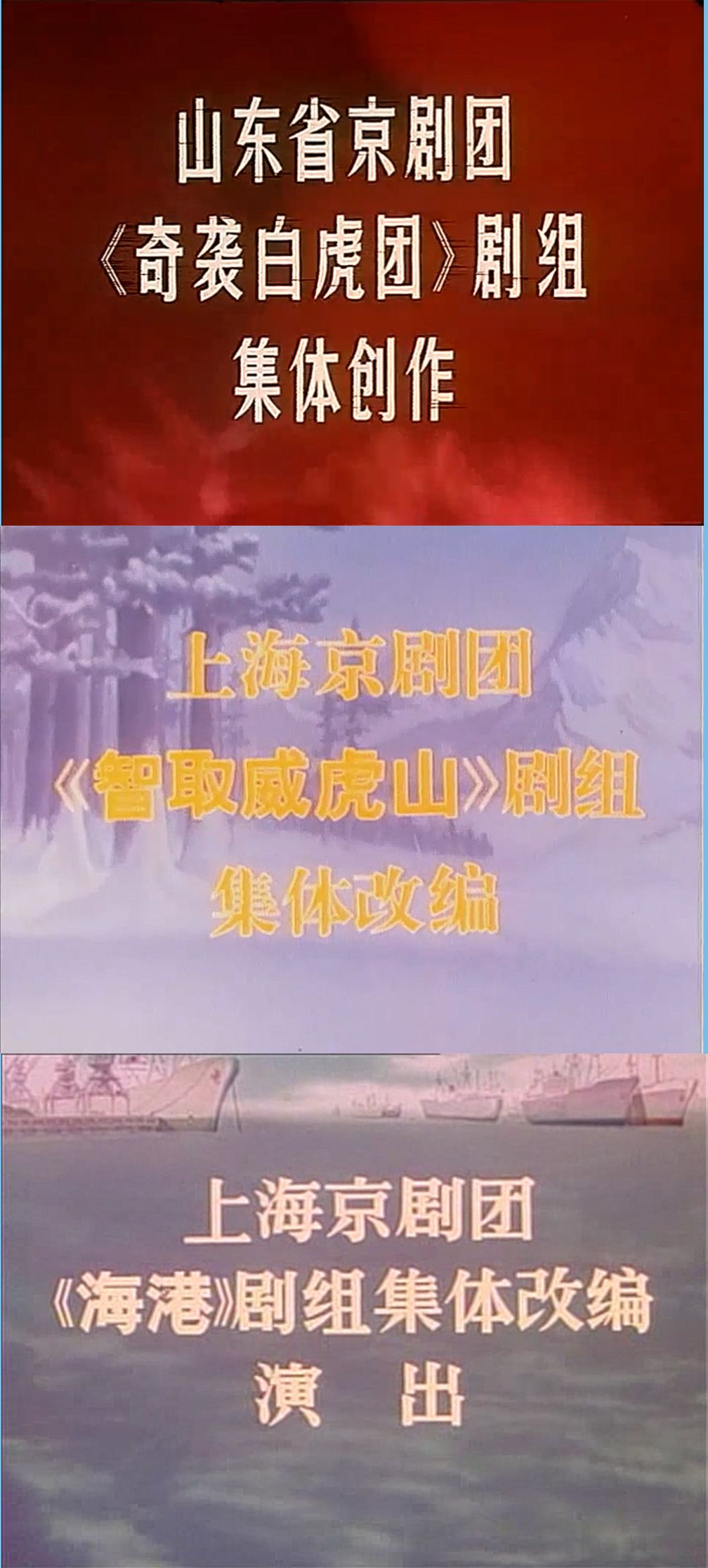
04、“樣板戲”的文本解讀
祝克懿在其博士論文《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中,將“樣板戲”放置在文本的情境中,並從語言的修辭、表現風格、音樂體系等方面對“樣板戲”的語言材料進行整理分析,這也啟發了筆者,以文本的角度重新關照“樣板戲”所表露出的同質化模因。
筆者選取了《杜鵑山》、《海港》、《紅燈記》、《紅色娘子軍》、《龍江頌》、《磐石灣》、《平原作戰》、《奇襲白虎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10部京劇“樣板戲”劇本,過濾掉對話人名、副詞、擬聲詞、語氣詞等無關文本信息,重新對劇本臺詞進行整理,得出京劇“樣板戲”文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文本,從一種“關鍵詞”形式提供內容取向的解讀。

詞和唱詞是戲劇作品的基石,詞雲或許可以簡單告知我們,京劇“樣板戲”在講述革命故事的過程中選擇了一種怎樣的敘事基調。滿目充斥著的“毛主席”、“同誌”、“革命”、“黨代表”、“任務”、“敵人”、“土豪”、“鄉親”、“鬼子”等極具時代氣息的語匯,僅從文本角度看,表達了一種單向的、指向明確的價值關照。
05、“樣板戲”作為一種革命藝術
政治和愛情是藝術的兩大創作源頭,在中國傳統戲曲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兩類主題先行的痕跡。政治主題下,有突出忠君報國的《楊家將》、有申明家國情懷的《四郎探母》、有反映廟堂宮鬥的《大探二》、有哭訴戰爭亂世的《荒山淚》。而愛情主題的劇目則數不勝數,《白蛇傳》、《紅娘》、《西廂記》、《霸王別姬》、《鳳還巢》、《牡丹亭》等等,共同構成了繁盛時期的傳統戲曲舞臺。
但是,“樣板戲”卻走上了一條完全政治化和去人情化的道路,這是樣板戲與傳統戲曲在藝術取向上的迥異之處。
在人物創作上,“樣板戲”中的角色表現出壹種模式化的臉譜特性。幾乎所有“樣板戲”中的正面人物都抱有苦大仇深的民族矛盾和階級沖突,人物經常處於極度歡欣、極度痛苦、極度幸福、極度憤怒的情感沖突狀態之中。[12]比如《紅燈記》中的鐵梅,本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但得知祖孫三代不是一家人,又面對敵人的威脅時,她突然充滿仇恨,轉而唱出“祖祖孫孫打下去,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又如《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寶,爹娘從小被敵人擄走,裝扮成啞人偷活在夾皮溝,她在劇中第一次出場就唱道“只盼討清八年血淚賬,恨不能生翅膀持獵搶,飛上山崗,殺盡豺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塑造純正的、無私的、愛恨分明的英雄,構建出一種屬於無產階級的浪漫英雄主義,成為“樣板戲”的重要藝術宣傳功用。根據江青的要求:“英雄一出場,就應當是一尊完美的雕像;任何場合,都要用最好的語言、最好的音樂、最挺拔的表演動作、最重要的舞臺位置和最突出的燈光服飾對他進行熱烈的謳歌”[13],正面人物自帶英雄光環,對毛主席和革命的忠誠、對無產階級的深厚階級感情和對敵人毫不留情的痛恨,而反面人物,則被包裝成暗淡、慘白、低矮、醜陋的姿態,人物關系總是呈現出一種劍拔弩張的誇張和過度。
這種情感塑造方法論直接導致了“樣板戲”中的人物完全拋卻了作為人本身的七情六欲,所有的人“都在說著同一模式的話語,其結果形成了奇特的偏離人性的階級共性話語。”[14]

在文革期間的倫理觀宣傳下,人性論被視作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流毒而遭到嚴厲批判,甚至在“樣板戲”再創造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到夜晚,爹想婆姨我想娘”被要求修改為“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15](《智取威虎山》小常寶的唱詞)的極端例子,“性”被視作腐朽和骯臟的代表,完全不被容於由革命純潔性所建立起來的倫理世界。
作為生理的兩性之別,在“樣板戲”中也被階級情誼和階級對立的二元關系所掩蓋。從人物形象來看,如果忽略掉明顯的服裝和裝飾,“樣板戲”中男性英雄和女性英雄之間將不存在任何性格和語氣上的差異,如《杜鵑山》中的柯湘、《海港》中的方海珍、《龍江頌》中的江水英,她們都是吃過苦的階級同胞,有著與敵人不共戴天的相似生活經歷,面對階級敵人要討清自己的“血淚帳”。“樣板戲”英雄沒有任何關於情欲的表達,在女英雄身上,更看不到任何作為女性之美的外化,婚姻、家庭、母性等正常的人類倫理被完全消弭掉。

而就音樂的藝術性表現來看,在保留了部分中國傳統戲曲元素的前提下,創作者們用西洋音樂體例對“樣板戲”進行了包裝,如引用西洋樂器伴奏、插入合唱段落、增加西方音樂體系中的旋律和音色,通過借鑒資產階級的藝術手段反對資產階級,以實現毛澤東對一種更為純潔的、革命的政治世界的期待。
但另一方面,“樣板戲”又在極力擺脫傳統戲曲中蘊含的中式古典主義形態,以諸多新穎的手段對京劇進行了革新,比如取消了京劇中原有的“尖團音”之分、刪去了念白中原有的“上口字”和“湖廣調”、小生,甚至旦角,摒棄小嗓改唱大嗓等。
在唱腔的風格設計中,英雄人物的唱腔設計盡量靠近“高精尖”,即追求一種嘹亮激昂的運腔,以此強化“偉光正”的英雄氣質。一般說來,傳統京劇中的旦角唱段,最高音會安排在鋼琴小字2組的mi到si之間,素以好嗓子著稱的四小名旦之一張君秋先生,在《秦香蓮》中最後一句“叫一聲殺了人的天”,以“天”字高腔結束,達到了小字2組的si,在傳統劇目中已經算是非常少見的高音。而在“樣板戲”中,仍以《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寶為例,她的唱段《只盼著深山出太陽》,最後一句“飛上山崗殺盡豺狼”,以“狼”字做結尾的高音拖腔中,竟然又設置了一個高腔,最高音達到了小字3組的do,也就是通常所說的High C,這種情況在《紅燈記》李鐵梅、《紅色娘子軍》吳清華、《海港》方海珍等的唱段中隨處可見。
無疑,慣常性地使用高音,過於註重英雄化聲腔,將“樣板戲”的主要人物塑造出一種難以靠近的精神氣質,使得“整部劇作的音響單一貧乏,總是呈一種走高的趨勢,缺乏一些戲曲必有的、豐富的審美品性。”[16]也許在上演之初會給聽眾帶來耳目壹新的激動聽感,但難以想象的是,十年文藝,只能聽到如此頻繁的“高精尖”程式,會給人們帶來怎樣的精神緊張和心理壓迫。
06、“樣板戲”的極端政治化
“樣板戲”從一開始就成為披著文藝外衣,用以表現和參與政治鬥爭的畸形藝術作品。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政治運動,毛澤東將鬥爭的矛頭直指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派,而他們背後代表的權力合法性來源則分屬兩條歷史路線:戰爭年代,以毛澤東為首的武裝鬥爭路線和劉少奇主管的白區地下鬥爭路線。
為人熟知的幾部“樣板戲”,從題材上看,主要表現了四個歷史時期的故事,分別是:抗日戰爭時期的《紅燈記》、《沙家浜》、《平原作戰》;三次革命戰爭時期的《杜鵑山》、《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沂蒙頌》;抗美援朝時期的《奇襲白虎團》;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海港》、《龍江頌》。毛澤東就曾在觀看《沙家浜》後表示:“要突出武裝鬥爭,強調武裝鬥爭消滅武裝的反革命”。[17]那麽,突出哪一條路線在四個歷史時期發揮了更大作用,便成為“樣板戲”劇情演繹的重要政治選擇。
對毛澤東本人的個人崇拜也理所應當成為“樣板戲”創作的“政治正確”,“毛主席”和“獲得勝利”之間,兩者在不斷地互相印證。隨處可見的毛主席語錄,被原封不動安插到劇情中,“毛主席萬歲”、“紅太陽”、“大救星”等口號不停復現,僅“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一條語錄就同時出現在四部劇中[18]。當毛澤東聽到《奇襲白虎團》劇中的嚴偉才說:“我們必須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這叫做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時,他笑道:“這些話不都是我講的嘛!”[19]他本人也非常願意看到“樣板戲”作品對自己政治能動性的肯定。

“樣板戲”蘊含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政治內核,即:共同的階級仇、民族恨。[20]它宣揚的是一種以階級仇恨為基石的鬥爭哲學,所折射出的暴力性,體現在人物的每一句臺詞、每一場情節中。正如李松所說,“樣板戲”家仇國恨的情節邏輯體現為:個人仇恨→家庭仇恨→民族仇恨→階級仇恨→國家仇恨。[21]
以政治指令指導文藝,是“樣板戲”文藝創作過程中的顯著特征。在《談京劇革命》(1964)一文中,江青提出“要在我們的戲曲舞臺上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來。這是首要的任務。”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樣板戲”創作“根本任務論”。1968年5月23日,“樣板戲”創作者之一、後升任文化部副部長的於會泳,第一次公開提出“三突出”口號,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本就深耕於濃厚的左翼政治傾向,由於諸多激進的政治指令幹預,“樣板戲”不斷蛻變成負載極左意識形態的文藝作品。
07、“樣板戲”歸來
文革結束後,“樣板戲”從中國的文藝舞臺上消失了若幹年,高層意見和民間思維都在小心回避這些曾讓人膽戰心驚的音樂。
到80年代,事情開始起了變化,鐵梅的扮演者劉長瑜感嘆道:“樣板戲《紅燈記》凝聚了許多專業人員的心血,至今有不少人喜歡它,前幾年在某些場合不準唱樣板戲,現在我演《春草闖堂》,演完了不唱一段《紅燈記》就不讓下臺。”[22]這一次,政治宣傳發生了神奇的轉向,80年代開始的對“樣板戲”的民間回應,慢慢放松了上層權力的神經。
2008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發布了關於開展“京劇進中小學課堂試點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規定:在已修訂的《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中增加了有關京劇教學的內容,確定了15首京劇經典唱段作為中小學音樂課的教學內容,根據不同學段學生的具體情況,將15首京劇唱段安排在一至九各年級。[23]規定的15首曲目中,有9首來自於京劇“樣板戲”,但“樣板戲”的字樣早已被規避,“現代戲”這一弱化了政治面貌的界定語被重新使用。
戲曲名家裴艷玲曾戲謔地表示:“《紅燈記》‘獄警傳似狼嗥我邁步出監’好不好?好!可是妳學戲開蒙,不也得‘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嗎?妳能拿《紅燈記》開蒙?武生戲妳怎麽不用郭建光開蒙?”[24]很不幸的是,裴艷玲的戲謔如今正以一種曖昧的姿態成為現實,看看近年來的新編現代戲,“樣板戲”的基因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成為一種復興、成為中國後現代戲曲演進的一種“優良傳統”。
“樣板戲”終於重回人間!
08、永遠革命,永不消逝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開頭與結尾分別有一個情節遙相呼應:童年玩伴的傻子,在兩次場景中出現時,嘴裏都不停地念叨“古倫木、歐巴!”。起初,很多人只當那是一句沒頭沒腦的瘋話,而此刻終於恍然大悟:原來那是“樣板戲”年代給王朔、姜文們留下的最深刻的青春暗號,一整代人的青春英雄數來數去,也許都逃不出嚴偉才、李玉和、楊子榮、趙勇剛和郭建光。
戴錦華曾感嘆“樣板戲”背後所代表的壹整套文化生產現代性,她本打算將“樣板戲”作為一個文化笑柄,卻突然發現它是“一個如此現代的文本”[25],塑造出了一種完全有別於八十年代的現代化敘事。西方六十年代左翼思潮,也憑藉電影《解放軍在巴黎》之口,對“樣板戲”連連稱贊“思想多麽深刻!”,視之為革命化的中國先鋒藝術。
現代性的迷思也好,先鋒派的意味也好,“樣板戲”留給當代的社會思考與文化爭論從來沒有停止。
最後,用《智取威虎山》創作者們的話作為總結也許正合時宜:
常寶這一個人物的唱腔,它是什麽“流派”?什麽“流派”也不是,幹脆說:革命派![26]

文獻引用:
[1] Barbara Mittler."Eight Stage Works for 800 Million People":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usic—— A View from Revolutionary Opera[J].The Opera Quarterly, 2010, 26(2-3).(吴群涛、李松译,王建平校)
[2] 高波.“样板戏”——中国革命史的意识形态化和艺术化[M].1.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p35.
[3]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M].01.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p132.
[4] 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其内幕[M].1.知识出版社, 1995 :p19.
[5] 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其内幕[M].1.知识出版社, 1995 :p24-25.
[6] 转引自Barbara Mittler."Eight Stage Works for 800 Million People":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usic—— A View from Revolutionary Opera[J].The Opera Quarterly, 2010, 26(2-3).(吴群涛、李松译,王建平校)
[7] 李松.“样板戏”数目考辨新论[J].长江学术, 2012(01):p150.
[8] 江青:《在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9] 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其内幕[M].1.知识出版社, 1995 :p55.
[10] 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其内幕[M].1.知识出版社, 1995 :p90.
[11] 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其内幕[M].1.知识出版社, 1995 :p108.
[12] 祝克懿.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M].1.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p223.
[13] 许晨.人生大舞台——“样板戏”内部新闻[M].01.黄河出版社, 1990 :p127.
[14] 祝克懿.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M].1.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p264.
[15] 高波.“样板戏”——中国革命史的意识形态化和艺术化[M].1.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p77.
[16] 祝克懿.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M].1.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p90.
[17] 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其内幕[M].1.知识出版社, 1995 :p56-57.
[18] 祝克懿.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M].1.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p213.
[19] 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其内幕[M].1.知识出版社, 1995 :p89.
[20] 刘康润:《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文汇报》,1972年6月3日
[21] 李松.“样板戏”中的阶级斗争与家仇国恨[J].戏剧之家, 2010(8).
[22] 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其内幕[M].1.知识出版社, 1995 :p2.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2019-10-07].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4/201001/80578.html.
[24] 许石林.裴艳玲:你非让我说,我就骂娘[EB/OL].[2019-10-11].https://mp.weixin.qq.com/s/Ac4RC4qcsdlzrig6ELrXog.
[25] 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M].01.知识出版社, 1999 :p250.
[26]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关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音乐形象的几点体会》,《红旗》1970年第2期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