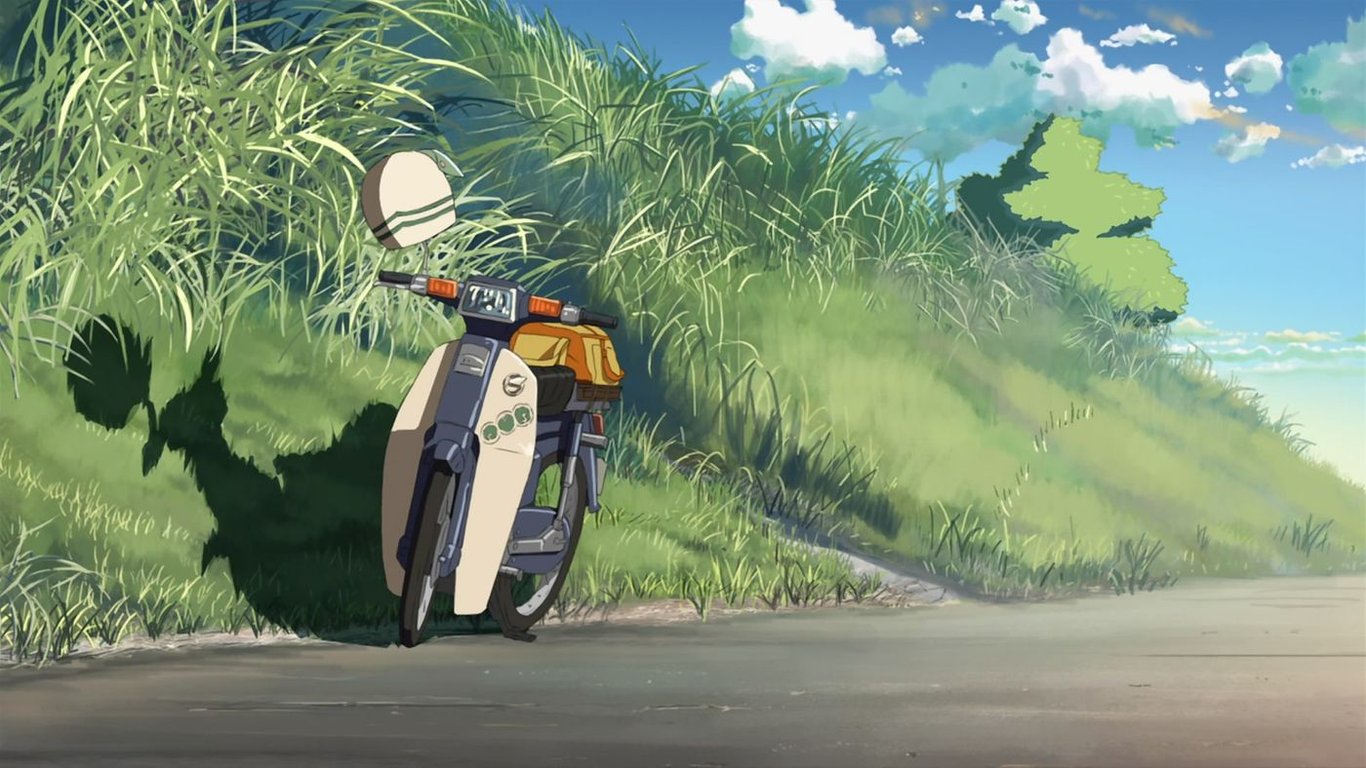
飞鸿响远音
等待
最烦的就是个等字。
什么都要等。给访谈对象发信息要等回复,续签证的材料要等签名,连清洁工做卫生,他都要等地晾干了才能进屋。学语言要等,申请结果也要等——如果没有一件事发生在当下,此时此刻,那时间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只是为了抵达那些尚未降临的未来吗?
烦躁之间,阿米给他发了消息,说研究生院长还没在邀请函上签名,让他过来商量怎么办。能怎么办?两人聚一起就能远程遥控院长签名了吗?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呢?可他不能等。套好了衣服他就出门了,在门口差点被鞋带绊倒,低头一看才发现鞋带根本没系好,没走几步就松了,右脚长长的鞋带被蹂躏地耷拉在地上,灰头土脸的,要不是一头系在鞋上,那样子真像被赶出家门的不肖子孙。于是他又弯下腰系鞋带,这次为了防止脱落,他多打了个结。出了大门,身边走过一个头顶箩筐的妇女,箩筐里是削了皮的芋头,白胖娃娃坐篮子一样地一晃一晃,又像粗大的藕——他不禁想到许久没吃到藕了。上次吃藕还是两年多前第一次封城期间,他为了在公用厨房见到暗恋对象,没事就去做饭,照着日剧里的食谱做了个金平莲藕——连暗恋对象也是白白胖胖的,像个小孩子。
如果放在平时,他甚至想上去买两个。自打上次看到门房大叔蒸芋头闻到淡淡的甜香味,他就馋得不行,想让大叔帮自己买几个,又怕被坑钱——他是怕惯了。兜里本来就没个仨瓜俩枣的,还得处处省钱。不过今天他既会吃到蒸得甜香软糯的芋头,又会被狠狠地宰一笔。如果此刻他知道这两件事会在一天先后降临,不知道他会不会精神分裂——至少也会分裂一小下吧。但此刻他只觉得箩筐女士头顶的是一堆手榴弹,若非还算结实的身体捂住了他一脑门子的怒火不喷出来,只怕此刻芋头先后炸飞。箩筐女士的衣服上有六个汉字,写着“无热血,不青春”。他此刻确实是够热血的,热得都要炸雷了。哪来的青春呢?青春早就小鸟一样一去不回来了。是啊,连青春也是在等待中蹉跎过去了。读了一堆学位,也不像是多努力来的,像是苦劳得到的一点微薄的回报。
十点多的光景,一天的温度已经升到最高,远处的路面都可以看到热扰流,每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都像是要赶紧躲开这块随时会爆炸的是非之地一样,他此时的怒火已经到了连空气都能助燃的地步。所以路边有乞丐一口一个argent一边尾随他的时候,他甚至连摆手呵斥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别的不会,什么chinois,argent,学得倒挺快。他不禁冷笑一声。
商量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博士生院长没签字,打了一番电话也没人接。两人决定带上东西直接上移民局。他讨厌这样,带着许多未知不安地等待着。这等待不是鳄鱼捕食猎物,潜伏在水下蓄力一击,随时准备弹射出去。潜伏的猎手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主宰着其他生物的生杀大权。他现在是被抛进深海的浅海鱼,和时间赛跑着。不赶紧游上去就会被水压挤爆。可是往哪游呢?四下漆黑一片,看不到一点亮光和方向,一不小心还可能顺着暖流游到海底的火山口,或者游到鮟鱇的嘴边做了盘中餐。慌乱地挣扎、摆动鱼鳍,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动作。每进一步可真难啊。
《大宅门》里白老爷就这么说过。“凭什么退一步?我每进一步有多难?凭什么退?”白老爷还说过,“最烦的就是个‘忍’字,什么都要忍,那还能做什么事”。白老爷到底把自己起了个好歹,我跟他不一样。想到这,他也就只能暂时忍了。
本以为移民局会是个像样点的建筑。可若不是门口手绘的牌子上写着immigration, 周围有不少持枪的警察,他甚至以为是个普通小学校。牌子上还有autorite du Lac Tanganyka的字样,看来和环境部门也在一起了。院子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厅里人们见缝插针,那场面活像电影里已经战乱国家的边防,大批民众抢着要逃离战场。阿米身材魁梧,在前面开道。绕过几拨人后他们进了抬头visa service的办公室,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一些法语词和数字他倒是听出来了——他早就听说非洲语言里有不少法语词汇。听出来的意思是按照时间有不同的价格。等阿米拉他边走边解释,他一下头就大了。走到抬头有chef的办公室门口,看到门上贴的价目表,他才知道阿米所言非虚。除了几天的过境签证和一个月有效的普通签证,对他这种长居人士,要么每三个月续一次,单这一项就要七十美元——如果需要多次出入境还要加钱,或者办理两年居留的无限出入签证,要价高达五百美元。当然还可以花四位数的美元获得可以居住九十九年的签证。究竟是这个国家能活这么久,还是我能活这么久呢?此刻他真希望自己是个刚果人,因为刚果留学生只需要花二十五美元就可以获得一个一年逗留的长居签证。是啊,有好处的时候他就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好像每当有各种好处的时候,他的国籍总是排不上用场。可你想从小就成长在刚果,整个小学时光国家都在内战吗——你能活过小学吗?或者从小就生在布隆迪,四五岁的时候父母经历大屠杀么?想到这,他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趋利避害。阿米已经拉着他走出大厅了。那半封闭的大厅里满是浓厚的男人的体味和烟味,让他想起来中学时常去的网吧。只是今天的心情实在很沉重。
跑了一上午的结果不仅什么事都没办成,反而要再搭进去一笔不小的开支。回程的车上他只觉得闷热。不过他庆幸地发现自己随便抓的衣服是一件在巴黎临时起意买的优衣库,虽然比薄衬衫厚了一点,但是面料丝滑柔顺,相当透气。薄衬衫穿在身上,此刻只怕早就湿透。一个路口处他们停车熄火,前面不少军警戒备停车,阿米说应该是有要员经过,果然不一会就看见一辆满载持枪军警的皮卡开道,后面一水的黑色吉普,最后同样是一辆满载持枪军警的皮卡压阵。人们说说笑笑,以为常事。他知道今天阿米忙前忙后,一顿午饭少不了都请客表示感谢,让阿米随便挑。阿米略一迟疑便定了校外吃。他只是没心思地看着窗外。
到了饭馆他就来心思了。又是一个非洲特色的自助——一个盘子想盛多少盛多少,只此一盘。大多数都是普通的素菜,蒸土豆,蒸芋头,烩蔬菜,烩豆子和软塌塌的薯条——让他想到激烈做爱一整晚后自己坍塌的身体。阿米特意提醒他多盛两勺cassava,阿米说这是一种用cassava叶子熬成的糊糊,是本地特产。浇了两勺在米饭上,尝一口像中药。怎么这什么都做得有点药味?他管不了这么多,牛肉使劲地盛。结账的时候才发现按块算钱,眼尖的服务员早就在他盛肉的时候算好了价格。一块就要一千法郎。他盛了七块。单点素菜的一盘只要四千五百——看来阿米这次没有狮子大开口。不过这不重要,他今天就等着这一顿。他每种都盛了两大勺,盘子堆得像金字塔。甫一坐定就扒拉起来。活着,像牲口一样地活着,他想。哎?这句是谁说的来着?他一时想不起来,可能是余华,可能是张承志,也可能是梁晓声,或者高尔泰。总之内容肯定和那段时间有关。可牲口能吃炖牛肉吗?牲口能吃得这么精细吗?牲口能活着吗?难道七块牛肉不是牲口做的?他不禁想笑。如果再多一个自己,那这世界一定多出一个杠精来。那些自恋的知青油腻老男人他是做不成了,做个当代小布尔乔亚似乎也没什么钱。看来连人生都需要等待啊。
饱餐一顿的两人不再说话,似乎复杂的手续和多出来的许多文件又一次把他们压入了深海。下车回家,他趴在床上昏昏沉沉睡着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闷上心来瞌睡多”,这句他记得,是《西游记》里形容金角大王的。说的是金角大王折了兄弟银角大王,和孙行者乒乒乓乓打了一通,回来洞里见手下小妖俱被行者发狠打死,落了个孤家寡人,心下凄惨,故而昏昏默默。
我连金角大王都不如,他模模糊糊地念叨。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