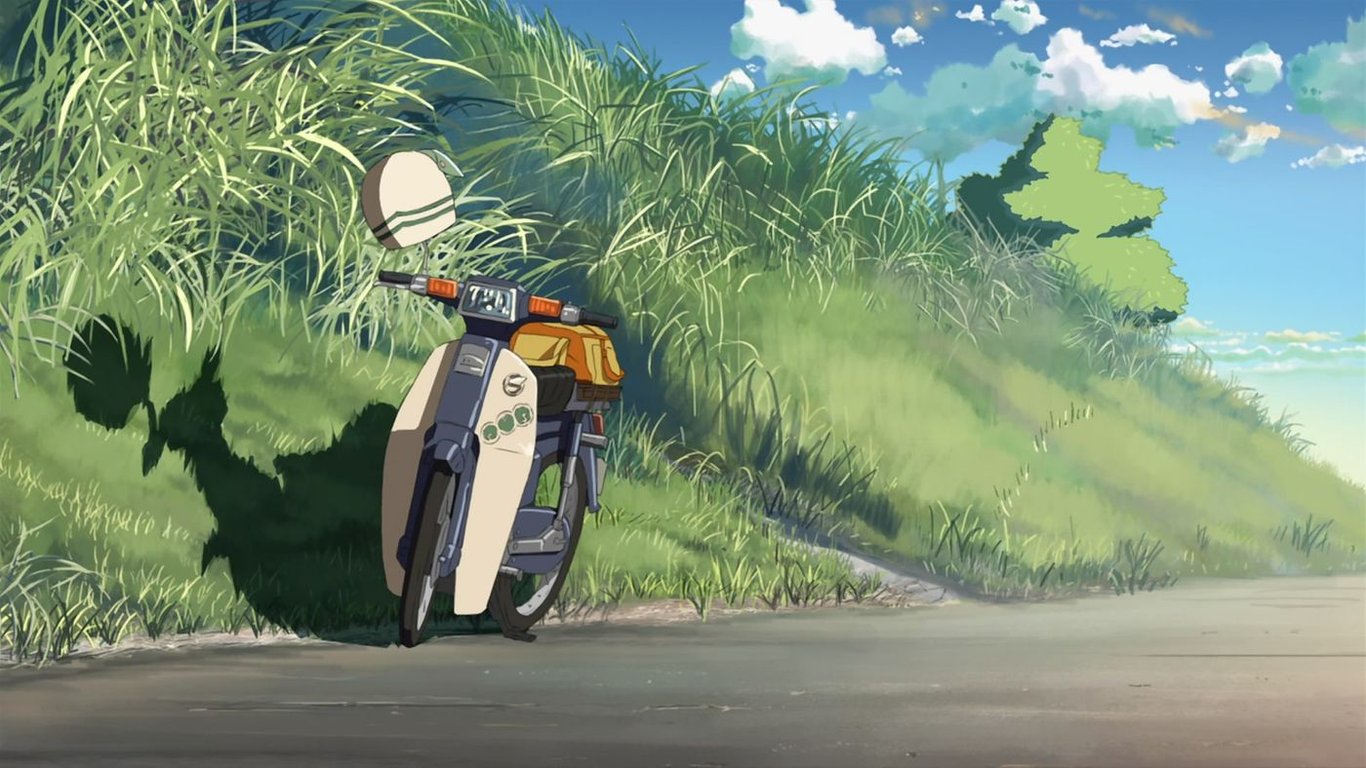
飞鸿响远音
入侵
我对昆虫和形似昆虫的其他节肢动物似乎总是缺乏好感,小时候不爱吃皮皮虾和蟹,因其面目可憎。不知是不是因为形态和四条腿的哺乳动物差别太大。认知上的差异带来未知的恐惧,加上小时候家长讲给我的各种传说,比如臭虫在人睡觉时爬进耳朵,住在里面不出来最后耳朵化脓。啃食得寸草不生的行军蚁、把人蛰死的杀人蜂、含有剧毒的黑寡妇,还有一些真实的案例,比如吃了含有寄生虫的肉,寄生虫爬进身体,钻进脑子,整个人疯疯癫癫,再也回不去。小时候被要求强制服下的驱虫糖丸,尽管做成了塔的样子,加了糖,可我吃起来总有怪怪的味道,怪得难以下咽。小小的昆虫,在我小小的世界里,留下了许多坏印象,仿佛它们是危害的来源,污染的罪魁祸首,让人谈之色变的怪物。
好像电影里的昆虫也总是扮演负面角色,金字塔里的护卫甲虫、变成昆虫破坏通信的变形金刚、可以操控的蜜蜂无人机,无孔不入的昆虫看似渺小,聚沙成塔的时候也能让人恐惧。这就是我待在房子里的感受。没有多少“虫声新透绿窗纱”的浪漫与对春日的期待,隔着纱网扑向室内内灯火的飞蛾,小型蜻蜓一样的马蜂,如同迷失航线的鲸群般爬进室内的马陆,嗡嗡作响的金龟子,潜伏在浴室角落的蟑螂。水泥砖瓦丛生的城市空间,在灯光下和阴影里,几种生物就组合成一个互不侵犯的生态。
如果有入侵,那就是他们入侵了人的环境,入侵了我的环境。蟑螂马陆喜欢阴湿,藏在浴室本无可厚非,可当我打开灯,为角落的黑暗带去光明时,突然看到它们或蠕动着黝黑的身躯,或大摇大摆地张扬着长长的触须,像是在挑衅我入侵了他们的领地。我对两种生物的态度截然不同,大概是因为马陆移动缓慢,好像我对它有完全的掌控;而蟑螂移动迅速,就让我摸不到头绪,失去控制的可能。我不禁对发笑,这是否就是一种潜移默化感知的意识,总是想着掌控什么?或许也有历史因素,毕竟蟑螂是“四害”之一,可爱国卫生运动的背后,对人口、身体的发展要求与强健渴望,不也一个民族神话的重构、对现代的呼唤?在包苏珊的表述中,八十年代的锻炼身体,在话语和实践的建构上为“为中华之崛起”的道德感所召唤。一副强健的身体,一个优生优育的民族,一群计划的人口,似乎才是展望“现代”的明天的基石。于是所有危害这些事业的事物都要被清洁,现代的社会、现代的城市,应该是干净、光滑、整洁的。那些阴暗的角落也需要被清理,哪怕我们正在入侵的是它们日常的生活空间。
不知是出于本能的恐惧,还是历史幽灵的阴影挥之不去,我捕捉了蟑螂。本想放到院子里放它一条生路。可是放生后它在廊下徘徊的身影又激起了我心中的恶,那种无处而来、单纯因为我有能力掌控和捕杀的恶。于是我走到院子里,抄起一块板砖,用碾压的方式拖行,直到它变成彻底的二维的存在,然后用花坛里枯萎的叶子和花瓣铲走它的尸体,扔进花坛——这听上去有点讽刺,竟然是个有点符合人类世界的浪漫的埋葬方式,在紫罗兰的簇拥与朱蕉的守护下,化作春泥,返回最原始的地方。看上去很美,可也十分残酷,这也许是我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方式吧。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死去的蟑螂从土里复苏,长成一棵巨大的树,旁边环绕着许多它的孩子,它问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一时语塞,讪讪地说了一句我不喜欢,然后回房间抄起斧子,使劲地砍伐起来。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