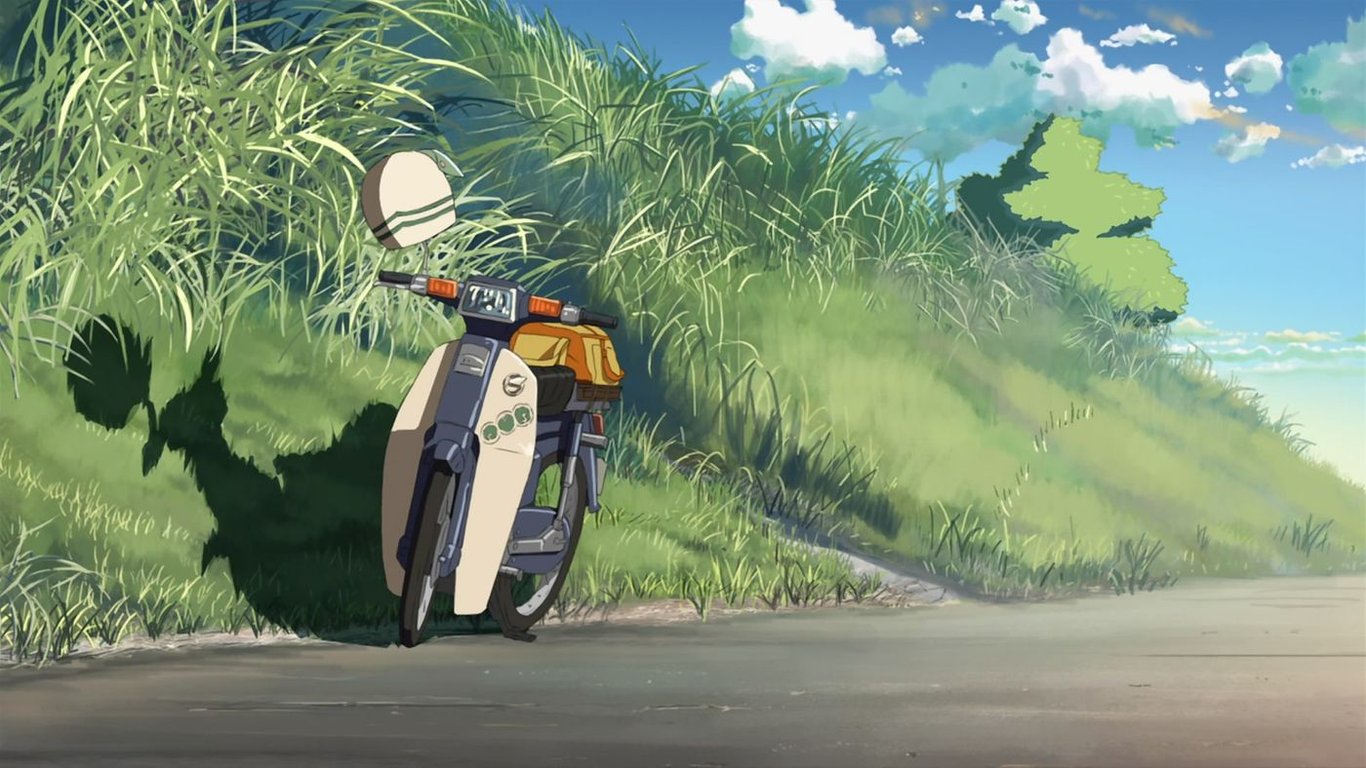
飞鸿响远音
武汉
这是一篇迟来的游记,或者说是有关武汉记忆的整理。它缘起于 2013 年的早春三月。我提心吊胆的同时,又抱着做坏事的窃喜与侥幸,在董老师于外地访学的间隙与朋友跳上了南下的列车,在紧张的毕业论文收尾之际,去武汉和十堰偷得几日浮生。如今武汉已经以另一种沉痛的形式为世人所知。这篇文章大概与此无甚关联,它不是因为一周年的时光溯回而勾起我对这座江城的记忆。在去武汉之前,我已经看过水汽弥漫的长江,穿过雨水和空气洗刷得灰旧的老式楼房,呼吸过疑云密布的水汽。我的启蒙电视剧之一,正是以武汉为背景的《来来往往》。所以我对武汉最初的记忆,是康伟业在逆流而上去往重庆和宜昌的江船上一把拉起林珠的手放在胸口;是康伟业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放下一切事务义无反顾地飞往北京幽会林珠;是康伟业和林珠在北京的宾馆长长的走廊上勾肩搭背吻颈交欢地大步流星冲进走廊尽头的套房,咣当一声关门的巨响和林珠伸出手来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这关门声从此把我的懵懂未知关在了门外,把情欲与荷尔蒙关进了门内。一霎时的电闪雷鸣穿透我年幼的心,人世间最原始的冲动从坚硬的泥土破土而出。从此我对男性的审美是康伟业这样高高大大、沉默克制却激情满满的男人,对女性的审美是林珠这样时尚靓丽、风情万种又大胆得不管不顾的女人。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不再是我对男性与女性审美的全部。但他们带我第一次去了武汉。那座城市可以街道新旧混杂、天气闷热不堪,又纠缠了理智与情感、当下与历史的复杂生活状况。康伟业陷入那些理还乱的情感中,与发妻段莉娜名存实亡的婚姻,对失去新鲜感后远走高飞的情人林珠的想念,在新新女孩时雨蓬身上所看到的初恋女神戴晓蕾的影子,分不清一切的他大醉江边,于码头上一枕到天明。我那时觉得,康伟业像极了和妈妈吵架后的爸爸。同样的灌醉自己,早上一觉醒来时妈妈早已按部就班地上班,只留下不知所措的我看着混乱的家里回想着昨天的争吵。呵,男人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的一切。所以我不喜欢电视剧添加的略显光明的尾巴,康伟业回心转意,段莉娜多少年来第一次真情流露,两个人在最初相亲见面的亭子互诉真情。我仍然记得小说中对段莉娜的形容,她庸俗的审美把家装饰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夜总会,俗艳夸张的衣服穿在身上像个老妖婆。若干年后我在《红楼梦》才知道了一个更精确的词语,死鱼眼睛。
我去武汉的时候当然不只有《来来往往》的记忆。李娜已经二满贯加身,她在球场用湖北方言泼辣训斥丈夫的画面早就传遍世界。大陶红的敢想敢干的来双扬和颜丙燕的负重前行的李宝莉逐渐搭建起我对武汉女人更为立体和多面的想象,她们勇敢、坚韧,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她们不一定聪明,但拥有生活的智慧。
武汉的公交车和南京的公交车一样开得飞快,甚至更加不讲道理。江边公园附近有新式摩登的大楼,也有如《来来往往》中一样灰旧了几十年的楼房。这座城市是那么横冲直撞、风风火火。我记得第一次吃豆皮是在往马甸方向的一个湖北菜馆,还是当时男朋友带我去的——他就是一个湖北人。油光酥脆的豆皮裹着米和肉末,油脂带来了饱腹的快感。然而我和朋友更深入武汉的小吃街时,我却无缘饱更多口福——武昌鱼太多的刺让我望而却步,裹着锡纸的烧烤在我面前冒着煎香的热气,我只能咽下口水。
那年去的太早,武大的樱花稀疏可见,武大校园里还未游人如织,但我们似乎都不太喜欢这个校园。不只是对庞大校园的凝视让我沉默,这里太富于生活烟火,不适合静心学习。校园里到处是做生意的人,有卖椰子的,好像还有关于校园旅游的。我所记住的是一个糕点店买到的樱花牛奶,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樱花炮制,但颜色很娇嫩。
最后我们去了武当山。我想亲眼看看玉娇龙跳崖远遁的地方。只是后来我才知道电影的外景地在河北。那个跨越在空中的月牙形的石桥,从我看这部电影起就一直以为它在武当。那不是什么张三丰修炼的场所。比起张三丰等等历史存在的人,我反而觉得李慕白、玉娇龙才是真实存在过的,她真的跳了下去。对自由的向往与家庭的约束、对情感的压抑与放纵,还有执念的追求与放逐,好像都那么真实地在我经历的每件事中矛盾着。三月的时间,武当山的背阴面残雪压枝,清角吹寒。裹在寒衣中跻攀寸步千险,脑子里想的是玉娇龙和罗小虎,现实里是我在情感世界的沉默。我现在的种种问题,大多来源于沉浸在影视与文学中太深,把自己的生活一一类比到文本中,仿佛只有那样我才能确切感知自己活过,仿佛那些经历过的才是真实的、有温度的。
也许我所去过的不是真实的武汉,只是一座由光影和文字搭建起来的江城,它仍旧若隐若现在江滩河道中,从未靠近,从未远离。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